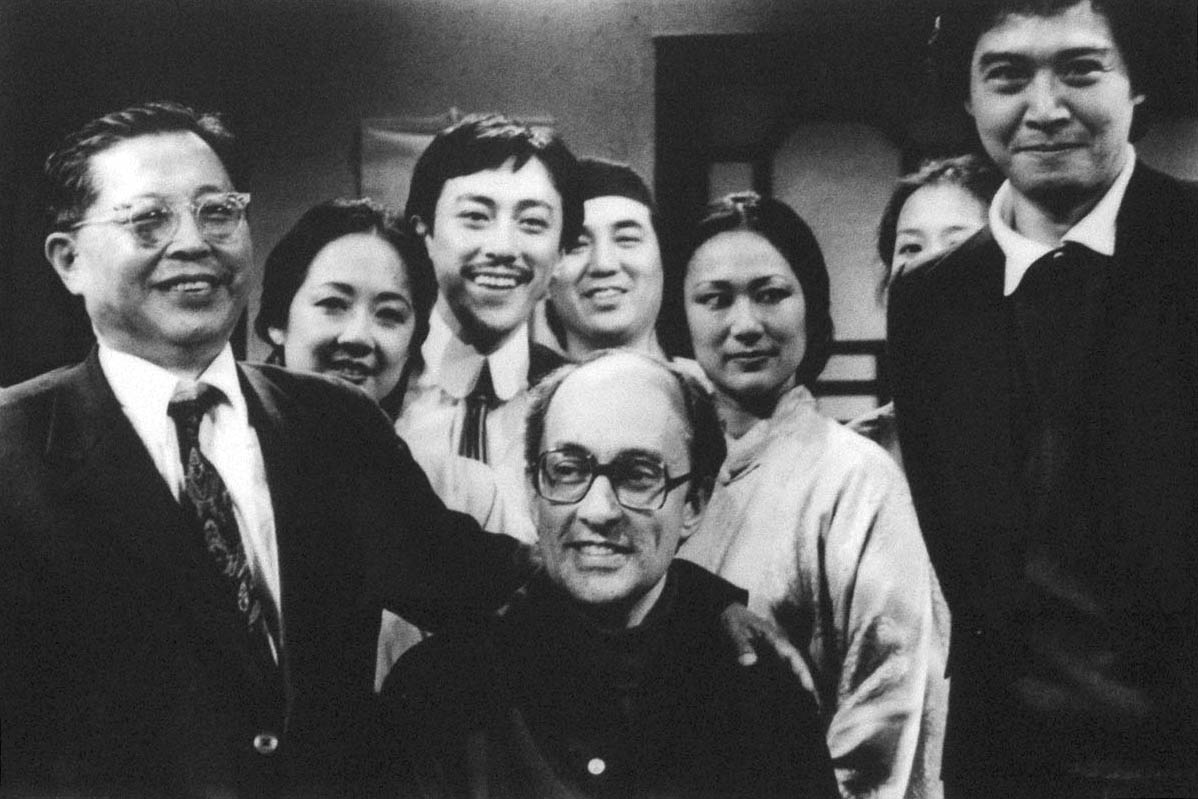
曹禺访美
今年恰逢剧作家曹禺先生诞辰百年,金秋时节,将在上海、天津、北京、潜江、香港等地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演出和学术研讨活动。伟人已逝,背影渐远,但精魂不灭,英灵宛在。
100年前,一个名叫万家宝的孩子诞生于天津。23岁时,他以曹禺的笔名发表了惊世剧作《雷雨》,被誉为中国戏剧的天才,该剧也被称为“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后曹禺又创作了《日出》(1936)、《原野》(1937)、《北京人》(1941)、《家》(1942)等经典剧作。解放后,尽管其创作高峰已过,但宝刀未老,仍有《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王昭君》(1979)等剧作问世。自曹禺的代表作发表以来,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至今仍不断上演于世界各地舞台。随着时间的磨洗,其剧作深刻隽永的人文内涵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日益凸现出来;曹禺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而他的创作经验对于中国戏剧的发展与繁荣深具启迪意义。
艺术创作是人类一项复杂的意识活动,艺术作品则是人类精神灌注其中的产物。当自由的人性在尘世中突围,天才的灵性在天国外寻觅时,我们似乎无法给感性的创作加上理性的标签。但是,随着曹禺戏剧研究的不断深入,他那充满诗意和质感的语言、鲜明而典型的人物、奇特而精妙的构思、丰富而深刻的寓意,已经开始被探究和解析,让人们从中或可领略其艺术创作的玄机与意义。
苦闷是艺术的积淀
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认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曹禺虽然自幼生活优裕,但是由于生母早逝,父亲严厉,直接导致了亲情关系的扭曲和家庭氛围的冷寂,也造成了童年曹禺内心的苦闷和压抑。在《雷雨·序》中,他说,“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正是这样的心态情感,使他延续了对于人生认识的严肃性,秉持了人文关怀的细腻性,让他决不会高蹈于现象一般,张扬于情绪表面,而是把心沉得很深,把视角放得很奇,以冷静、敏感、犀利的目光,在别人习以为常的世象背后,发现生命存在的本质真实,体悟不可知的命运玄机,以及被压抑的人性和人生的困境。
观看曹禺剧作的演出,我们或许难以感受时下泛娱乐化所带来的被安抚的快感,但是却让观众深感戏剧情境的惊悚,并由此引发自我的颖悟,实现心灵的净化。
曹禺最早发现了处身其中的社会与人生的残酷,在他青少年时期,父亲和大哥的尖锐冲突,让他发现了亲情背后的残酷;保姆段妈家破人亡的故事,让他感知了底层人们被压迫、被损害的残酷;而姐姐因婚姻不幸抑郁而终的遭遇,让他领悟了女性美的生命被剥夺、被毁灭的残酷;特别是父亲逝世后家道中衰的打击,更让他领略了世间小人趋炎附势、隔岸观火的残酷。这些不幸,在一个平常人心里,或许只多一些自怜自艾的心思,但在曹禺心里,却像一滴墨汁晕染开来,延宕生发出“天地间的残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见《雷雨·序》)的哲学意味,甚至直接导致了他对旧的社会形态和家族制度的反诘。曹禺在戏剧思想和美学层面上所表达的残酷,比法国戏剧理论家阿尔托所提出的“残酷戏剧”,在时间上要略早一些,其戏剧作品熔铸了他最炽烈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其中所具有的深刻哲理和普泛的人文价值,或许正来源于他对人的现实存在的超越性反思,以及对于人的生命、尊严、终极意义的不懈求索。
守住创作的心源
剧作家夏衍曾经教导年轻的写作者,“不熟悉的不写”。曹禺是“以我手写我心”的人。封闭的家庭,被扭曲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些“家的梦魇”固然带给曹禺内心沉重的压抑,但是,也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欲。家,作为他的灵感来源和真情所系,一直萦绕在他的意识深处。他的戏剧情境多半置放于封闭家庭,《雷雨》《原野》《北京人》《家》概莫能外。他熟悉周朴园式的威严,懂得仇虎式的迷惘,深知蘩漪式的乖戾,熟谙愫方式的静美,因此书写起来得心应手、妙趣天成。写出视域中自己熟悉的事,写出性灵上自己相通的人,这是曹禺戏剧创作成功的保证。解放后,曹禺在提交自己的创作计划时,也曾列出过要写反映工农兵的戏剧,但是无奈笔锋不利,书写迟迟。
就目前的研究结论看,人们普遍认为,曹禺解放前的剧作要好过解放后的,笔者也曾被海外的学者考问这一问题。其实这里没有简单答案,它关乎社会、历史、创作心理、审美倾向等诸多奥秘。当“家”这个曹禺戏剧意念的源泉枯竭之时,也正是他的创作情思无法维系之日。首先,曹禺的戏剧起势很高,正所谓“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创作差强人意,如果不是最好的,他宁愿舍弃一般的。这和很多码字数、混稿费的写家志趣殊异。其二,一个人的创作有高峰就有低谷,天才的作家尤其如此。写不出就干脆不写,决不应付差事,这也是曹禺的正直。其三,在新时代的环境里,离开了“苦闷”和“忧郁”的曹禺,放弃了他曾经以心血灌溉的素材源地,转而去书写自己并不真懂的领域,这是他创作生涯的大转折,也是他的戏剧之笔逐渐艰涩的开始。曹禺说“写作这东西,可是心血,是心血啊!”不曾在自己心血里孕育生成的人和事,怎么可能展现出真的灵魂?因此,如果把创作当成是对自我心灵矿脉的开掘,那么切忌避开自己的富矿区,转而寻求他人的宝藏,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
人是戏剧的灵魂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而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戏剧文本不仅隶属文学的高级范畴,而其因为最集中、最典型地显现了在假定情境中人性的各种反应,因此更具真实可感的人性内涵。一部好的戏剧,总让人为其中的人物浮想联翩,为其命运结局感慨唏嘘;而一部不那么好的戏剧,或许在人的印象中留有一些情节断片,但总归会很快消散。佳构剧或肥皂剧有时也会有一些奇特的构思,但总归因为人性的挖掘深度不够,而淡化了其艺术的价值。
想到曹禺先生的戏剧,我们的眼前会出现一系列生动、具体、奇异而富有魅力的人物,周朴园、蘩漪,陈白露、潘月亭,仇虎、金子,愫方、文清,觉新、瑞珏等,哪怕是出场时间很短的鲁大海、顾八奶奶、白傻子、陈奶妈,也都是各具个性,栩栩如生。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无论沿着曹禺笔下哪一个人物的命脉开掘下去,都会给人带来发现的惊喜。笔者的一位澳门朋友,仅以周冲形象分析为题,就完成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硕士论文。
曹禺善于塑造人,是因为他善于琢磨人。在晚年,他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是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田本相在《曹禺传》中写道,“他一生都在探索着人,探索着人生,探索着人的灵魂……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曹禺的人学观念有他普泛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愫,他从不把人物当成个人意旨的传声筒,从不用简单的道德规律去考量一个形象的价值,也不会让人物成为诠释某种主题的工具。他总是尽心竭力向内挖掘人的灵魂,向外审视其命运变幻的轨迹和奥秘,审视其在特定情境中的独特动机和行为魅力。因此,他笔下的人物,不仅有生命的质感、美学的韵味,更有时代的机理、现实的内涵。
追寻恒久的文化价值
23岁就创作了重要剧作《雷雨》,并且奠定了自己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地位的曹禺,被公认为是杰出的艺术天才,具有超凡的秉赋。然而,如果我们回溯他23岁前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积累,就会发现,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早在中学时期,曹禺已经阅读了很多古典、现代书籍,一部家藏的《戏考》居然被他翻烂了,他还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在校园戏剧活动中,更是积累了编、导、演的各种经验。此时他已开始酝酿《雷雨》剧情,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以致睡床之下堆满了废弃的稿子。一部《雷雨》可以改成二十多集的电视连续剧,并且一直被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得到很多艺术家不同角度的诠释,这也从侧面显现了它的厚重内涵和凝练叙事。
曹禺认为戏剧创作要寻找“金刚石的语言”,他的创作似乎没有过宣泄式的快速书写,总是反复琢磨、历经推敲,恰如老蚌育珠一般,因此其剧作至今依然保有超越时代的优美、生动、精妙、洗练。在创作方法上,曹禺秉承现实主义的精神,又兼蓄现代主义的精髓。他认为,所谓现实主义,也不是那么现实的,他有自己的判断、取舍、坚持、涵化。在《北京人》中他没有写出抗日的背景,也没有点明愫方的奔赴地是延安,他讲究的不是戏剧合不合局部的、暂时的意念之“槽儿”,而是讲究戏剧够不够人性的、美学的超俗的“味儿”。他追求着戏剧艺术的高境界。
为了这种高境界的出现,他不愿重复已有的创作模式,一直探索着新的戏剧结构和表现形式。从《雷雨》典型的闭锁式结构,到《日出》群像式、散点状的人物谱系,再到《原野》带着粗犷、原始气息复仇行为的精神追索,再到《北京人》契诃夫式的静水深流、深刻隽永的表现形式,他一直奔突着,探索着,要打破自有的成功模式。晚年他一直想要写出“一个大的东西”,但毕竟垂垂老矣。尽管这样的自我折磨耗尽了他的力气,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是一位不曾凝滞、衰颓的智者。
在只求一时效用、不求持久价值的时下,人们正热衷于造星和包装的市场效益,却忽视了艺术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恒久性,才是它赖以存世、经久不衰的前提。而那些像烟花一样绚烂于瞬间的东西,注定不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踪迹。应该正视的是,曹禺执著的创作方法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