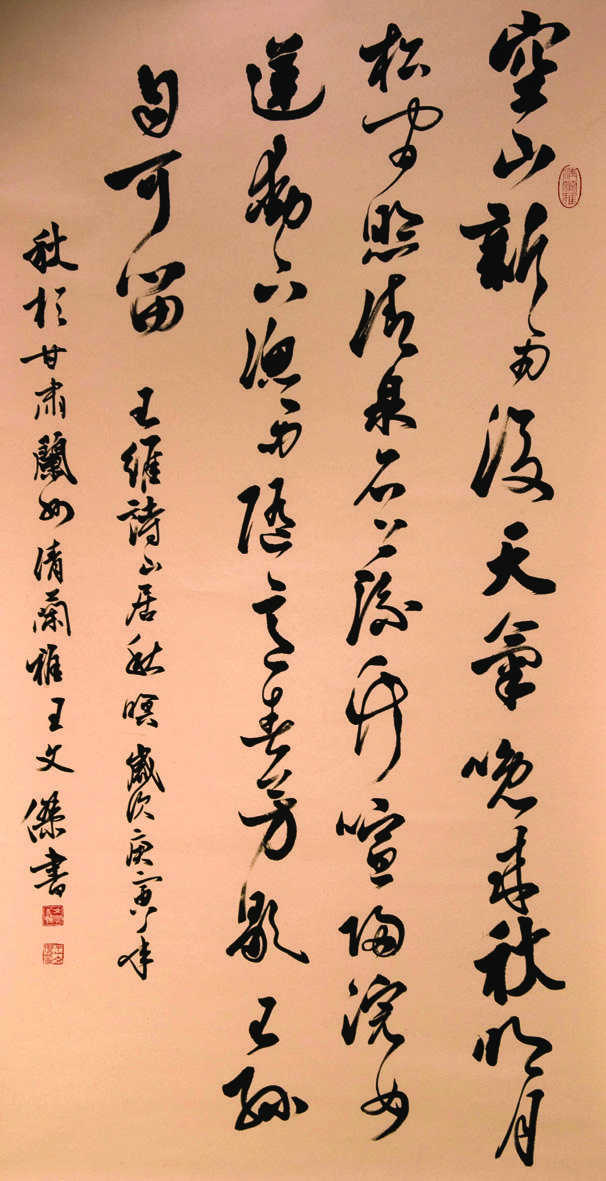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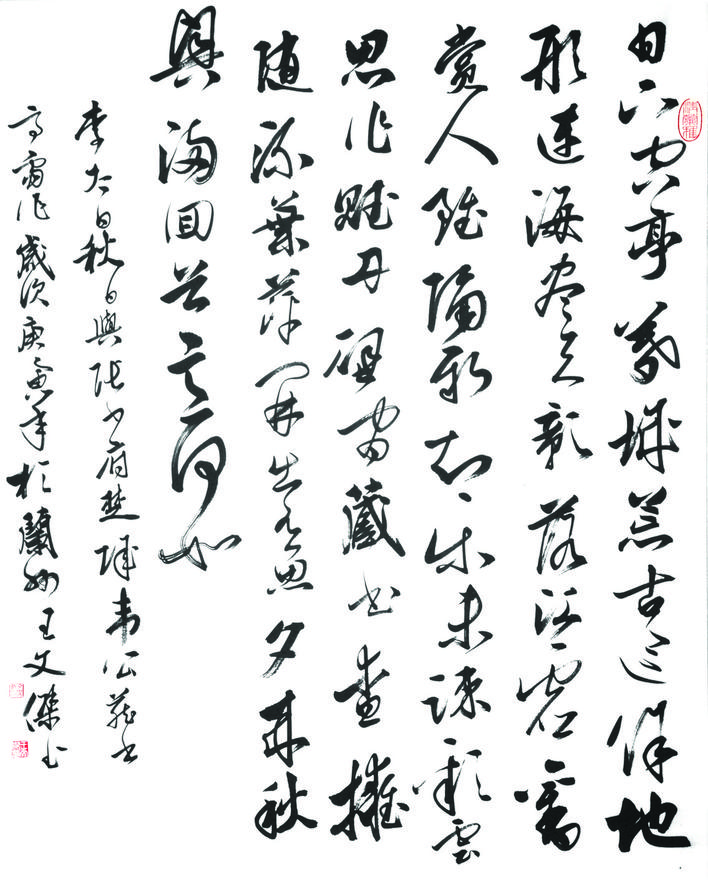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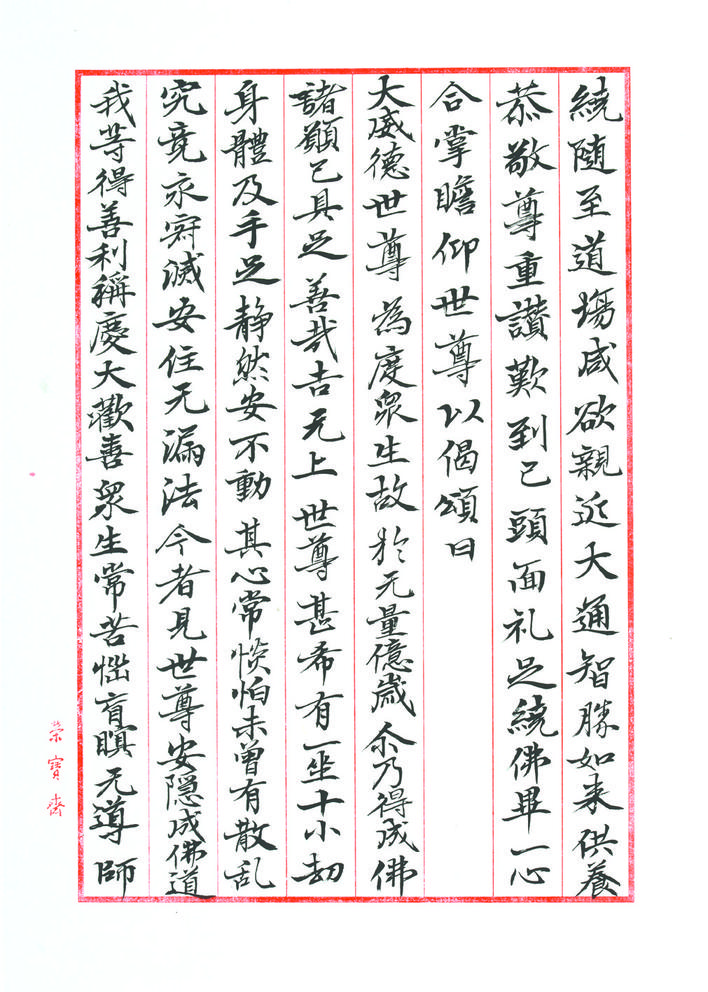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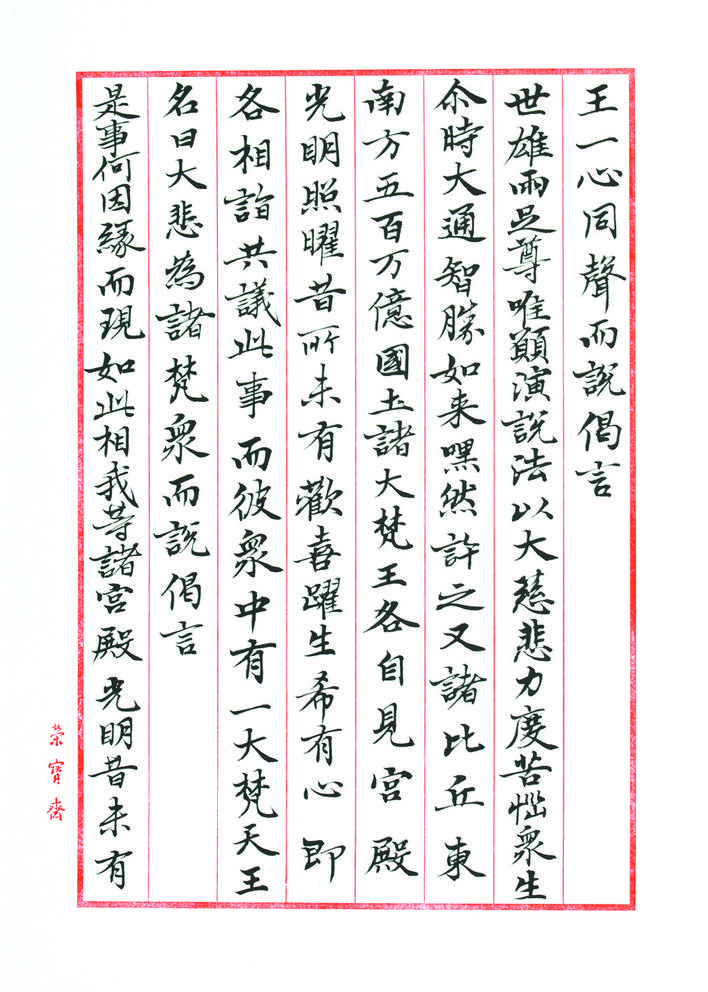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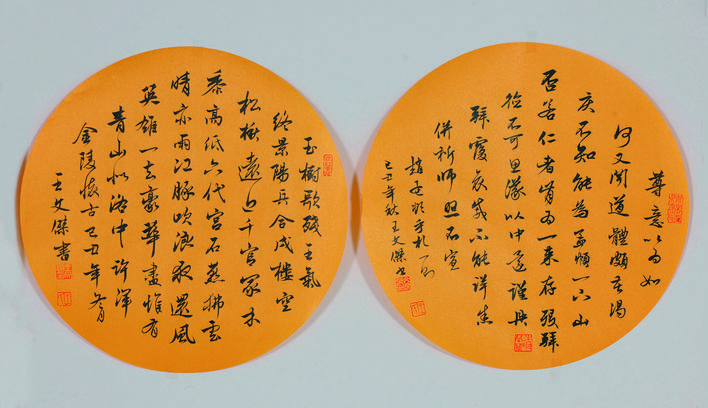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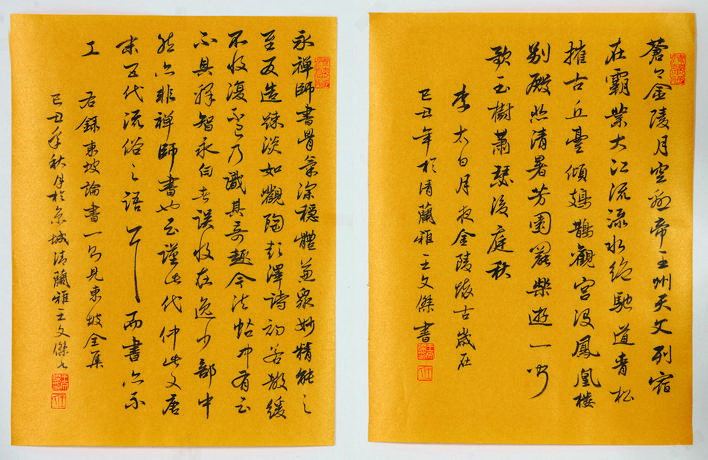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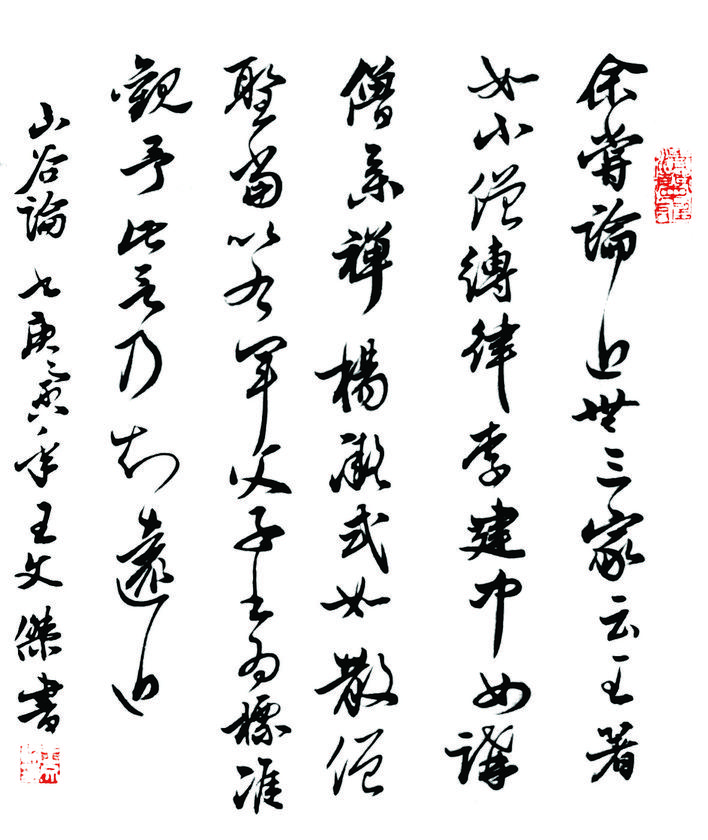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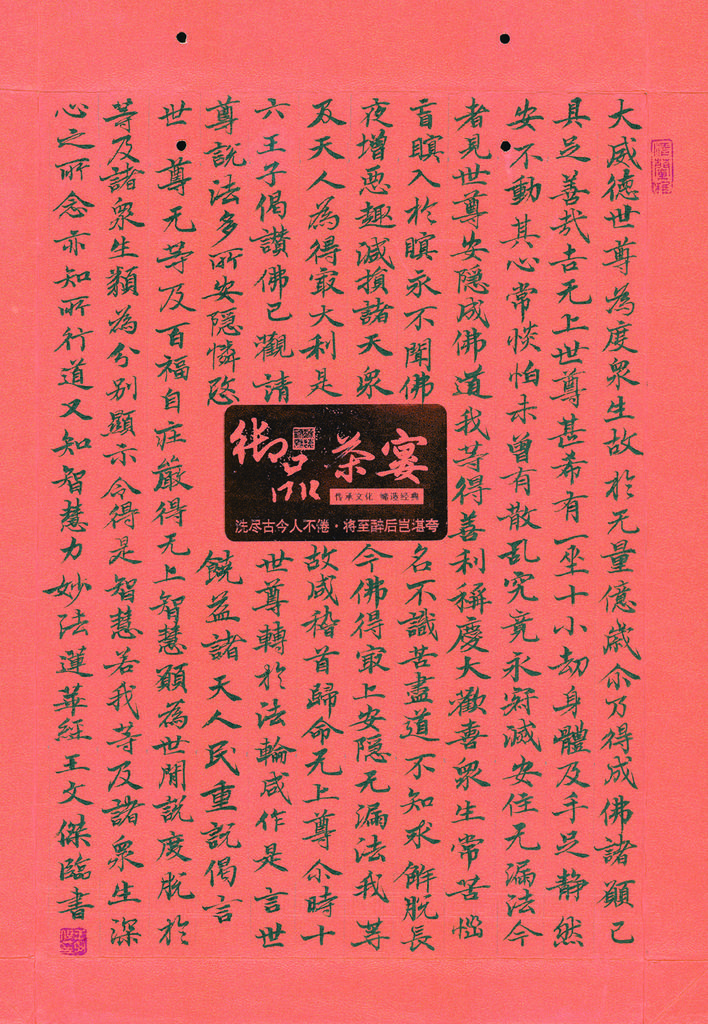
岁月如河,我们每个人都是划舟击水的过客,而我们祖先是一批聪明且极富智慧的过客,他们为后人留下一笔取之不尽、万世不竭的财富——中国汉字。汉字的构成,可谓丰富多彩,别有意味。最近,无意中看到两个字,一个是“忠”,一个是“患”,把这两个字一点点地拆卸开来分别剖析以后,会觉得很有意味。一个“中”字底下加个“心”,上下搭建,成了一个“忠”,其意不言自明;再看看“患”字,本来一个“中”字加个“心”字,恰好构成个“忠”,可偏偏又多个“中”来凑热闹,两个“中”字串起来,把心死死地压在下面,喘不过气来,于是就有了“患”。 如果我们的眼睛不仅仅把透视焦点集中在这两个字的表象上,还会看到隐含在这两个字后面的许多东西。
“忠”,是一种品质。看字解意,不论做人做事,把心摆正了,谓之“忠”,有了一个忠字,才能人有口碑,事有所成。忠,应该成为一个人做人的底色和基调。中国人自古流传下来并且为世世代代看重的“良心观”,强调自我修养净身自责的“良心账”,表明中国人最崇敬的桂冠不是挂在身上,说在嘴上,贴在脑门上,而是悄悄地埋在心里。《论语·阳货》说“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这是患得患失的来历,鲁迅在《两地书》中说过:“既无‘患得患失’的念头,心情也自然安泰”, 很明显,“患”是由心境决定的。有患得患失之念,心情一个样;无患得患失之想,心情又一个样。忠不忠,全在心;患不患,也皆在心。作为一种气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徐而来之,挥之不去,是品格和修养的长期熏陶和积淀。有人遇到欣喜之事时,常常以“祖坟冒青烟了”来形容老辈人的修行德性和后来人得到对应回报的一种因果关系。此是闲话。不过用它来对应一段至理名言还是很贴切的:善乃至宝,一生用之不尽;德为良田,百代耕之不竭。
“忠”是一种修养。中国人经过治国安邦修身齐家实践总结出一条非常有警示作用的排比式格言:治天下先治国,治国先治家,治家先治人,治人先治心。核心就是爱,这个繁体字的“愛”,还是有心字在里面,上面像是人,下面是友,抽去中间的这个“心”,爱也就不复存在了;治人,治理形形色色、参差不等的人,多为社稷培养有一身浩然正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有识有志之士,志是什么?是由士和心组合成,又离不开“心”。治人,还强调德为先,德,凝聚着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成长为人到寿终正寝所应履行的义务和职责,而支撑人这个“德”字半壁江山的底座还是“心”。所以,中国人特别讲究修身。修身,实际上是内敛,内敛就是一种自我修养调节的心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修身也即修心。
“忠”是一种专注。忠字是在警示人们:凡事都要一个中心,不能三心二意。听过一个猎人的故事令人永志不忘:大兴安岭有位老猎人,绰号“神枪”,专打特别名贵的白狐。“千羊之裘,不如一狐之腋”,有人一生都打不到一只白狐。可老猎人几乎每年冬天都有收获,他打的白狐甚至看不出来枪眼还是肚脐眼,以保持白狐的完整美好和与众不同。老猎人年轻时,只身一人,在雪地里一守候就是一个冬天,可有时一个冬天连个白狐的影子也未见到。岁月流失,猎获的白狐寥寥无几,猎人的一头黑发里倒有缕缕银丝渐成“白狐”了。但“神枪”耐得住寂寞,几十年如一日和狡猾而尊贵的白狐较量。宁要完好的狐皮一具,不求破损的烂裘千张,这就是老猎人与普通猎手的区别,职业猎手和业余猎手的区别。人这辈子,只要认认真真干一件事是没有干不好的。条件是:一门心思,专心致志,就是专注。专注是一种厚积薄发的蓄势,是一种博存约取的积累,是与轻浮焦躁全然有别的安宁和沉静,是隐默自守淡定从容的一种修养,是不悔初衷锲而不舍的一种坚守。
“忠”是一种睿智。无论从人文的角度还是从医学原理,有谁能说清楚,脑和心这两个器官的严格界定和绝对区别?可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创造了“心想”的概念,包括源远流长的中医提出“心主神明”,把大脑和心的细微之处加以区别。脑子里装的是记忆创造逻辑推理之类,而心里装的一般是道德伦理做人标准之属。人们在磨砺自己大脑的聪明才智的时候,别忘了一定要给心找个好地方,心眼放正了,脑瓜子里的聪明才智才会有用武之地;心眼子歪了,脑瓜子的聪明智慧就转换成诡计多端了。人这辈子,嗜欲的拘牵、情欲的纠缠、利益的驱动,是脑子里经常无法回避的东西。脑子里的河床常常干涸龟裂,就用心灵纯净的山泉帮助滋润一下;脑子这把锁因为风霜雪雨锈蚀不灵时,就应该启动心灵这把钥匙去把它打开,让心灵这扇窗户透透阳光和新鲜空气。该用脑的时候用脑,该用心的时候用心,让产生良知的心灵和创造智慧的大脑相辅相成,实际上这是中国人的睿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