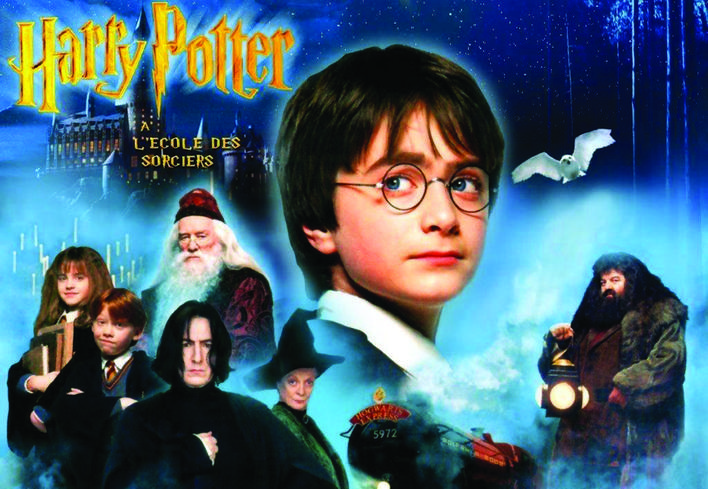
2007年,《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在一大群安保人员的保护下与读者见面,“魔法妈妈”罗琳随即宣布了这一系列终结的消息,不过让全球“哈迷”略感安慰的是他们还有一部电影值得期待。
2011年,哈利、罗恩、赫敏这个“铁三角”组合最后一次演绎了他们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奇幻历程,随着《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大幕落下,这一系列电影以绝对的高票房完美收官。
不管人们对其持何种态度,我们都必须承认,十多年来哈利·波特每每新书出版或是新电影问世必定在全世界掀起追逐的狂潮。在英国,连夜排队的孩子们尖叫着展示有作者亲笔签名的小说;在中国,许多学生花四五个小时购买首映式电影票,还有人不惜“重金”打扮成哈利的模样苦苦等候;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都曾宣称,自己是哈利·波特不折不扣的粉丝。
那个戴着黑框眼镜、手持一根小魔杖的男孩仿若一只有魔力的蝴蝶,每当它微微挥动翅膀,就会在全球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如今,一路十年,哈利·波特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毕业”了,然而与之相伴十年的人们却无法轻易割舍,一个正读高二的孩子不无伤感地说,现在没有了奥尼尔,没有了哈利·波特,没有了变形金刚,我们就这样告别了童年,独自长大。惆怅、无奈、热爱、担忧……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关于哈利·波特的言说会终止吗?
十年初印象:谁的哈利·波特?
2001年,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着手引进“哈利·波特”时,中国的儿童文学市场还鲜见类似的作品,无论对读者还是研究者而言,幻想文学的阅读和创作似乎就是经典童话和民间传说,甚至有人彼时还曾因为创作的童话里屡有鬼怪的痕迹而遭到口诛笔伐。所以在今天,我们似乎更该钦佩《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责任编辑叶显林当年的勇气和眼光。当他从各类媒体的报道中看到J.K.罗琳和她的魔法学校时,即敏感地意识到这会是一部深得孩子们青睐的与众不同的小说,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这部小说此后竟拥有数量庞大的成年人“粉丝”并掀起席卷全球的热浪。他还依稀记得最初的阅读体验:新奇的故事,环环相扣的悬念,跌宕起伏的情节,性格鲜明的人物,以线带面的多维叙述方式。小说新奇的故事和独特的结构与此前的同类题材儿童文学作品大为不同,古老的魔法与现代校园生活结合在一起,西方文化中屡见不鲜的“魔法和巫师”题材以英国现代学校教育模式为支撑,并通过大量真实、有趣的细节吊足了读者胃口。比如画像里的人物不但会动还能相互串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每年一次的“魁地奇世界杯”既有学校运动会的影子又具有飞行的魔幻色彩,负责送信的猫头鹰、专门出售巫师装备的“对角巷”、稀奇古怪的咒语密令……他认为,仅凭这些,眼前的这部小说就一定能获得众多小读者的芳心。他甚至没想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一些出版禁忌,比如西方的魔法能否为中国孩子接受,小说中的死亡、黑暗是不是会引起争议等。
不得不说的是,小说来到中国时它的既定读者群是孩子,这是一本被贴上儿童文学标签的著作。然而从它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之日起,其阅读、讨论的范围就远远超越了儿童文学和少儿读者的范畴。从七八岁的小学生到大学生、上班族,再到六七十岁的“老人家”,都是小说的忠实拥趸。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读者,都对小说倾注了极大热情。自称铁杆“哈迷”的儿童文学作家杨鹏清晰记得刚读到这部小说的激动,“我看到了相似的观念和思路”,超前的创作理念一下子引起了他的共鸣,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文学和奇幻文学的看法,他隐约意识到这部作品肯定会在短时间内大红大紫、雄踞少儿图书畅销榜。
一本为孩子引进的书,不仅开发了少儿读者的阅读市场,还点燃了成年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又具备改编影视作品、电脑游戏,开发系列周边产品的无尽潜力。我们不禁要问,它究竟是谁的哈利·波特?有人说,哈利·波特就像一面镜子,每个人都能透过它看到自己的影子。
对许多孩子来说,他们与哈利·波特的最初相识可能缘于在书店的随意翻捡,或是父母如往常一样夹在一大摞教辅书里抱回来的“课外读物”。山东师范大学附中的王林杰就曾把每本小说都读了20多遍,因为看得太投入被父母收缴过无数次。2001年,这个上小学三年级的男孩在同学的推荐下一口气读完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起初,他完全被惊险刺激、波折横生的情节打动了,深埋在心底的英雄梦被激活,哈利勇敢的战士形象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不断膨胀的勇气和力量。年龄渐长,他在更深入、系统的阅读中得到了新的东西,小说带给他对人生和世界的认识、思考,他着迷于英国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现实,并被主人公的品质所吸引。哈利的勇敢正直,罗恩对朋友的忠诚,赫敏的聪明、勤奋,这些让他懂得,平凡人通过努力能够成功,爱与正义是永远主宰世界的真理,和平与安定时常要以流血和牺牲为代价。他说,哈利他们已经成了自己的老朋友,久未谋面总会心存惦念。
与孩子们相似,那些兼具读者和创作者身份的人们也透过这面镜子看到自己需要的因素。儿童文学作家简平认为,哈利·波特现象又一次验证了优秀文学作品经久不息的魅力,它让人们意识到儿童文学还可以是这样的,奇幻文学也可以有另一种面貌。从创作的角度出发,对他触动最深的是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悲悯情怀和历史厚重感,作家不可远离生活与现实扎进书斋凭空创作,即使是奇幻文学。罗琳的经历告诉人们,想象力不是在天上飞来飞去那么简单,想象要有现实的根基,融入作家对生活独特的观察和体悟。
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都有这样一个最直观的印象:哈利·波特不同于以往读到的奇幻文学作品,甚至不能将其简单定义为“儿童文学作品”。这种有趣的现象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文学创作和阅读的感受,以“哈利·波特”为代表的这类儿童文学作品是成人和孩子可以一起欣赏的,随着读者年龄、阅历的增长、积累,他们总能从中不断咀嚼出新的味道。
十年若只如初见
在各大搜索引擎上搜索“哈利·波特十年”的词条,我们会看到各大媒体精心设计的专题回顾栏目,其中囊括了人物、咒语、器物、情境及经典瞬间的归纳与陈述,而网民撰写的各类文章更是不计其数。新世纪以来,似乎很难有一部小说或电影得以持久地享受这样高规格的待遇,当然关于哈利·波特的质疑之声也一直不绝于耳,只是这些争议在某种程度上又使其得到更多关注。美国国家图书协会举办的禁书周曾连续十年把哈利·波特图书列为“禁书”,原因是其中包含“超自然主义”、“魔鬼内容”、“暴力”和“反家庭”的思想。在欢呼与咒骂中,哈利从一个11岁的男孩长成17岁的少年,这一形象所拥有的持久生命力值得人们深思。“哈利·波特”系列用十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奇迹。
200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林品用45000字的篇幅撰写了《作为现代性寓言的后童话——论〈哈利·波特〉》作为本科毕业论文;今年8月5日,“哈7”上映第二天,他一身哈利着装出现在影院的照片爆红网络。他清楚小说、电影的每个细节,并对罗琳的才华表现出敬仰之情。如果你不经意间抹黑了哈利·波特或是叙述不够准确,他会迅速纠正并反驳。
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语言,每个悬念都有可解的原因,情节的戏剧性一浪高过一浪,小说与电影紧密而有规律的对接,时尚文化与商业操作完美融合。叶显林认为,“哈利·波特”的流行有其独特而不可复制的文化基础。在国外,它诞生于魔法题材的复兴阶段,此前科幻题材作品流行多年,已渐式微;在国内,情势也大体如此。魔法题材在西方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其“复兴”也最有文化根基,罗琳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一点,并且推陈出新。在国内,对西方文化多年来的弘扬和对西方文学著作的译介使许多读者对西方魔法并不陌生,《魔戒》《纳尼亚传奇》等的流传使魔幻题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受众基础。
除了恰当的推出时机,更重要的当然是作品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吸引力。儿童文学评论家王泉根说,“哈利·波特”把传统题材与现代小说创作技巧融为一体,古已有之的魔法题材在现代校园中展开,小巫师们虽具法力但也面临真实的困难。啃下厚厚一摞材料准备考试,因观点不同和老师发生冲突,男女同学间滋长的美好恋情……尽管很魔幻,但却很真实。再者,罗琳从尊重孩子的角度出发,在前几部作品中以儿童的视角结构故事,积极为孩子争取生存权、教育权和发展权,她相信儿童拥有潜在的巨大能量,这些都会鼓励少儿读者并使他们产生共鸣。此外,简平则认为,“哈利·波特”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是吸引孩子的重要因素,孩子们拥有改变自己、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故事将现实世界的黑暗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并通过合理的方式加以引导,避免了常见的“主题先行”的情况,潜移默化地引导孩子去理解善良、友谊、爱和正义。他们在故事里学会如何对待朋友及身边的事情,懂得人性的复杂,而这都是他们无法回避的成长经验。
除此,“哈利·波特”的持久生命力还在于它蕴藏深刻的文化内涵,包括人类对生存格局、生存方式的反思以及向原始文化、巫术文化寻找精神资源的求索。王泉根认为,不能简单将其巨大、持久的影响力归结为流行文化和市场运营的融合。长达7部的“哈利·波特”是“新世纪以来的一部大书”,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困境的深刻反思,永无止境地开发欲望同地球有限的资源形成尖锐的矛盾,自文艺复兴以来盛行的理性思维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罗琳从原始思维中寻找精神资源,希求回归本真、回到原点。较早研究“哈利·波特”的学者叶舒宪曾指出,它的风靡全球表明新的生态自然观正取代人类中心主义;麻瓜世界与魔幻世界的对立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批判,针对理性的异化和人类的“过度增长癖”开出猛药:用复归巫术幻想的万物有灵世界的方式来克服人对物欲的痴迷,来对抗市场魔鬼的力量。
延续十年的“最后一课”
印有“一切都结束了”的《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的巨型海报标志着一个童年时代的终结,成为一代人告别青春少年的时刻。有“哈迷”说,他相信这世界上至少存在一种咒语——闪回咒,每当触到与之有关的微小片段,记忆便闪回至那个魔幻世界。“哈利·波特”进入中国的十年,给中国的儿童文学带来了诸多有价值的经验并引起启发性的思考。
从新世纪初这个系列在儿童文学市场中“一枝独秀”,到随后一系列以“魔幻”、“奇幻”、“玄幻”之名出现的大量作品,“哈利·波特”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幻想文学的创作、阅读及出版。叶显林回忆到,在这个系列刚进入中国红极一时的阶段,他每天都能收到大量魔幻题材投稿,除了个别文学性、可读性较高的作品外,许多小说的介绍都是“超越哈利·波特”等字样,作品主人公名字及作品背景不中不洋。许多作者认为给主人公取一个外国名字就是国际化了,殊不知从异邦捡拾那些自己消化不了的东西,生编硬造只能拼凑出神不似形也不似的东西。发展我们自己的幻想文学,还得回归本源,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对于密切相关的阅读而言,它在一段时间内“拯救”了传统阅读,将世界各地的读者特别是小读者的目光又吸引到了书本上。它改变了读者的传统阅读习惯,培养了更广泛的阅读兴趣。
除了创作与阅读,“哈利·波特”系列在出版运营上的成功恐怕是很多出版人最津津乐道的案例,简平将其概括为 “一揽子计划”的文化产业链。创作伊始,成熟的出版商已经开始酝酿整个流程,精心策划每一个关口、环节,小说版权的多语种交易及时、顺利,强大的出版发行平台,电影与小说紧密而恰当的衔接,各种媒体的大力造势都为作品营造了氛围,提高了认知度。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但借鉴并不意味着复制,试图复制“哈利·波特”的成功无疑是愚蠢的。叶显林认为每部文学作品的个体差异很大,“哈利·波特”系列的成功是诸多偶然因素凝结发力的结果,这可能是其他图书所不具备的。一味复制、模仿难以获得真正的生命力,但“哈利·波特”系列的成功至少让出版界意识到一本书可以多么畅销,可以拥有多么持久的影响力。当然,儿童文学界的同行们在这十年中也越来越意识到,“哈利·波特”的成功,固然有其超拔的想象力,但正如作家汤素兰所说,“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英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中,有着一个民族深刻的心理和文化印记,这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