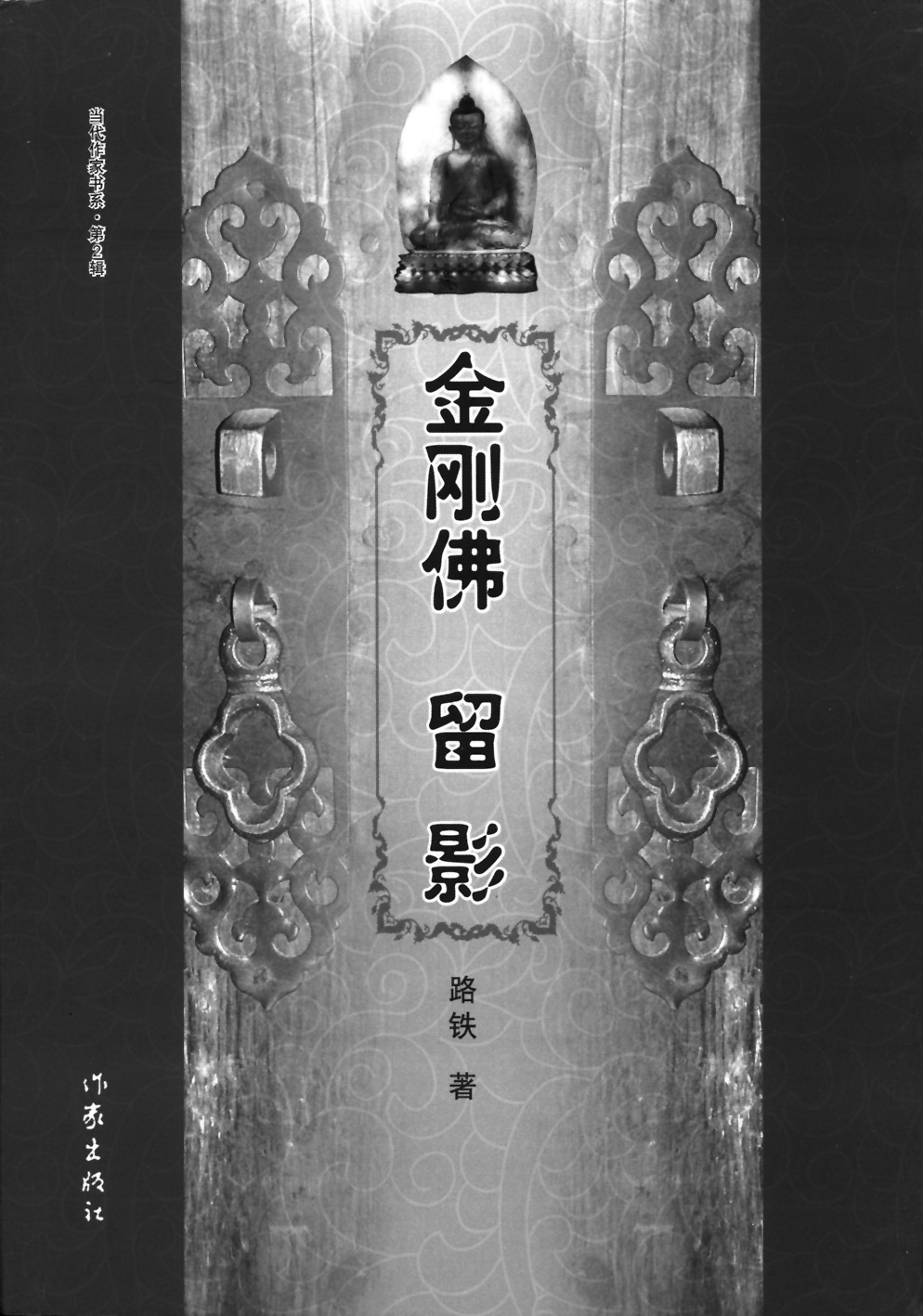
《留影》是路铁的第二部知青题材力作。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正本清源的社会责任和爱众亲仁的道义担当,让良知重返那个“广阔天地”,重温那个“大有作为”时代,探望当年知青心灵,抚摩当年知青脉搏,从而给那段使共和国伤筋动骨的历史保留一份清晰可靠的CT造影。这既是对历史的交代,也是对千千万万当年知青的一种深情致意和慰藉。
路铁曾被委派随学生下乡,教师身份一变而为“带队干部”,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滚泥巴炼红心。因此,对那个作为“文革”元素之一,曾席卷神州大地搅动千万家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切身感受,也因此使他的笔触所到便给人以入木三分之感。
腊月三十这天,19名女生和男生起程下乡,学校敲锣打鼓热烈欢送,大家高呼口号“扎根农村干革命”,然而来送行的家人却是悲悲戚戚的样子,更有人“竟背过脸不住地擦泪”。下乡第二天,一道来落户的索问道和索淑姿兄妹为重病硬“熬着”的爸爸能否挺过这个寒冬而忧心如焚。清明节到了,梅琴书梦见在文革中惨死的妈妈,“一边在本子上写,一边流泪”,这写给冥冥中妈妈的信字字撕心裂肺。冉嘉“买来一包点心和烧纸,要像社员祭祀亲人一样来祭祀爸爸”,她的爸爸在“文革”中被逼自杀。知青们来到山村首先感到的是,贫下中农似乎并不注重他们的知青身份,而是把他们当做离开父母的孩子予以关照。他们从贫下中农慈善的面孔上读到了使人温暖的四个字:父老乡亲。闻过喜是个积极向上充满革命激情的女孩,而与她同行的男知青古作圣喜欢发牢骚,说些不合时宜的话。两人一路唇枪舌剑争论不休。夜幕中路旁不知什么怪物“哇哇”叫了两声,闻过喜被吓得一声惊叫,跳过来一头扎进古作圣的怀里,双手紧紧抱住古作圣。“她刚才还是那么胆壮气豪地教导古作圣,这时,竟似乎一点底气也没有了”。此时此刻,二人的两个生命体本能的感到了对方的真实存在。这样的情节还有很多。
与其说路铁的匠心在于设置这些表达人性之美,既平常又典型、既生动又可信的细节,再现了知青的真实生活,不如说是一个有着相当思想深度和文学识见的作家的拳拳心意。可以说,小说处处昭然在目的是人性光芒。人性这个东西,几十年来东躲西藏,被四面伏击,“文革”更是对人性的全面围剿。然而人性从各个角落艰难突围,依然和人同存。
《留影》还告诉读者,当年知青并非所有人都是“集体无意识”,在被上山下乡的风暴裹挟、鼓动之中,也不乏敢于独立思考、颇有理性的头脑。到县城看望重伤的麻名立回来,古作圣在路边小摊买到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和《朱柏庐治家格言》这些被当做“四旧”的几本小书。这是那时在偏僻农村才偶尔出现的文化景观。接下来,男女知青在农事之余竟然争相传抄,偷吃这些文化禁果。还有一种书可以明目张胆地宣布“想读它”而不怕惹麻烦,那便是过去学过的课本。上山下乡运动按照“文革”整个战略计划,实现了在校学生与书本的彻底切割。但政治说教和红宝书诵经般的背唱,救赎不了精神的空虚和大脑的荒凉,于是又开始和书本藕断丝连。这说明群氓式的癫狂过后理性开始回归了。
很有舞蹈天赋的女知青麻名立在劳动中被大石头砸断了腿,大家对她深为同情和惋惜。女知青况今更是石破天惊地诘问:“谁给断的呢?是那个大石头吗?”
别人听着都有点害怕,没人敢接她的话,她自己接着说道:“她就不应该下乡!”况今在写给自己私下看的从不示人的日记中,毫不掩饰地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大胆地提出质疑。在非理性的东西以超强之势压倒一切的背景下,敢于理性思考、大胆发声,无疑是罪不容恕的异类,也因此导致了她后来的悲剧下场。
仅仅提出人性和理性,并不能概括这部小说丰富的思想含量。但对历史理性反思也许最值得肯定。
这部小说叙事简练、流畅,情节递进快捷,跌宕有致,没有那种拖泥带水令人腻歪的文字。人物对话准确、到位,突显人物个性的同时并能借以推动情节发展,是语言的另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