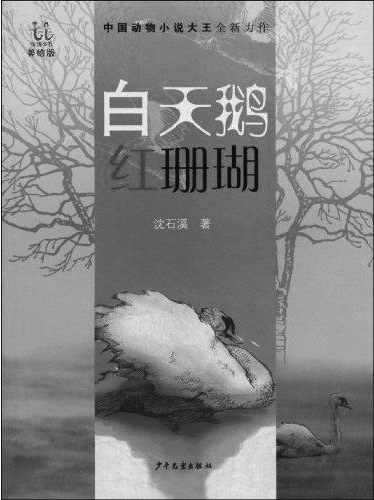
沈石溪的《白天鹅红珊瑚》获得了第24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这是用三个独立的中篇连缀起一部完整描写白天鹅生活的长篇小说。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历来得到研究者们的密切关注。沈石溪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小说似应具备如下要素:一是严格按照动物特性来规范所描写角色的行为;二是深入动物角色的内心世界,把握住让读者可信的心理特点;三是作品中的动物主角不应当是类型化的而应当是个性化的,应着力反映动物主角的性格命运;四是作品思想内涵应是艺术折射而不应当是类比或象征人类社会的某些习俗”(沈石溪:《漫议动物小说》)。在《白天鹅红珊瑚》中,沈石溪实践自己的“动物小说观”,以“专门研究鸟类”的“动物学家”的视角展开叙述,并努力以“动物特性来规范所描写角色的行为”。
《红弟一生的七次冒险》一节选择了天鹅一生中七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片段,包括出生、死亡、迁徙、爱情等等。沈石溪把天鹅一生中所有可能遭遇的磨难,和可能享受的美好时光,都最大程度地浓缩、集中到了这七个生命片段之中,各种偶然性与必然性交织在一起。在作者的笔下,每一次冒险都是红弟生命中的一次挑战,也成了新生的机会。无论是“在最后一秒钟啄破坚硬的蛋壳,并从乌鸦嘴里侥幸脱险”,还是从沼泽中救出深陷泥潭的心爱的彩云,抑或让自己的生命在与毒蛇的搏斗中谢幕,为心爱的妻子报仇,为天鹅群剪除生存障碍,红弟都幸运地从命运的缝隙中胜出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在《四只哨兵天鹅的生命档案》里,白肚兜、半点红、蓝翅儿、歪歪脖四只天鹅成为哨兵的原因各有不同。作为天鹅身上一种独特的习性,失去了繁殖能力的“老雌鹅”为鹅群担当哨兵的角色。这四只进入作者叙述的啸天鹅,它们各自成为哨兵的缘故,和作为哨兵殉职的经过、细节,都是相当“个性化”的,体现了作者对动物主角的性格命运把握,也是作者着力叙述的内容。这个过程中有时候又恰恰暗含了某种叙述的巧合。例如,白肚兜因为“丈夫”芝麻雄被“寡妇”小妖妖勾引走了,而走向生命最后一站的哨兵岗位,但最后却是为了救芝麻雄和小妖妖一家而殉职。半点红、蓝翅儿则是因为站岗过程中与天敌的积怨,而最终丧生。歪歪脖和红珊瑚虽然一个丑一个美,在作者笔下,却都与“母性的强烈本能”连在一起,这种“母性的强烈本能”也成为叙事的动力来源。歪歪脖“苦苦追求”、“梦牵魂萦”的爱情,在它用自己的生命挽救首领之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实现了。“美”是始终贯穿在对红珊瑚的描写中的一个关键词,最终也成为作者对它的褒奖。
任何的动物叙事中其实都包含着作者的价值判断、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或者是象征意义,只是内容不同,寄寓的方式不同。《白天鹅红珊瑚》里,叙事的缝隙中也总是穿插、伴随着叙述者“我”的理解和看法。这样的揣测将叙述者“我”的视角明显脱离于动物心理的拟写,不易干扰对动物自然属性、动物行为的描写,可以避免让动物有过于丰富、复杂、近乎于人类的心理活动,而让动物角色的内心世界更可能具有让读者可信的心理特点,同时叙述者“我”的视角又是可以表达作者自身的情感、倾向、态度的一种方式。例如:“我很难理解白肚兜为何要扑撞黑森森的枪口,芝麻雄和小妖妖是它不共戴天的仇敌,何苦为救仇敌而让自己粉身碎骨呢?或许只有这样一种解释,啸天鹅头脑简单,只会直线思维,当履行哨兵职责时,根本就不会想到自己所要保护的对象与自己有何种恩怨纠葛,缺乏将私仇和公职联系起来通盘考虑问题的能力。它们真的没有人那么聪明。”正如在对动物习性的了解中,在尽量贴近动物习性的文学叙述、文学想象中,对于其中所透露出的真善美的价值的赞美和肯定,是沈石溪动物小说中明显的价值倾向。在《白天鹅红珊瑚》里更是如此,“如果非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天鹅,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选择‘美’这个字……写天鹅不写美,就好像射击跑靶一样,总觉得没击中目标”(沈石溪:《白天鹅的生命世界》)。穿插在天鹅的故事中的“我”的感喟、思索、体悟,让我们看到了沈石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价值和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