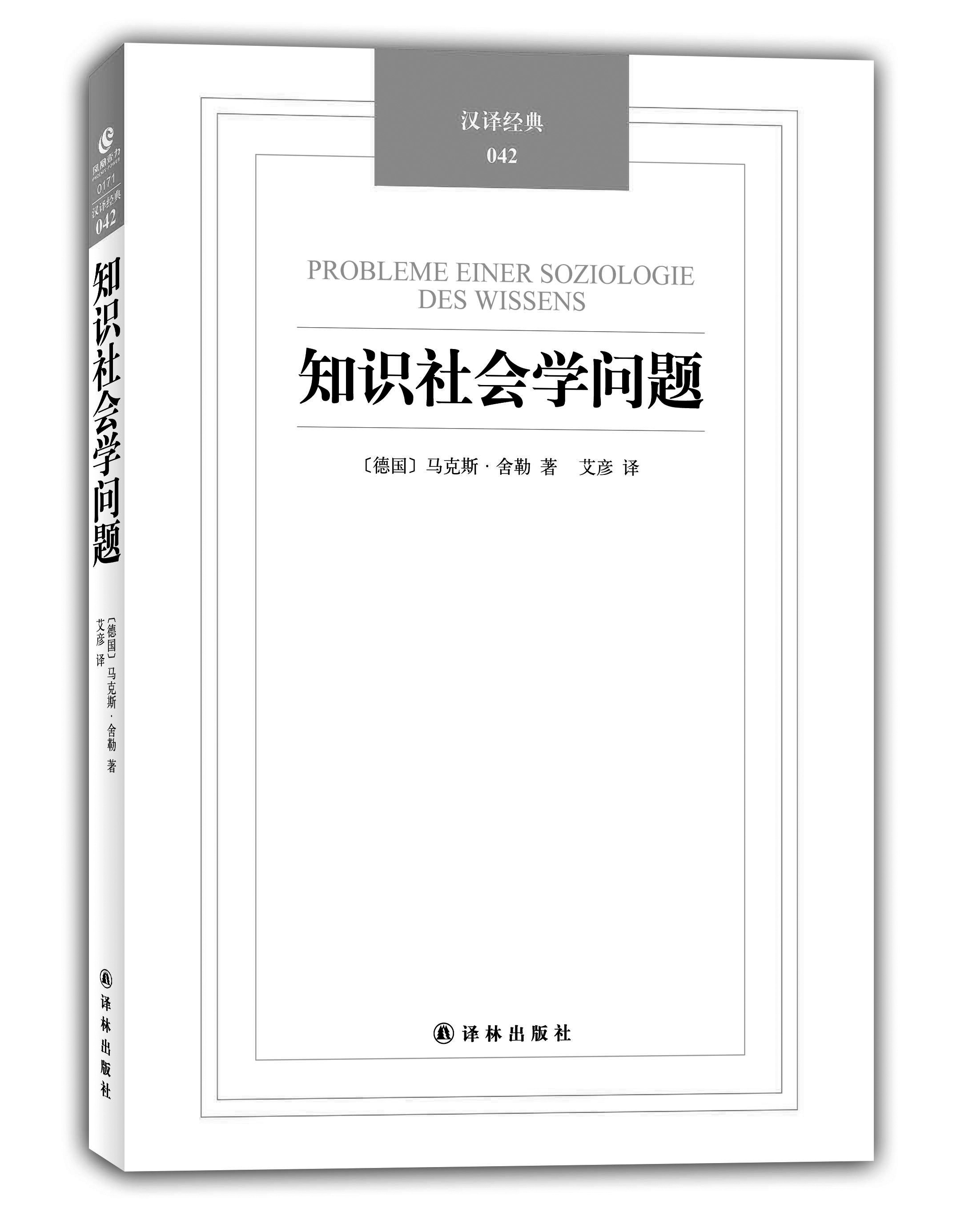
一位涉猎过西方知识社会学的学界友人,在得知我翻译舍勒这部《知识社会学问题》时曾惊讶地对我说:“你翻译这部著作只是为自己看的吧?它层次太高、太阳春白雪了,国内社会学界有几个人能读懂?!”
其实在现代西方现象学哲学界,舍勒已经被公认为学术影响仅次于E.胡塞尔的第二位学术大师。而我认为舍勒本书所包含的思想内容为“以人为中心的现象学知识社会学”,都是从社会哲学的高度对人类社会之不同方面的关注及其结果。
马克斯·舍勒1874年8月22日生于德国慕尼黑市的一个领地管理员家庭。舍勒在深入学习哲学、心理学和医学的同时,还广泛涉猎包括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在内的现代西方多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大学三年级,他以论文《对逻辑原则与伦理原则之关系的确定》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年仅23岁。
从根本上说,舍勒之所以一开始便集中关注人及其地位和命运,既是由他的社会背景和知识文化背景导致的,更是由他本人对这种背景的切身体验导致的。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高度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实际上已经把它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危害非常清晰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就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对这种局面做出的反应而言,无论先于舍勒而成为社会哲学大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舍勒学术思想直接来源之一的新康德学派、奥古斯特·孔德和费迪南·滕尼斯,还是与舍勒几乎同时的E.胡塞尔、W.詹姆斯、R.G.柯林伍德、M.韦伯等在当时已经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分别从特定的学术立场,做出了自己对这种“危机”的独特回应。正是由这些回应组成的学术思想氛围,构成了使舍勒成长为杰出的现象学社会哲学家的学术思想背景。
当然,即使同样是对这种危机做出“回应”,舍勒也自有其独特之处——他所集中关注的既不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马克思),不是宗教伦理、理性化和官僚制(韦伯),更不单纯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建构和式微(特勒尔奇),而是与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密切关联的世界价值秩序、社会精神特质和主体的体验结构。舍勒最终得以完成其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创新,就是现象学及其研究方法,成为现代德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现代西方学术界的大思想家之一。舍勒一系列重要著作有《论自我认识的偶像》《同情的本质和形式》《现代道德建构中的怨恨》《德意志人仇恨的起因》《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等。
舍勒虽以人为中心来关注时代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但他绝不是一个肤浅的、就事论事的“时事评论家”,而是深刻地洞察危机的方方面面及其背后的形而上学根基。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是“怨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危机”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同时体现在现代人的社会精神特质和主观体验结构方面,后者的转变具有更加根本的重要意义,它表现为人对世界的情感性价值评价态度由“爱”转变成了“怨恨”:“世界不再是真实的和有机的‘家园’,不再是爱和沉思的对象,而是变成了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
在舍勒看来,以资本主义类型的人为代表的现代人,都是心中充满了怨恨的市民。他们追求最安稳的生活而又必须面对充满恐惧的现实,由于人对人的根本不信任所导致的内心的形而上的无依赖感,而形成怨恨态度并投身于外部事务之中的,而这种倾向和做法最终导致他们破坏了以往形成的所有各种团结共同体及其人际关系的情感纽带。这样一来,他们便只有通过外在的利益和法律、契约才能结合起来。舍勒认为,从内心中缺少形而上的依赖感这种根本意义上说,不仅资本占有者具有这种怨恨情绪,作为非资本占有者的无产阶级也同样具有这种怨恨情绪。所以,舍勒不认为通过社会革命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他认为这样的运动是无法根本改变上述基本价值观和主观体验结构的。
不过,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是否用“怨恨”一词就可以囊括无遗了呢?是否只是到了13世纪末以后,西方现代人内心的形而上无依赖感才开始逐渐形成?我们无法一一具体探讨和论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简单地回答:“不。”当然,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舍勒不认为社会变革可以改变资本主义的观点,只是出于特定学术观点的不同。
那么,舍勒是基于何种世界观而得出“怨恨”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呢?在舍勒看来,世界的现实是在分别由“内驱力”和直接作为现象而存在的世界的“抵制”组成的两极之间,在这两者存在的张力之中给定的。我们有关这种世界现实的经验——其中既包含诸如爱、恨的情感体验,也包括对于这个世界的各种认识——也都是这样形成和给定的。
在他看来,人会因为其内驱力得不到实现和满足而感到痛苦,包括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乃至宗教思维在内的全部思维的任务,就是以某种方式消灭这种痛苦。
为了克服这种痛苦,人类在思考和行动过程中采用的各种态度和技术主要有哪些类型呢?其中的一种技术类型我们可以称为通过从理智的角度认识、控制和征服外部客观世界而满足和实现“内驱力”的技术,舍勒显然对这种技术评价不高。另一种技术主要是通过包括东方的佛教和道教在内的东方神秘主义,以及通过西方的基督教体现出来的,这是一种试图通过遏制或者解除“内驱力”而尽可能取消世界的相应“抵制”的与不抵抗有关的心理技术。舍勒认为,它并不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技术,而是一种通过使人保持谦恭态度,通过取消“内驱力”及与之相应的对“抵制”的感知过程,而使这个世界本真地存在,从而使人获得有关世界的各种本质的洞见的技术。
舍勒从独特而又深刻的理论角度揭示了东方和西方各自的哲学和宗教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并且因此而表明了他本人对工业文明“危机”之根源的诊断:在他看来,危机就是由于西方人在克服“痛苦”的过程中,从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出发通过运用自然科学技术去控制和征服外部世界而使自己的“内驱力”得到实现和满足,从而既在客观上把外部世界形式化而抽掉了存在于其中的全部本质和意义,又在主观上完全忽略对这种“痛苦”的理解,使处于团结共同体之中的个体之亲情和友情关系纽带全部分崩离析,才最终出现的。因此,要想消除这种“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西方现代人所具有的这种基本倾向和观念,重新建构已经被“颠覆”的以爱为基点和实质核心的价值秩序。
舍勒通过对人的道德活动进行连贯而彻底的现象学分析指出,“内驱力”在不断生成、不断走向日益精神化的过程中,始终都是努力按照某种绝对的价值等级体系(即爱的秩序)来实现自身的,这五种价值等级是:(1)可感觉的价值:包括从令人愉快的价值到令人痛苦的价值的领域。(2)功利性价值:包括实践性价值、效用性价值,以及经济性价值在内的领域。(3)生命价值:包括从高贵的生命价值到低级粗俗的生命价值在内的领域。(4)精神价值:包括审美价值(美丑)、公正价值(对错),以及对于真理的纯粹认识的价值在内的领域。(5)绝对价值;包括圣者价值和非圣者价值在内的价值领域。
舍勒认为,价值等级体系的秩序是绝对的和固定不变的:价值越高级,它就越全面,它对物品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它的内容也就越不易被量化;同时,价值越高级,它所导致的实现也就持续时间越久、越深刻。每一个价值等级,都具有与之相对应的理想群体类型:(1)与“可感觉的价值”相对应的是“大众”或者“人群”。(2)与“功利性价值”相对应的,是通过各种制度关系和契约关系表现出来的“社会”。(3)与“生命价值”相对应的,是通过血缘关系凝聚在一起,并且通过家庭、部落以及民族表现出来的“生活共同体”。(4)与“精神价值”相对应的,是由那些追求真理、美以及正义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化共同体”。(5)而与“绝对价值”相对应的,则是由圣者和信徒组成的“爱的共同体”即“教会共同体”。
舍勒认为,由于推崇个体的独立自主,现代西方社会实际上仍处于比较低级的价值等级之上。应当按照这种绝对的价值等级体系及其相应的理想共同体类型,来改造西方现代人的动机结构和情感体验结构,从而克服工业文明之“危机”。
在我看来,虽然舍勒这种通过揭示绝对的价值等级体系来回应上述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做法不乏理想化色彩,但却是极具独创性和发人深省的。我们不会全盘接受他的结论,但在已经跨入新的21世纪之际,在直接面对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主导的人类文明的方向和出路问题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无视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做出的回应。
(《知识社会学问题》,(德)马克斯·舍勒著,译林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