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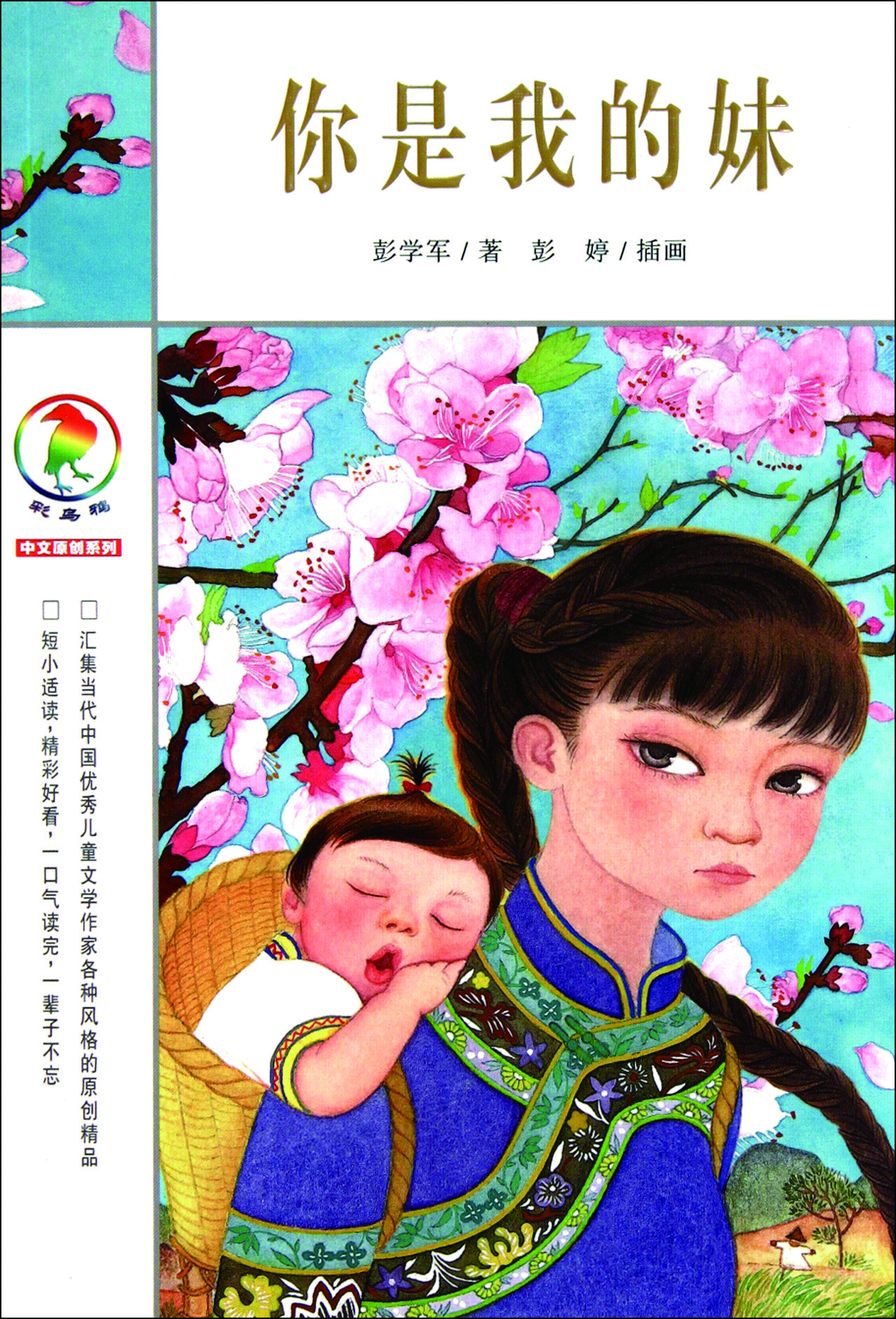


法兰克福书展上,杨红樱作品德文介绍


2012年1月,《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文平装版问世,主编高洪波、王泉根在这套书的序言中指出,开放的中国需要融入世界,世界需要认识中国。别具特色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需要走向世界,世界不同肤色的儿童也需要认识和感受中国儿童文学。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童书版权输出,事关国家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因此,如何壮大我国童书出口市场,也就成了童书业界的重要任务。
版权贸易的巨大逆差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少儿出版是目前版权交易非常活跃的出版领域,但是和成人文学出版一样,版权交易上的巨大“逆差”一直是少儿出版界的重要话题,虽然近些年随着少儿出版的发展,富有远见的少儿社在努力推介优质图书“走出去”,但优秀原创作品真正融入世界范围内的阅读依旧任重道远。
从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据来看,报送2009年度少儿类图书选题的出版社共计269家,其中专业少儿社30家,非专业社239家,少儿类图书在整体新书市场与各大出版社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就是说,近300家出版社出版了上万种儿童图书,但能够输出版权仅有十几家,而且输出的品种较为单一,输出的数量也不大。中国版协副主席海飞表示,中国缺乏自己的国际品牌,既走不出国门,又难以与世界精品抗衡。改革开放以来,少儿读物引进多、输出少,贸易逆差一度达到48∶1,真正进入国际英文出版主流的微乎其微。
回顾中国童书出版市场的版权输出,我们需要将视线放到21世纪初我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2001年12月,我国对外国资本开放了全国各地所有图书零售市场。中国童书出版市场的版权输出意识一直较为强烈,输出品种也较为可观,但输出方向多为港澳台等地区,在版权贸易上,还不能与欧美发达国家平等对话,引进的多,输出的少,逆差巨大。据有关部门统计,2002年,中国引进版权10235种,输出版权1297种。2004年 9 月,第1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版权输出2494项,比过去有了较多增长,但与版权引进5583项相比,反差依然惊人。
在2006年第1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版权输出合同(包含意向)共计达成1096项,比前一年增长98.2%;版权引进合同为891项,比前一年增长6.7%,首次实现了现场签约图书版权贸易顺差。2011年第18届图博会期间,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逾2000家中外出版单位展览展示了20万种精品图书,举办近千场文化交流活动。经统计,此次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953项,比去年增长24.13%。其中,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1652项,比去年同期增长17%,达成引进协议1301项,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1.3。虽然引进与输出的比例在缩小,但去年图博会期间,国内童书出版商正式公布的签约项目仅有两项。一个是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的科学童话绘本版权输出至韩国;一个是“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和“阳光姐姐”伍美珍的4部作品与英、俄、德等8国出版商签约。
海飞曾撰文称,我国童书引进输出的比例,从2000年的9∶1,提升到2009年的7∶3。从产业成长看,童书出版年产值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2007年增长35.66%,2008年增长17.43%,2009年增长18.36%,童书出版已经成为拉动和提升我国出版业整体增长的一支重要的“领涨”力量。但是如果“没有基于内容创新的原创儿童文学出版的极大繁荣,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和中国少儿出版‘走出去’都很难实现”。海飞强调: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要通过版权输出来实现,版权输出的实质是品牌和知识产权的输出,而品牌和知识产权只能在雄厚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出版的基础上产生。
中国一向习惯于引进欧美的童书品牌,而欧美日等出版强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儿童文学图书的版权输出大国,就在于这些国家许多少儿出版社都拥有自己的品牌图书和品牌形象,比如《长袜子皮皮》《丁丁历险记》《蓝精灵》《机器猫》等等。在精心打造品牌图书和品牌形象的基础上,版权输出成为这些出版社收入的重要来源。反观我们的少儿出版,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的品牌图书和品牌形象还很少,少数品牌图书和形象的产业化程度也很低,出版赢利模式单一、陈旧,缺乏国际上成熟的童书“一条龙”赢利模式,像“变形金刚”那样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的商品更不多见。
出版人如果仅仅满足于把别人的东西引进来,做“加工商”,而不是致力于内容的发现、策划、升华,加强原创儿童文学图书的出版,做“制造商”,那么我们版权的引进和输出的比例即使缩小,意义也不会很大。
原因复杂,亟需突破
之所以呈现出这种差距,并非“一日之寒”。
首先是国外读者对中国的了解甚少,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事实。“中国话题”是国际书业界非常关注的出版资源,其兴奋点不仅在于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与生活,还有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乃至激发异域孩子们想象力的中国儿童图书。但总体上来说,引进中国图书的意向,对国外出版人,尤其是欧美的出版人来说,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强烈,重要的原因正如国外展商所说,只有那些选定中国作为文化旅游地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希望开拓中国市场的企业家,才对中国图书有更为浓厚的兴趣,一般读者对中国并不了解。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中国之于他们,仍然是蒙着面纱的神秘国度。因此,向西方普通读者传达中国信息,更应该加大“拓荒”的力度。对国外书业界来说,读者多寡是他们决定引进与否的根本因素。
其次,即便是传达给西方读者有限的中国信息,也并非来自中国作者这一原创者的渠道,而是经由第三方“转译”或“意译”。以俄罗斯为例,从2001年到2006年,俄罗斯翻译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图书,共1274种,但这些图书真正为中国作者所写的寥寥无几,它们要么由非中国人所写,要么是近些年到俄罗斯工作或移民到俄罗斯的非专业人士所写。但正是这些学术态度并不严谨的人,有着诠释中国的话语权,成为俄罗斯的流行作家。俄罗斯文化人在演讲中提到的著名“中国话题”作者,我们在国内几乎都不闻其名。
第三,“走出去”的期待过高,甚至超过了对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韩、东南亚国家等华语文化圈的重视程度。我们应该看到,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例的变迁,从1996年以来的10:1到2005年的7:1,以及此次展览会的8:10,作出最大贡献的恰恰是华语文化圈,是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和韩国、日本等国家,接受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图书版权,它们是我们“走出去”取得成绩的前方阵地,也是进一步走入欧美国家的重要桥梁。
第四,国内童书的创作理念应该得到提升,编辑、出版人的出版理念应该以儿童为本位,关注儿童本身,同时合理调整出版格局。有些国内出版社的绘本尽管装帧精美,造价不菲,但考察、洽谈的国外出版商却很少。这些新出版的绘本,在画风上带有极重的模仿痕迹,故事也几乎大同小异。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方卫平认为,国内童书自身的创作理念确实需要提升。“国外童书中的童趣、想象力、游戏性、幽默感,都值得创作者和出版人琢磨。我们的童书太复杂、太做作、太说教了,缺乏在天真、单纯的故事中展现深刻主题的能力。”
德国图书信息中心王鑫表示,编辑理念上的差距,造成了中外图书的内在不同。“国外编辑往往注重孩子怎么想,总是以孩子的视角来编书。像在德国,既有大型出版集团,也有只有一两个人的小出版社,他们专注于图书编辑,并没有考虑要迎合市场,要卖出去多少。”但国内的编辑不仅要编书,还要关心书卖得怎么样。毛毛虫童书馆版权负责人郭桴就抱怨,国内童书编辑的日子并不好过,奖金完全和图书销量挂钩,编辑更关注的是什么书好卖,而并不是关注什么作家值得培养。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国内童书出版商对本土原创图书热情不高,“原创书要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引进版,定价25元的书,创作时间要花上一到三年,首印上万册都很难保证作者的生计。”郭桴算了一笔账,“做引进版童书,尽管首付版税需50万至100万元人民币,但往往销量有保证,如今很多出版社宁可做引进版,而不肯冒险做原创。”这样一来,引进高于输出的现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五,合理调整出版格局。我国的童书出版格局也不太合理,几百家出版社都在出童书,但是精品并不多。海飞说:这是“满天星”式的“散沙”型结构,个头太小,力量太散,缺乏以资本、人才、市场为导向的集约型童书出版集团;童书出版品牌影响力不强,缺乏像《安徒生童话》《哈利·波特》这样的国际性品牌童书,缺乏国际性品牌作家;出版的现代化、数字化进程也都存在着滞后的问题。
第六,儿童文学实际上一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尊重,导致了专业创作者、研究者的流失,这对一个发展尚待完善的领域,打击是致命的。曹文轩表示:“这几年童书作家的收入的确是提高了,但是儿童文学的专业地位却没有提高,无论是专业的研究界、批评界还是童书作家本身,都没有把为孩子写作当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来看,我认识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不敢轻易写作儿童文学作品,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为孩子写作当做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要深思熟虑后才动手,但是国内的童书作家却没有这种使命感。”
我们一直在努力
随着国内外出版界交流与合作的深入,中国童书“走出去”也逐渐显示了一定的成绩。这与各家专业童书出版社的构想与努力密切相关。
明天出版社每年向海外输出版权的数量大约有十几种,副总编辑傅大伟认为,在向不同国家输出版权时,要考虑到对方的购买力、欣赏眼光和阅读兴趣等市场需求,提供适宜的内容介绍。像“杨红樱亲子绘本故事”在2005年和2006年分别由中国港台地区的出版商和越南出版商购买了繁体字版权和越南文版权。越南版与原版相比,封面没有改变,但开本缩小;繁体字版与原版相比,用纸更加考究,色彩也更亮丽,由平装变成了精装,封面、系列图书的名字和每一本图书的具体书名都有所改变,如“杨红樱亲子绘本故事”之《寻找快活林》变成了“童话森林绘本”之《寻找快乐的狐狸》。
新蕾出版社陆续开展了向我国港台地区和海外的版权输出业务,品种相对比较齐全,包括中国文化类读物、小说类读物以及图画类读物等,最近也开始面向韩国、泰国等国家输出版权。据新蕾社编辑张昀韬介绍,韩国的一家出版社已购买了新蕾社拥有版权的《宝葫芦的秘密》一书的版权,并且在韩国少儿文学类读物市场上取得了比较好的销售成绩。由于这本书在韩国市场上的成功,韩国的其他出版社也开始关注中国经典作家的作品,该社的《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也将版权卖到了韩国。另外,张昀韬也注意到,中国古典文化读物在韩国很受欢迎,新蕾出版社“各民族的神话”丛书中《汉族的神话传说》就已经输出到韩国。
海豚出版社版权创造了输出的新模式——合作出版。“感知中国文化——互动学习丛书”就是采用这种模式出版的一套作品,它由海豚出版社与美国OCDF公司合作出版。在做这套书之前,海豚出版社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查,认为随着国际上的“中国热”和大批中文学校的成立和中文课程的设置,“中国文化”对国外图书市场有很强的吸引力,但目前国外图书市场上的中国文化方面的图书或内容陈旧,或较为专深,一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虽很有兴趣但望而却步。因此,该社针对目标市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将读者对象锁定在美国的小学教师、亚洲地区的国际学校的老师、国外领养儿童的家长、国外中文学校的老师、海外华裔子弟、小学及社区的公共图书馆、美国的家庭学校以及支持中国文化的团体等。“感知中国文化——互动学习丛书”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的手工艺品、中国的节日、中国孩子玩的游戏、中国民乐乐器等40多个主题,根据国外教学特点进行设计,将中国文化有机融入国外孩子所熟悉的教学情境和兴趣点,寓教于乐。
北京大众世纪文化有限公司在《年》和“中国吉祥兽”两个绘本项目上采用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同时出版的模式,在童书的海外版权输出方面进行了尝试。这两部作品是向广大青少年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读本:其中《年》讲述了年兽的故事,也就是中国传统节日——“年”的由来;而“中国吉祥兽”作为一套丛书,则介绍了龙、凤凰、麒麟等6种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动物。出版人孙玮介绍,该公司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模式来操作该类选题是出于三方面考虑:一方面,其母公司新加坡大众书局在东南亚的网点可以为北京大众公司所用;其二,在中国大陆进行图书产品生产的成本相对较低;第三,五地同时出版也可以有效地分散出版成本、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也越来越重视版权输出工作,与韩国、越南、日本等亚洲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出版商建立了常年联系,积极推荐和输出自己的产品。社长王建平介绍了该社对版权输出工作的系统规划。她认为,要建立稳固的输出产品线,用整个产品线去洽谈合作,建立自身的品牌和产品线;做好版权输出的售后服务;积极主动拓展输出版图,增强与各国出版机构的信息交流,积极主动搜寻版权输出需求,对构架稳健的版权输出市场非常关键。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开拓信息资源,消除沟通障碍;找准输出定位;遵循国际惯例,注重版权贸易市场长远健康的发展。王建平特别指出,“在国际版权贸易中,无论与哪国的出版机构洽谈合作,都应该坚守民族文化气节,有文化自信,公平合理,平等交易。在价值判断上,不要重引进,轻输出。”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开拓西方主流社会版权市场上也有了突破,具体做法是:利用“浙少版”图书的图文总体优势,为海外图画书市场量身打造“走出去”图书。该社聚集全国一流的插图画家和儿童文学作者,为欧美童书市场专门设计制作了 “绘本中国故事”丛书。该书全面展示中国童话、神话、成语、故事等,绘画具有中西结合的艺术特点,符合欧美儿童的阅读习惯。同时该出版社也十分重视博洛尼亚书展这个重要的国际舞台。“绘本中国故事”正是通过在书展上的大力宣传,受到多家欧美出版商关注,并有两家表示了明确的合作意向。
接力出版社将版权输出的工作重点放在作品的前期推介上,如作品的简介、作家简介以及相关样张的翻译等,在行业媒体上推介出版社的重点产品,通过书展和境外行业媒体“双管齐下”地宣传原创作品,如“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就曾在美国著名书业媒体《出版商周刊》上进行过宣传。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认为,出版社版权输出的图书品种逐渐增加,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图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较高的品质,适合引进国的市场需要;二是图书在国内市场上畅销,久居排行榜上,良好的销售情况能促使国外出版社做出购买版权的决定;三是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网”及《中国新书》上介绍重点图书,向代理公司推荐新书,使国外出版社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自己的图书信息。
为什么一定要“走出去”
也有人认为,中国人口多,自身的童书市场就非常广阔,现在发行量动辄10万册的童书并不稀奇,这是很多中小国家不能比拟的,所以是否“走不出”似乎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么急迫和必要。
其实,中国童书“走出去”不仅仅是一个贸易顺差、逆差的问题,更是一个参与世界文化发展进程、展示中国形象和中国人民族性格的问题。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拿到这样的高度上来着眼,那么我们势必将在全球文化政治领域逐渐丧失话语权。
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强调,研究者要加强研究和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力度,同时,创作者也要“修炼思想和艺术的内功”。“走向世界,不能只简单兜售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因此,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只有将民族传统文化、现代生活内涵、儿童心理情感恰切而有机地融为一体,具有历史感、人情味、艺术美,真实、深刻地反映中国人的生活,有效地揭示中国问题,抵达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孩子的灵魂,才能具备“走出去”的姿态和底气。
海飞一再表示,要用敢于竞争的姿态、勇于创新的精神、自由宽松的环境去培育、打造童书出版和儿童文学的中国品牌;还要下大力气解决文字翻译问题,认真搭建中外沟通新平台。
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在《正是此时,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一文中指出,“儿童文学蕴含着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对话和价值期待”。今日中国多样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对养成民族下一代人性基础的影响、濡染和意义,都在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当人们向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迈进,世界的眼光正在更多地关注着中国。而中国文化的宣传与输出,是我们这代人需要持续努力的工作。鲁迅说:“童年的情况,便是将来的命运。”所以,儿童文学的创作、阅读折射着未来的中国,中国儿童文学的输出对世界重新看待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有着重要且无法取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