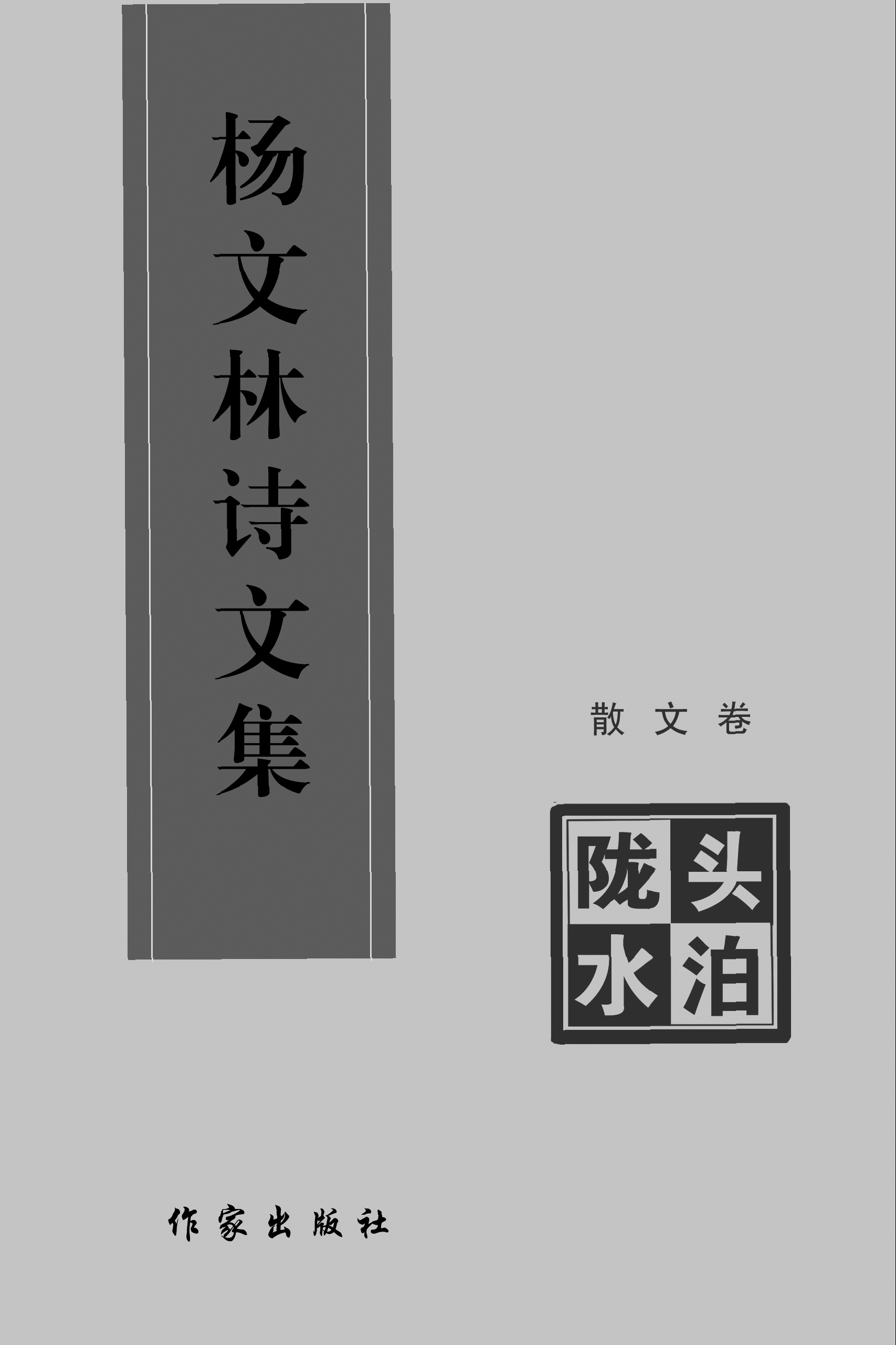
面前摆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杨文林诗文集》(作家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诗歌卷《北草南花》和散文卷《陇头水泊》;蓦然想到今年是老诗人的八十寿诞及从事文学创作60年,真可谓三喜临门。无论是八十大寿,还是创作60年,对人生对文学都是很高的标志,应该庆祝。可是因老诗人的为人低调,也可以说因某个环节的疏忽,错过了。因此,读老诗人的新著便有了特别的感慨:这哪里是普通的诗文集啊!它分明是杨文林一个甲子的文学情缘,是他汗水、心血与智慧的结晶,是他文学圆梦的记载与见证,换言之,是他生命的光焰。
没错,杨文林是视文学为生命的,这两本集子的成书过程,就足以成为鲜明例证。就诗文集的素材而言,是他数十年的生活积累,而写作成书却是近10年的事。也就是说真正把素材及“半成品”加工提炼成作品,是在他脱离开纷繁的文学领导岗位之后才动手完成的。此时正是他年届“古稀”至年逾“古稀”的人生阶段。对一般人而言,这正是含饴弄孙、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收官”阶段,而他却依然为圆文学梦,青灯伏案,孜孜以求。此情此景,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对此,我尊之为“杨文林精神”。
很难用“厚积薄发”来概括这种精神,杨文林信奉的是“慢工出细活”。
“十年磨一剑”呢?亦似不妥,成书用了10年,而生活的积累与储备却要向前延伸10年、20年、30年……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呢?有点贴切,但不传神。
倏然,明代大学者、大诗人顾炎武的诗句涌上心头——
苍龙日暮还行雨,
老树春深更著花……
对文学梦想的追求与行政领导及编辑工作的冲突,长期困扰着杨文林,有时令他痛苦不堪。杨文林自叹:“同仁们期望我老树著新花,而我却没有顾上写诗,不能说不是因为忙,编刊物,办笔会,建宿舍,跑经费,要编制,干了很多和写诗无关但和文联、作协、刊物有关的事情,加之,有些年里思想纷争,常做检讨,心情不好,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间竟无一首新作发表。”(《杨文林诗文集》诗歌卷《北草南花·后记》)。
杨文林所钟爱的文学创作,几乎要被他所竭诚投入的卓有成效的文学组织活动及编辑工作所淹没。
其实,愚以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杨文林对文学的执著、挚爱与虔诚,由神圣而敬畏,任何对文学创作的不严肃、不认真的轻慢行为,都被他视做对文学的亵渎。所以他积累的素材甚多,而动手写作的甚少;而写成初稿经过再三修改、推敲拿出发表的作品则更少。
用心良苦,必有回报。这反倒成全了杨文林,形成了他创作的独具特色——少而精。在许多红极一时、各领风骚三五年的作家、诗人纷纷“江郎才尽”之时,杨文林却达到了“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大化之境。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民文学》《延河》《飞天》推出了他的散文,篇篇堪称精品——《大鼓天音》,蕴涵着浓郁的陇原民俗文化,充盈着动人的乡情、乡音、乡韵;《陇头水泊》,牵动陇人与生俱来的盼水、敬水、思水的神经,满怀对家乡自然生态恶化的忧思、忧虑与忧患,氤氲着浓浓的人文关怀;《宝石蓝的华沙车》,叙写文坛轶事,感时抒怀,楚楚动人;《豆饭养食忆》,回忆的是过去,而针砭的却是当下时弊……
10多年前老诗人曾有一次赴德国的探亲之旅,行前他放出豪言:“这次到德国去,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给德国人讲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的故乡人见识见识咱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这件趣事已过去10多年了,杨文林的探亲之旅也是去了复来,来了复去,从未听说他在德国讲马克思主义的“盛况”,倒是读到了他一篇接一篇地刊于《人民文学》等刊物上的厚重而充满文化意蕴的散文——《一面坡上的酒风景》《克林根酒村的小康》《诗哉,酒哉》《文明的纽带》……
这些散文,一改沿袭了数十年的介绍异国风情的旅游散文窠臼,直接深入德国这个古老而又弥新的国度,以文化为契入口,让读者感同身受,同作者一起观察、体验、思索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称这些散文为文化散文,而且是大文化散文。这儿的“大”不是指篇幅的浩繁冗长,而是指题旨、视角、眼光及胸怀。
文如其人,指的是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杨文林其文品与人品可以互相印证,互为诠释。他为人热情,对人真诚,重友谊,讲义气,乐于助人,又常常心怀感恩。
李季、闻捷1958年来到甘肃,担任甘肃省作协主席、副主席,兼任文学刊物《飞天》(当时为《红旗手》)的主编、副主编。正是李季、闻捷对杨文林的赏识与提携,让他实现了由“杨中尉”到(编辑部)“杨主任”的人生转折,走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文学之路。当时,杨文林只有26岁。
“文革”中闻捷被打成“反革命”,关“牛棚”进干校,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许多人避之惟恐不及,而杨文林却利用出差路过上海的机会,前去看望闻捷——这正是闻捷含冤死去的前一天。患难见真情。没有见到闻捷,成为杨文林终生的遗憾,但“却深深地记住了他生于兰州、母亲已含冤去世的孤零零的小女儿赵咏梅一双透着茫然的、怯生生目光的眼睛。这是一种难忘的悲情,使我牵思30年……”(《陇头水泊·后记》)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杨文林是不写散文的,而当1979年闻捷冤案“平反昭雪”的消息传来,他竟用一个不眠之夜,写出了情似井喷、泪如雨下的《悼念闻捷同志》的长文,读之,令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感人至深。
2002年《闻捷全集》出版,杨文林在兰州组织了盛况空前的“《闻捷全集》出版座谈会”,闻捷的生前好友、闻捷的女儿赵咏梅、上海文学界的代表等200多人出席。会后他又亲自带领赵咏梅经陇东赴陕北闻捷工作过的地方及她母亲的故乡访问,为赵咏梅补上了温馨的一课,体会到了父辈的关怀及大地的温暖……
乡土情,民族情,同志情,文学情,以情动人,以情感人,是杨文林做人的成功之处,也是他为文的成功之处。有一篇《陇上文坛四君子》,写老诗人与金吉泰、刘志清、任国一、张国宏四位农民作家、诗人半个多世纪的情谊,以及这四位农民作家、诗人的文学道路及人生际遇;见人,见事,见思想,见作品,很生动,很感人。
杨文林写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诗,其历史的纵深与穿越,文化的积淀与厚重,视角的独特与开阔,意象的微妙与新奇……拿今天的审美眼光看,也属上乘之作。有一首抒写帕米尔高原的诗:“帕米尔出生时海水退去\岩浆雕塑的万山之祖把赤裸的躯体交给大地而把面容埋进了云里”。起势不凡,一开始就写出了帕米尔的惊世骇俗,卓尔不群。之后,一泻千里,直抒胸臆:“站在帕米尔的肩上,能听见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涛声抓一把空气,能闻见吉尔吉斯草原的草香和黑海的咸风西瞥一眼,能看见雅典的宫殿和罗马的古城东望山下,连着万里长城能听见一路响来的汉唐驼铃”……
读老诗人的《北草南花》,你既能感受到作者对诗的风格的一贯坚守与继承,也能感受到其诗风的发展与变化。他的后 “伊犁篇” ——新时期西部行吟,较之前“伊犁篇”,在诗质诗艺的开掘上都有了深入与升发,上了新的层次,达到了新的境界。老诗人追求变化的诗风,在“南国篇”中更为明显,他以西部诗人的眼睛与视角,寻觅南国自然、山水、草木、花卉之美,熔铸短章,别有情趣。
1985年7月“西部文学研讨会”在伊犁召开,闭幕式上,杨文林朗诵了他的即兴之作《鲜红的象征色》。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我没有走进伊犁河渔场那里离国界太近沿着开阔的伊犁河谷拉着苏维埃共和国的铁丝网\……鱼族没有国籍在那边下游恋爱在这边上游生育度过一年一度的蜜月再回巴尔喀什湖生息如果,不幸触上这边或那边的河栅也会酿成别离的悲剧”……
渴望中苏关系的解冻,渴望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与和谐……杨文林的诗唱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心声,因而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特别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朋友,不仅鼓掌,而且起立欢呼。一位维族诗人走上台去,与杨文林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啃”了半天之后,又把他们的民族宝典——枕头般厚的大书——《福乐智慧》赠予杨文林,以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