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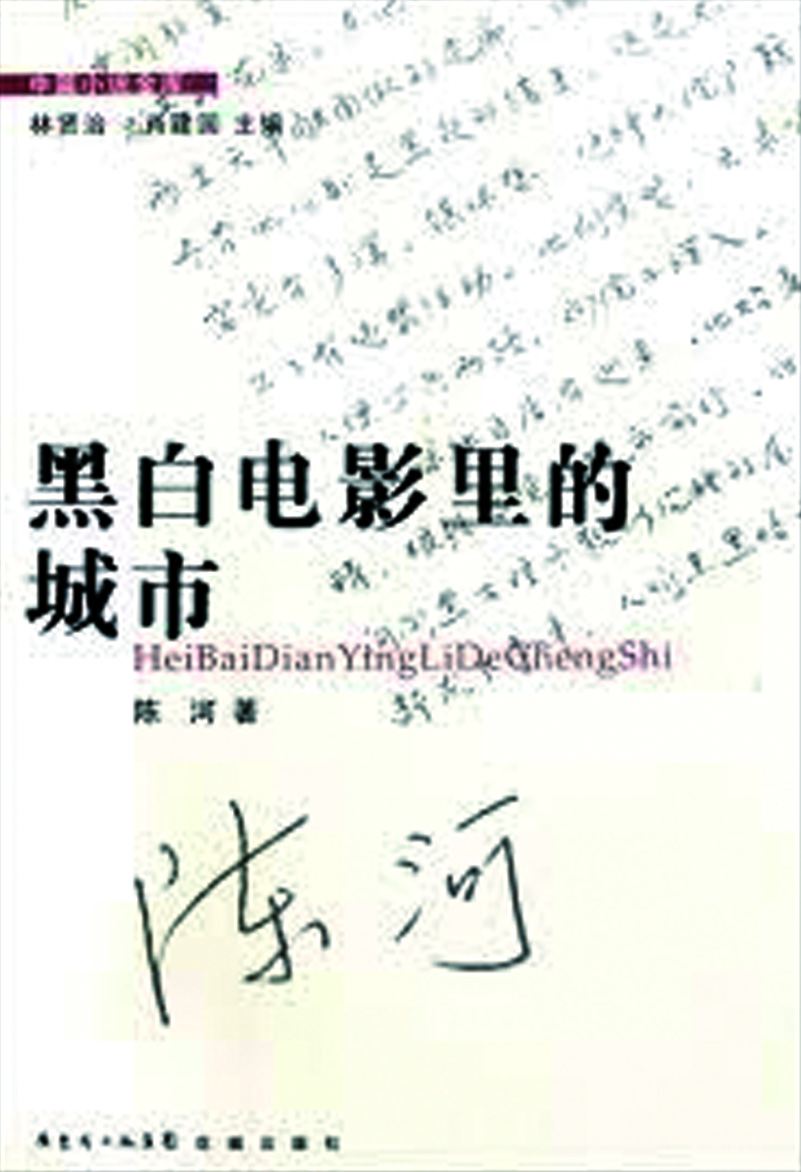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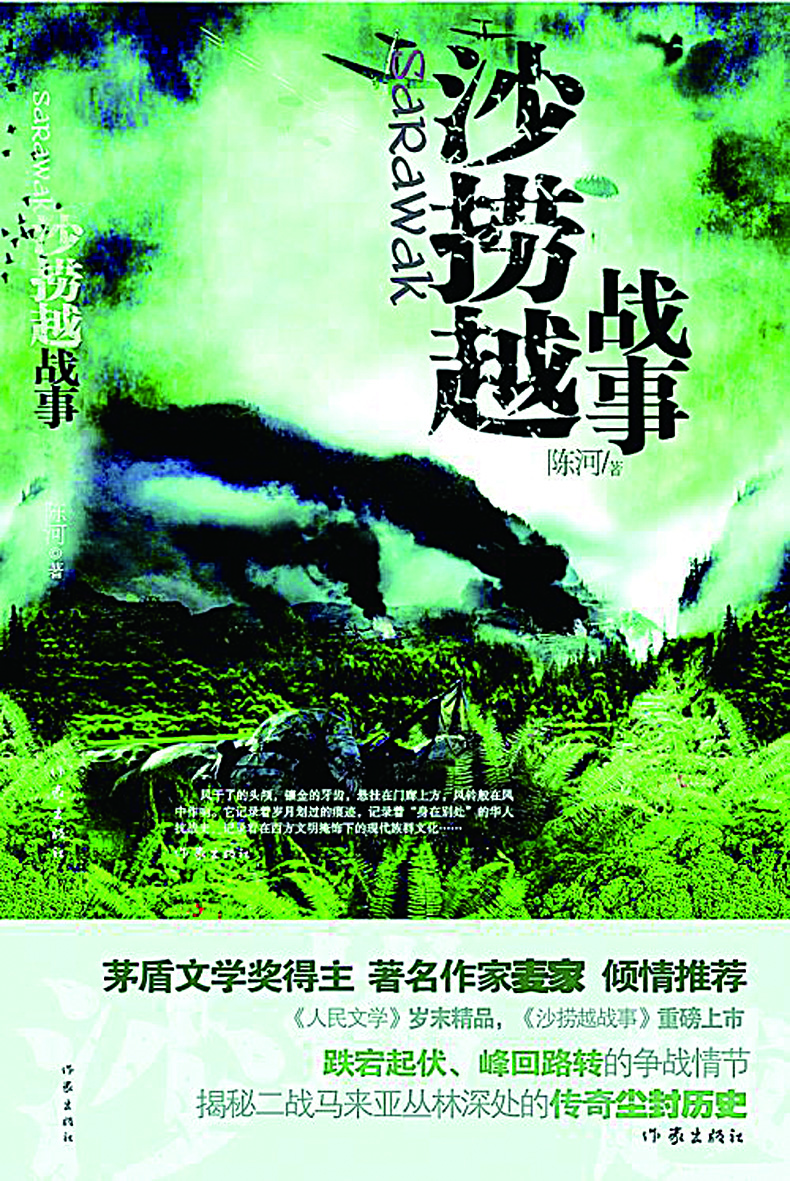

第一眼看到陈河,正可谓“人高马大”。这个1958年出生的温州男人,在人群里高得很是突兀。都说温州人是最能打拼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同样是从温州走出去的加拿大华人小说家张翎,这些年以她柔软的笔书写着历史烟云中的“双城记”;而步履稳健的陈河,则是以男性的大手笔,为我们凿开历史潜藏的暗道,再将东西方打穿,拓展出一片前所未有的崭新视野。
写作的奇妙之处常常是因为源于无法遏制的冲动,一部好作品就如同是一场苦恋的爱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不可预测,且爆发的时候激烈而执著。陈河曾在《为何写作》中这样表白:“十几年前当我放弃了写作出国经商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放弃才成全了我日后做职业写作者的梦想。当然,这个回归的过程让我付出了十多年的时间。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并没有浪费时间。这十几年所经历的事情给了我丰厚的生活积累,让我的生活外延大大扩展。我源源不断地写出了作品,有了自己的粮仓,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有几根挂在墙外晒太阳的老玉米。”
2009年的秋天,我曾与陈河一起站在中国腹地古城西安苍茫的灞河岸上,陈河眯着眼,极目横扫远方,那时他的内心已经开始了信马由缰。从他重新执笔开启创作至今只有短短5年时间,先是短篇小说《夜巡》(《人民文学》2008年第11期)获得了首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2010年,中篇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得了首届郁达夫小说奖;2011年,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获得了第二届“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的主体最佳作品奖。此间他的小说还入选了《小说月报》第14届百花奖。2011年3月,央视第四频道“华人世界”栏目特别专访了陈河,称他是“死里逃生的华人作家”。这匹重新闯入文坛的“黑马”,速度之快,作品之重,总是令人惊喜。在历史的幽深隧道里,在东西方的跨界时空下,陈河给读者看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看他如精灵般穿越历史和国界的绝妙身手。
早年学鲁迅的时候发现,认识“死亡”对一个作家至关重要,由“死”再看“生”,才能把“生”看得明白。关于“死亡”, 陈河呈现的不是“认识”,而是“体验”。体会过“死亡”的临界,陈河获得的是一种无畏和凛然,于是他重新看世界,就有了不一样的眼光。读陈河的小说,大开大合、激流勇进,没有犹豫,不见躲闪,在天地苍茫之间,他如入无人之境。
有人说陈河小说的迷人归功于他个人神奇的经历,其实不然。关于“文学”,陈河一直在通向高峰的路上跋涉。他曾经这样评判他所喜爱的西方作家:“有一部分作家的写作主要靠丰富而特殊的经历支持。比如杰克·伦敦,比如海明威。杰克·伦敦的小说充满男人气概和传奇性,可是你想在里面寻找一些更高一点的文学品位时可能比较困难。而海明威的3个长篇和大量的短篇同样写个人经历,可作品中包含了大量的象征。这样,他所写到的场景和情节就不再只是传奇,而是透露着神喻般的暗示。但海明威写完了自己的经历,再也写不出什么了,苦闷得开枪自杀。倒是经历不丰富、一心守在图书馆的博尔赫斯让全世界所有写小说的人敬佩得没有话说。卡夫卡也是这样,年纪不大就死了,没什么特别的经历。可我们看他的《城堡》竟然是那样深不见底无法看穿。所以我觉得写小说主要还得靠精神上的创造。”陈河小说的力量正是来自于大境界,而不是故事,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不是对于历史、对于生命在某种意义上的冷面“揭发”。
很多年前,小说家贾平凹说:“小说其实不是写出来的,是我去发现的。”当代中国的很多小说却是“写”出来的,缺少的正是“发现”。如今陈河说:“写小说有时觉得简直在和鬼神打交道。博尔赫斯有一个方法,他把将要去写的小说想象成早已写好的作品,他的任务只是要把它慢慢找出来。这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闭上眼睛按照这个说法去瞎想,我似乎能看见天边一座寸草不长的山脉,山的内部埋藏着一具具如恐龙化石般的东西,那就是我将要去写的事实上早已存在的小说。我得千方百计把这些化石一样的散乱部件找出来,拼接在一起。做这种事情得花掉一个人所有的体力和智力。到了你筋疲力尽的时刻,一阵风吹来,你挖掘出来的庞然大物会突然活了起来。用这样的方法去想象写小说有点像天方夜谭,可是这个想象过程令人愉快。 ”正是因为这样的“天方夜谭”,让我们读陈河的小说犹如在“探宝”,更犹如“历险”。
古今中外,评判小说家,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独特的。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中那个过去的电影和今天的城市,由陈河创造性地在小说里连接起来。迟子建说:“陈河还原了几十年前的一部黑白电影,第三世界的境遇和情怀是小说最打动人的地方。”归结一句话,陈河看见了我们无法看见的城市和人。
很多人喜欢陈河的长篇《沙捞越战事》,也是因为陈河写了一个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物周天化。周天化是生于加拿大、长于日本街的华裔加拿大人,“二战”的时候本想参加对德作战却因偶然因素被编入英军,参加了东南亚的对日作战,一降落便被日军意外俘虏,当上了双面间谍。周天化既不高大,也不英武,就那样死在了丛林中。这是“一段不为国人所熟悉的域外华人抗战史”。加拿大华裔学者徐学清评价:“《沙捞越战事》写的就是历史深处孤寂的忧伤,是种族之间隔阂的悲凉,是人性与人性中兽性以及族性之间的生死较量和无比复杂的相互关系。”
小说《布偶》更是奇妙,陈河写了一群生长在中国大地上非常特殊的人。王安忆说,“是一片眼熟中的一个陌生”。李敬泽说:“《布偶》在很多方面超出了我们的知识、经验和想象。”我们惊异于那个勇敢地品尝爱情禁果的莫丘,我们怜惜那个为爱情送命的柯依丽,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德裔后生裴达峰竟然假扮医生去追求生命本相的“壮举”,我们更感叹十多年后裴达峰与阿芸的那次历史性相见。一个中国南方的小城几乎成为世界的缩影,甚至是人类的缩影。最难忘主人公莫丘站在裴家花园的月光下,“泪水涌上他的眼睛。他想到:尽管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相互残杀,到处呼喊着口号,但的确存在着一种动人的优美。就像身边这座月光下的玫瑰园,无论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总会在皎洁的月光之下,放射出亘古不变的美丽精神”。
读陈河的小说,感觉犹如尖硬的铁犁毫无钝感地犁过深水的海底,那丰沃的海底似乎已经等待了好久,只等他的犁轻轻划过,然后翻起一道深深的沟壑。陈河似乎就喜欢那海底沉积的故事,手感滑腻,却又深不见底。他的文如其人,朴素却诗意,很“男人”,很“大气”,质感浓烈而厚重。
毫无疑问,是海外生命的移植与沉淀激活了陈河潜藏在灵魂深处的激情和欲望,正如同诸多的当代海外作家一样,生命的重新嫁接让他们蓦然焕发出饱满的异样光彩。陈河自己说:“我现在的写作状态得益于我这些年远离故土栖身异乡。远行漫游对于一个文人是件非常重要且必要的事,古代的文人墨客无一不是流落天涯的。”在这里,远离带来的是审美的距离,漫游呈现的是自由状态的洗礼,海外华文文学近30年来所形成的精神特质在陈河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呈现。
陈河的精神优势在于他对“历史”、对“人性”的重新解读,从东方走到西方,陈河看待历史和生活的视角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就如同作家的视野与他自己站的高度有关一样,陈河已经超越了“家国意识”的精神平台,他有意识地让自己走到了“局外”,这个“局外”的特征正是当今海内与海外作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陈河说:“能远离各种喧嚣,不紧不慢写自己喜欢的东西,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