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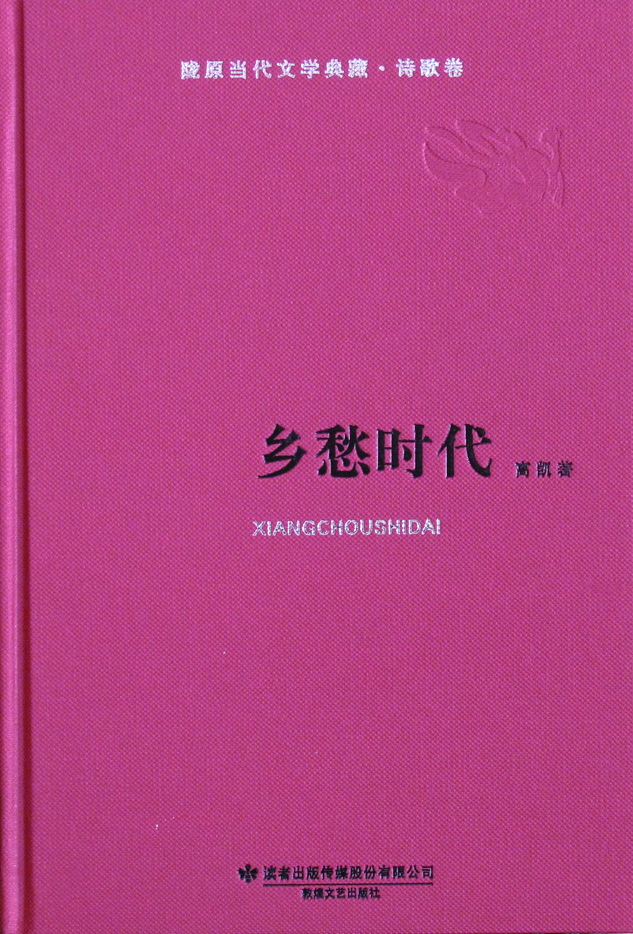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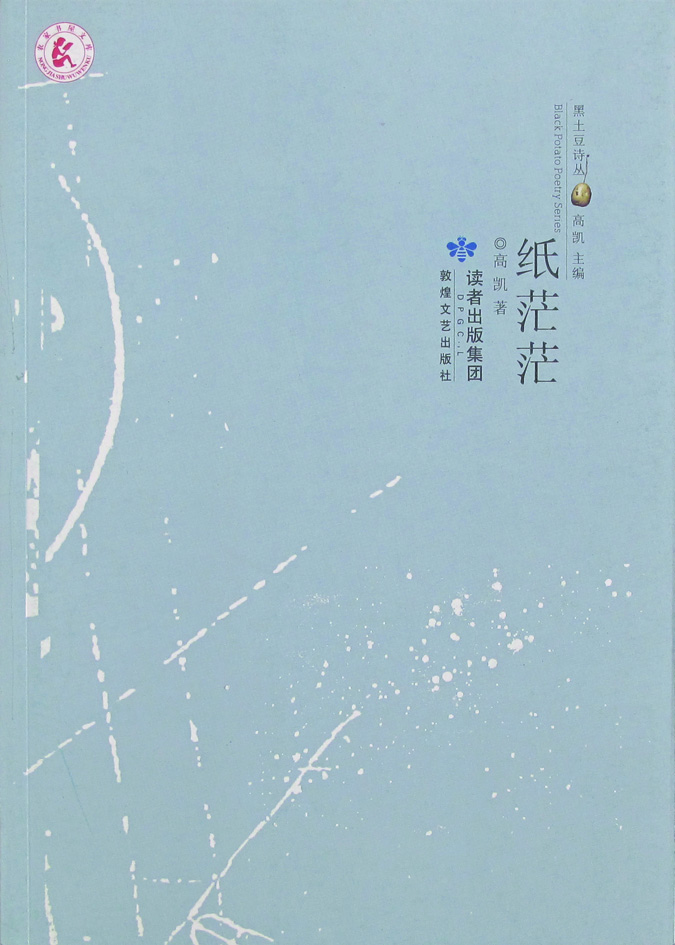
高凯的诗歌创作,起步于1980年代初,引起评论界的关注,是1990年代他的陇东乡土诗连续推出之后。10年生聚,2000年,高凯的代表作《村小:生字课》横空出世。这首后来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诗,凝聚着诗人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与出众的诗意捕捉力,也是他融入当时中国诗歌重返民间之潮的标志。近年来,面对高凯层出不穷的作品,已有不少的评论家给予高度评价。他们称赞高凯为“陇东风情的行吟者”、“黄土地上的歌者”、“西部乡土诗的代表诗人”,认为他的诗歌“从心化出”、“诗风健朗淳朴,阳光幽默,乡土味与当代性结合得十分出色”、“是现代诗与先锋诗日益泛滥时期的另类和净界”等。
丁念保曾在《当代文坛》撰文《沿着乡土的道路进入诗歌——高凯诗歌简论》,对高凯诗歌的概括简明而扼要:“高凯诗歌之所以在这个污浊的时代获得了清新、在这个矫饰的时代获得了朴素、在这个虚假的时代获得了真实,第一因为高凯诗歌拥有陇东故乡这一生命的根基,其诗歌创作的题材、主题、意象、语言以及抒情方式,都根植于这一沃土;因为高凯诗歌既有童心,复有爱心,更有一颗淳朴睿智的诗心:烂熟于心而妙手偶得、时刻留意而捕捉机敏、心地真纯而文本简洁、深谙诗味而能屈能伸,当年那个‘踩着诗歌的韵脚深入乡土’的诗人正在‘沿着乡土的道路进入诗歌’;高凯的诗歌气韵贯通、口吻平易朴素。诗中有气:真实生活的底气、用心感悟的灵气、鲜活跳动的生气。”
以诗集《心灵的乡村》为标志,高凯的早期诗歌主要以家乡陇东的风土人情为诗写的基本题材,表现为“风俗画的展现、乡情乡愁的吟唱、家园意识的追寻”三个主要层面。从诗集《纸茫茫》开始,高凯的创作虽然乡土依旧,但开始出现乡土以外的诗篇,“有对已逝的,与自己已了无关涉的乡村风物的追怀,有对当下的个人境况的自嘲与感伤,还有对一些世相情态的扫描”。到了最新出版的《乡愁时代》,高凯诗歌这一走出陇东的“大乡土”倾向更为明显,其中《拖拉机》《关于鞋匠》《大厦的出身》等,像是高凯的乡土大军中一支出征城市的小分队,表现出“乡土诗人在哪里乡土诗就在哪里”的艺术自信。高凯的诗歌虽然出现了上述新变,却并不影响我们对高凯诗歌总体风貌如下的判断:高凯通过对乡间故土简朴生活的诗性描述,彰显出民间生活的圣洁,引领人们深入平凡的乡土并获得心灵的超然,在对村舍炊烟原汁原味的直面中得到天地自然风清月白的身心净化。
宏观诗人与诗境营造
高凯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宏观”的诗人,具有极强的整体把握能力。他的写作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意在笔先的特征。如《草莽童年》《村子的传说》等。意在笔先,所以结构紧凑运笔明快;运笔明快,却也一笔三折;一笔三折,却也意尽即止——诗歌到意思为止,始终表意清晰,有一种不枝不蔓的简约之美。他往往抓住事物的一两个或两三个特征即能成就诗章。如《打鼓》,高凯只是执其“空”、“响”二端,并不怎么苦思冥想,却仍诗意盎然。
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高凯并不缺乏“远取譬”的能力,如《抚摸一把刀子》中:“就像从深沉的黑夜里/摸出一片月光一样 一把刀子/握在了我手里”,看似天处飞来,实则当面拾得。再如《我的纽扣》:“太阳是我的第一颗纽扣/你能不能给我解开//月亮是我的第二颗纽扣/你能不能给我解开//那些数不清的星星是我下面的纽扣/你能不能给我解开/最后一颗纽扣就是我里面的心儿/你能不能给我解开”。这一组纽扣从小处着想却蔚为大观。但是,高凯的比喻之剑却并不轻易亮出。他的诗歌设喻常常是点到为止,似乎只求喻用而不求喻质,实则为追求整体的谐调而不求局部的精彩。如《山顶上的黑鹰》中,“黑鹰很久以前就把村子盯上了/居高临下,像天空的一团乌云”,这样的比喻虽不卓异,但和语境的配合恰到好处。而且,高凯的诗歌意象往往并不密集,但由于大局在握,诗意却并不稀薄。
高凯诗歌是有着如上所述的“大局观”,同时其对诗歌局部低调处理,这样使得诗歌具象的敞开力也应运而生。高凯的诗歌创作,往往用料不多却味道十足。如《村小:生字课》,全诗以一种句式而成“点”,复以对此句式的重复运用而成“染”。再如《谜语里的老山羊》,围绕“白胡子老汉顺梁走/黑豆豆撒了二三斗”展开,从一个小小的谜语渲染出一首盎然的诗。再如《兔年的典故》,采用叙列二法,将兔的“典故”一一道来。这种诗歌生成看似乎率意,实则暗合法度,因为诗人善假于物、随体赋形。高凯有一种借用自然的造型与情景而营造其诗歌结构大模样的能力,这种因循自然的诗歌架构,让写作避免了苦心孤诣刻意营造,也让读者极易接受这些诗歌。之所以有人会认为高凯的诗歌都有一种歌唱性,正因为他捕捉到了那些来自乡村小学的常用语——花 花 花骨朵的花——是自带韵律的,而诗人无非是量材而用地顺从了这一韵律而已。
当然,言说高凯诗歌这种“一览无余”的宏观掌控性,还必须指出高凯诗歌其实耐人寻味的注重细节的语言炼金术。以《村小:生字课》为例,以一个句式简简单单大模大样而成诗,是其粗,但他能精心选定“蛋”、“花”、“黑”、“外”和“飞”这5个字,却是心细如发。再如《雪地上》之“乌鸦安窝的老槐树/弯着腰 背回一身厚厚的雪”,那个“背回”的“回”字,真是妙不可言,境界全出。
还原事实与诚实品格
生活中的高凯大智若愚,诗歌中的高凯大巧若拙。高凯的好多诗歌直陈其事直取心性,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事实性与内蕴的张力。如《村小:生字课》《你真坏》《走亲戚》《站街女》等,全诗不用比喻或者少用比喻,基本上都是实话实说的实事。高凯这些“事实的诗”,堪称对于坚“拒绝隐喻”、“回到事实”等理论不知不觉的响应,也再次证明了谢有顺的一个观点:看到比想到更困难(因而也更可贵)。换言之,认领一首天籁自足的诗,比创造一首挖空心思的诗,更困难,也更可贵。高凯的诗歌因此也具有了一种既能“证实”又能“证伪”、看似知性实为禅悟的特征。
高凯这种回到事实的诗,既对如白描这样的诗内功夫要求很高,同时也对像艺术发现力这样的诗外功夫要求更高,它要求一种诗歌的敏感状态,即时时张开着诗意捕捉的大网——有时候,我觉得高凯的这张网有些不太“环保”(网眼太小)。但是,高凯不把自己保持在这样一个诗歌的敏感状态,他又如何见别人所未见、言他人所未言——他如何说出真相?他的《羊皮筏子》云:“这应该是羊一生最生气的时候了/气鼓鼓的 集体被绑在一起//命都没了 一个个/还一起给谁生了一肚子闷气”,句句切题、字字及物。高凯说出来了,我们感觉近在嘴边;他要是不说出来,还不是远在天边?高凯有诗《在家里拾到一根针》。一件针尖般大的小事,锐然挑动高凯诗思,“犹如在家里偶拾/遗失在苍茫里的一首小诗”。高凯的好多诗,都得来全不费功夫,似乎是“妙手偶得之”。读他的诗,我常常惭愧:就是不能先于他而把这简单的诗认领到自己名下。诗歌需要诗人发现它然后认领它。诗歌是一匹黑马,来到人间只是为了寻找自己的骑手。
高凯这种屡试不爽的事实捕捉能力让他敢于触碰那些看上去极为平常且熟悉不过的题材,并不怕弄不好会说出陈词滥调。诗人似乎窥破了一个艺术的秘密:人们因为熟视,人们一定无睹!于无声处听惊雷,于人们熟视无睹处发现诗意,这才是所谓“陌生化”的高级境界。他的诗歌也给了“艺高人胆大”一个别样的解释:艺高人胆大指的不是走险路,而是走平路。在险绝的地方平平常常地走,真不如在平路上非常非常地走!
当然,对一个优秀诗人来说,仅有如上敏锐的感受力是不够的,还得有深厚的动情力。高凯的诗歌创作,其动情力最为根基深厚的来源,就是他的内心一直葆有的纯真。有纯真的心地垫底,就有一股虎虎而无所惧的底气,所以,高凯的诗歌敢想(不怕其想之奇)、敢说(不怕其言之拙)、也敢于率性而幽默(不怕人们冥顽不悟),更敢于把诗写得简单明快——这是他特征性的话语方式——以至于有人视高凯为童诗作者并从中挖掘出不少天真的质素。人说高凯的诗歌大巧若拙,诚然。在拙的底色之上,高凯的诗歌确实是虽不刻意却匠心独运。但是,高凯之拙,拙自何来?回答是:高凯之拙,来自心地之纯真。于坚曾说“杰出的写作不是与想象力有关,而是与诚实有关”,高凯正是中国当代一个诚实的诗人。
民间口语与乡土中国
高凯诗歌上述宏观掌控、回到事实等特点,连同他的乡土题材、亲情故事等内容,并及他的赤子真诚、故土情结等主题,让读者感受到一种不同于闪烁其词也不同于迷幻朦胧的亲和力,而他对民间口语坚定的使用,对民间口吻的熟稔所形成的独特语感,也是他的诗歌雅俗共赏的一个重要源由。
关于高凯诗歌民间口语化的特征,论者多有指陈,自是确凿无疑,比如“树梢梢上那几个酸杏不见啦/难道想不来咱肚子里有娃啦/当男人的要是在外面胡浪荡/当女人的就把他拴在裤带上”(《媳妇》)等等,无不是野风般清新,泥土般朴实。但是,当“擦去词语上的尘土”成为当代诗人一个伟大的使命,我们必须认识到:并不是回到方言土语就回到了语言的原初状态。方言土语当中仍然难免话语的蒙尘与遮蔽,同样需要一个澄明化的过程方可恢复其如初的诗性,在这一点上,高凯早有直觉,并能于自己的创作中实施去蔽除尘的努力。如他的《弹琴》,落笔即显机敏:“把所有的弦都绷紧/让自己的身心彻底放松”,这不就是“弹琴”吗?熟悉而又陌生,这就是诗歌艺术重新命名的真义——也是乐趣。有“琴心”者,天下皆“琴”,于是,“把一团旧棉花弹成新棉花/也是弹琴”,于是“一切动人心弦的动作/都是弹琴”,于是“弹琴的最高境界是对牛弹琴”。在这里,对牛弹琴,不再是一个成语,而是一个场景。不再是一种文化,而是一句诗。
高凯没有游离于民间口语之外,他是民间口语津津乐道的模仿者。这种所谓原创性的语言体验,对高凯而言可谓刻骨铭心血肉相连。高凯诗歌民间口语的原生态,首先表现为原生态的语词,如窑洞、碌碡、炊烟、磨道、崾岘、场院、喜鹊,但是更表现为原生态的语气和腔调——民间化口语的低缓叙述。如“忽闪忽闪的灯花是谁个剪的/一张一张的窗花就是谁个剪的”(《谁个剪的》)。高凯说自己“诗的意象、语言和节奏都是我的陇东特有的”。魂系乡土的高凯对民间口语那种隐忍、谦逊、徐缓的“节奏”,确实保持了虽然姿态向下但是最为坚定的持守。当然,他这种生命呼吸般真诚的持守也得到了回报,《村小:生字课》是一首佳作,正得益于在民间化口语化的叙述中营造了一个典型乡土中国意境。
高凯诗歌自动承接了中国当代诗歌的题材日常化、形式自由化以及语言口语化,从《陇东:遍地乡愁》到他的《怀乡病》,高凯笔下的乡土已渐呈乡土之痛。他是沿着乡土的道路进入诗歌的,他渴望沿着诗歌的道路进入乡土——进入中国人的灵魂之家与精神之源。诗人的宿命是:永远回不到故乡,所以诗人似乎永远都是在精神的还乡途中流浪。诗歌之路是喃喃着自己的乡音,絮叨着自己的故土,而有日渐远离故乡的不归之旅。
高凯以其浑然质朴又幽默蕴藉的诗歌风格,诚实面对心灵的诗歌品质,民间化口语化的灵动方式记录了当下乡土中国的疼痛与乡愁。诗人在广袤的西部黄土地上行吟歌唱,以他独特的诗歌经验重新书写乡土中国的民间和民间意蕴。高凯的诗歌赋予了当代诗歌写作更为中国化的叙述视角和话语方式,在日渐凋敝的中国乡土抒情中,他和他的诗歌创作会日益显示出独特和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