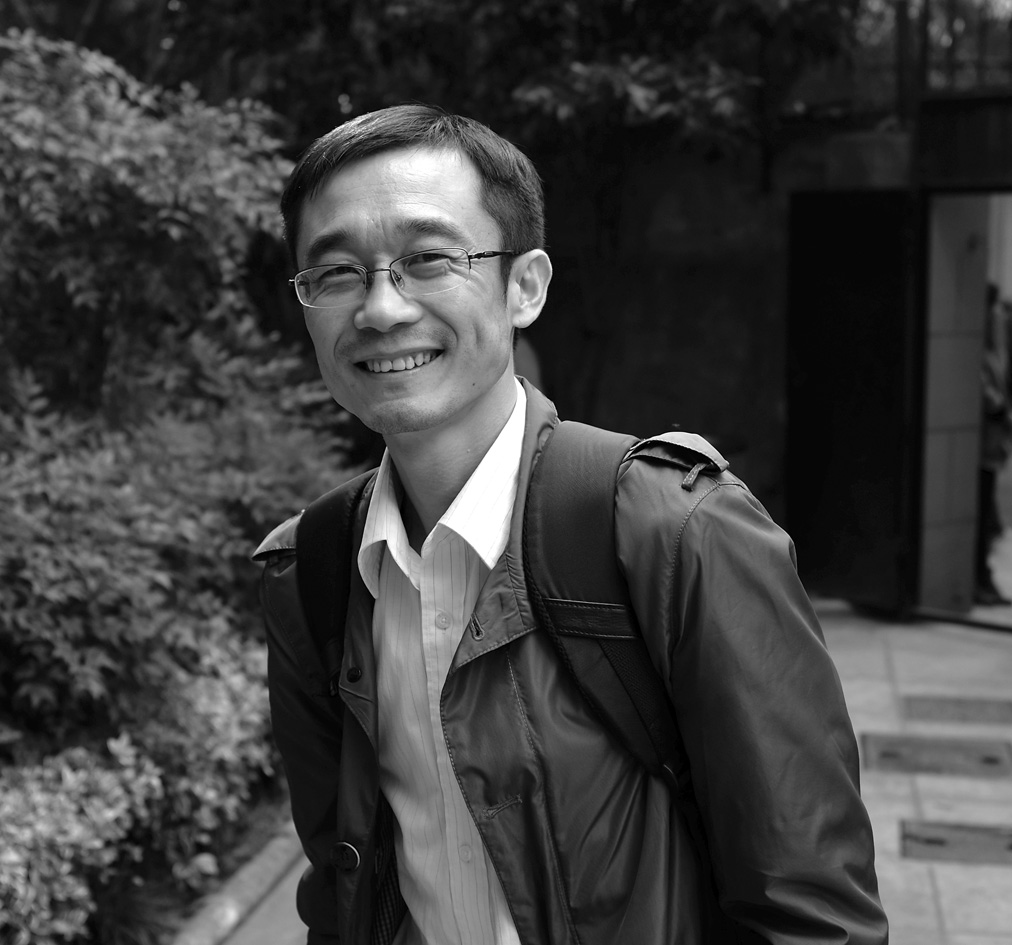
谈到《平凡的世界》,我就会立刻想起自己初次阅读时的印象。小说写了那么多困苦、无奈、失意、挣扎,给人的感觉却是活力四射,里面隐含着一种生命的向上冲动,无论如何都会沿着生活的缝隙艰难地爬上来。
《平凡的世界》里的这种活力,跟19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上升势头有关,那时人人都抱着一种奔赴新时代的热情,仿佛无限的好时光就等在前面,文学感染到了这份时代气息,自然就容易充满活力。进入1980年代末期,对新时期欢欣鼓舞的期待遇到了阻碍,兴头慢慢降下来,人逐渐变得恹恹的,小说也就难免感染了病废的气息,加之创作上现代派小说携带的阴郁成分日益加重,那种曾经非常鼓舞人的活力在小说里就逐渐减少了,连爽朗的笑声都要在小说里消失不见了。读这类作品多了,我经常会回想一下当年读《平凡的世界》的感觉,来抵御那扑面而来的颓丧气息。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我当然不只是在少年时期读过《平凡的世界》,那套绿色封面的四卷本,一直好好地躺在我的书箱里,我也在前几年鬼使神差地拿出来翻了翻。这次翻阅留给我的印象很差,不用说其中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法了,单单作品里未经检验的社会期许,不曾节制的激情,泥沙俱下的粗糙文字,就让小说显得非常陈旧。就因为这个原因吧,我终于未能完整重读一遍。后来,这次不好的印象就经常性地被我忽视,谈起《平凡的世界》,我更多地记起的,是那个到处生机勃勃的少年时代。
以上的印象或许表明,《平凡的世界》是一部跟时代缠绕在一起的小说,它因感受时代的气息而传达了那个时代的向上冲动,却也因为这冲动未经淘洗而在时过境迁后显得陈旧。从这个方面看,与时代冷静地保持适当距离的《繁花》,可以看成《平凡的世界》一个有意味的对照。
《繁花》与时代的距离,最典型地表现在它的观看视角上,这个有趣的视角,是客厅。当然,客厅只是个比喻,与其对应的比喻,是街道和卧室。现代中国最常见的,是专注于街道的小说——革命,流血,口号,标语,传单,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化大王旗……大部分时候,符号的指涉都有规范的指向,只要在阅读中看到几个典型符号,就不难判断这时的街道属于哪个时期。即使作品致力于写人物,也往往不过是随着街道符号起伏的标签,并不具有自为的空间。甚至事涉私密,街道上的喧闹仍然响亮地传来。
与“街道小说”对应的,可以称为“卧室小说”。这类小说恨不得把街道完全摒弃在作品之外,只专注于卧室的角角落落,以此刺探欲望,深挖人性,对卧室内的各类描写百无禁忌,人物如茕茕孑立的纸片人,所有的活动只证明了作者对欲望的探索深度。
在《繁花》以客厅为主导的视角里,退可以窥探卧室,出可以观察街道,而又能与卧室和街道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成为一个合适的内外转换器。客厅还连着厨房,厨房里烟熏火燎的味道,也不时散发出来。《繁花》对吃吃喝喝的热衷,对卧室偶尔的张望,都有着客厅视角的典型特征。而对卧室里的种种,《繁花》保持了一种明确的克制,它只交待事情的发生,偶尔也简单地点染几笔,但并不极力描写,也不深挖下去,点到即止,故事,仍然是在客厅里讲得出口的。
爱默生说:“连贯一致是庸人骗人的把戏。”场景不断变换的《繁花》,显然对连贯一致兴致不高。在这本小说里,很难找出一个贯穿全书的情节,只有挨挨挤挤的一件事连着另一件事,一个人引出另一个人,一场对话紧接着另一场对话,牵牵连连,似断非断。读《繁花》,仿佛在看一台不停改变频道的电视,不断变换的节目各自为政,不相关联。要陪伴这些看似无关的节目很长时间,才能渐渐发现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慢慢积聚起来,在脑海中形成某种特殊的印象。在《繁花》里,上海这座城市的现代特征和自然景致,以至浓浓的居家气息,自然而然地收拢在一起,酝酿,发酵,传达出世俗的深味。而那些登场的人物,也在这样的环境里活泛开来,起床,伸懒腰,化妆,然后大大方方地走进小说的正文。最终,《繁花》中看似散漫的记载,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氛围,这种独特的氛围又反过来安置着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最终两者完满地结为一体,呈现出丰厚的生活样态。
这样的书写方式激活了上海的体温与脉象,把这座城市从干枯冰冷的符号系统中还原出来,显示出内在的活力和神采。这样一座城市,不理睬理论赋予它的抽象命名,它是人物的置身之所,生存之地,因为居住日久,人就跟这座城市生长在了一起。这样一座城市,其实就是我们存身的世界,并不是那个在小说中久已被披挂上坚硬外壳的,叫做城市的异类。或者可以这样确认,《繁花》深入了所写城市的细节,看到了这个城市深处的秘密,并让小说的讲述者也变成了这个城市的组成部分。
这种对一座城市的喜爱乃至沉迷,让《繁花》接通了异于现代城市小说的另一个文学传统。早期欧洲所谓的城市文学,是与中世纪的宗教和骑士文学对立的创作,主要描写市民的日常生活,围绕市民关心的问题展开,鲜明的世俗色彩是其基本特征。我们熟知的古代小说,长篇的或成规模的,如《西游记》《金瓶梅》《封神演义》、“三言”、“二拍”、《海上花列传》等,无一不是以描写世俗为主,并且是要世俗之人来读的。《繁花》进入的,正是这一久被淡忘的世俗的城市文学序列。
从这个意义上看,《平凡的世界》魅力的逐渐消失,就不只是因为我上面说的写作上的问题,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过去之后,人们已经很难感受到弥漫其中的特定气息。《繁花》则因为接通了一个更为深厚久远的传统,有更多、更复杂的时代气息复合在小说之内,让人在阅读时会在总体的安静感觉之中听到轻微的响动,就像春天里青草生长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