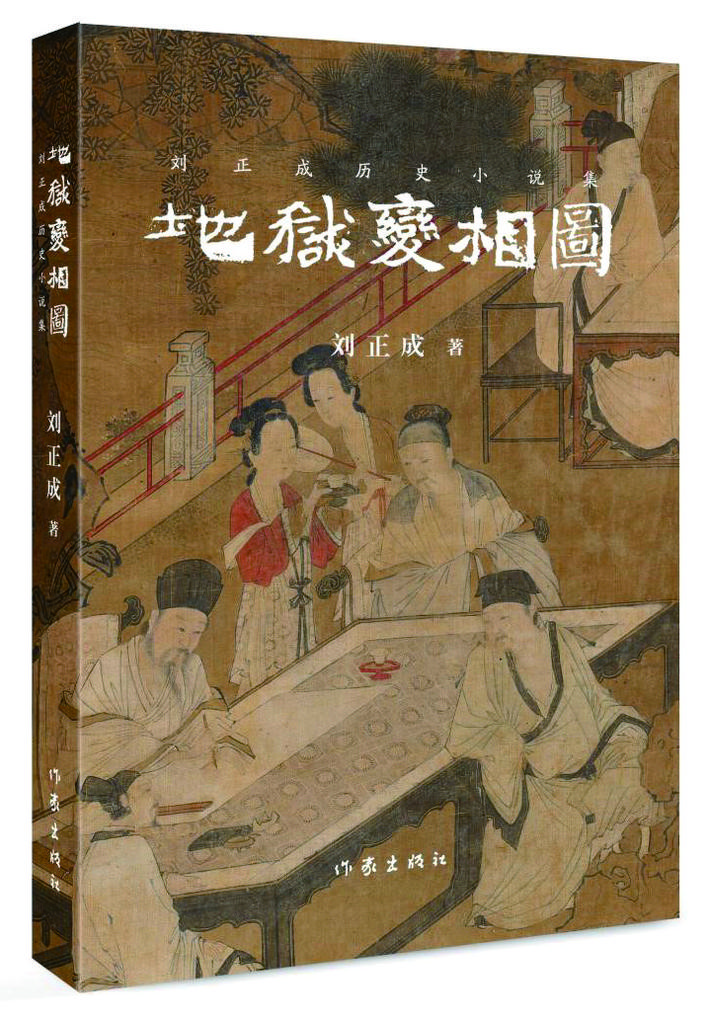
胡适之先生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名文《实验主义》中,介绍詹姆士实在主义哲学思想时说过:“实在是我们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此后演变成流传至今的名言:“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所谓“实在主义”与“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论坛上有多大差别我并无研究,但对于同样关注“实用主义”的胡适之来说,在这里他关于历史的观点还是很有意义的,并且到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例如,当下热播的电视剧节目中,撇开“抗日神剧”这种历史片不说,唐代、明代,尤其是清代宫廷剧的片目均统治着屏幕,这些热播的“戏说历史”无比夸张地把胡适之的名言由哲学领域置换成了社会学领域消费文化的代名词。因此,我在三四十年前写的这些历史小说已经分别由重庆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结集出版了两回,现在又承蒙作家出版社厚爱原封不动出版第三次之际,我要郑重声明绝非在追赶这个时尚热潮。恰恰相反,我也许在向“戏说”时代表达异议,在提醒大家自鲁迅写作“新编历史小说”和郭沫若创作“新编历史剧”所开创的现代文学史新传统中,还有一个在今天看来已成阳春白雪的历史文学领域存在着,并曾经是文学主流的组成部分之一。早已在英语世界蜚声半个多世纪的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不论,单从1949年以来,也有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吴晗《海瑞罢官》、姚雪垠《李自成》、蒋星煜《海瑞》等好小说好剧本载入文学史册。
当代著名诗人、文化学者吉狄马加先生在所赐之序中用了一个颇为生僻的成语“缟夜炫昼”为题,而道理却十分显豁。宋人杨万里《读退之李花诗序》云:“因晚登碧落堂,望隔江桃皆暗,而李独明,乃悟其妙,盖炫昼缟夜云。”王安石亦有《寄蔡氏女子诗》云:“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吉狄马加先生认为,“过去的历史是人类的秘密,而关于历史的小说是秘密中的秘密,是人类生活的胜境,那里有无限的风光等待我们去领略。”他把它比喻成春天里的娇艳桃花可以炫耀于白昼,尤其因为有洁白的李花可以照亮黑夜——缟夜,可谓至言,可谓知音!他认为,历史意义上的真实是有“缺口”的,而美学意义上的真实是“更高意义上的真实”,这把我的历史小说的价值是拔高了,但他的这种价值判断方法却是至理。
陆九渊曾提出“心即理也”,还说“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守仁则进一步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王守仁所说的“心”,指最高的本体,如说“心即道,道即天”。中国传统中的宋明理学被“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给糟蹋了,尤甚是王阳明的心学被扣上“唯心主义”批臭了,但在今天看来,它与前沿现代物理学——量子力学和古老的佛学对本体的认知均成了显学。如果说“戏说”历史是关注了可能发生的风流故事,形而下的声色之乐获得大众热捧,这种形而上的关注内心世界的认知寻求是否亦可以在“小众”群体里显现于世?出版社担心此书的市场受众,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象过我的历史小说可以像金庸的《神雕侠侣》《鹿鼎记》那样疯狂热卖,真那样这世界就真正奇怪了!但是,鲁迅先生可以借来自嘲的一副对联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本再版书还未出版之际,既然已经得到吉狄马加先生“一知己”,某夫复何言!
我在二版序中曾以“重读旧文章”为题,我也不能忘记一些旧人旧事,也就是当年赏识我的历史小说的三五个人。第一个人是我的文学老师、《四川文学》编辑,今年已逾九秩的刘元工先生,没有他的认可与鼓励,我的历史小说处女作《怀素自叙》也许不能在《四川文学》发表并从此开启此条创作之路,这可以从他为我写的初版序《我乐观地期待》看出来。刘元工先生本人是小说作家,他195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后,就被他的老师、著名作家沙汀调入西南文联,历任《西南文艺》《红岩》《峨眉》《四川文学》编辑,可以说他是四川当代文学史的见证人。第二位知音乃是已故老作家高缨,他看到我的处女作后异常兴奋地鼓励我照这个路子写下去,当年这对一个青年作家是多么重要啊!还有两位知音,一位是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另一位是已故四川老作家杨牧先生,他们的表达均颇有戏剧性。流沙河先生当年是《星星》诗刊的老编辑,我是《四川文学》的新编辑,我们四川文联盘踞在成都布后街熊克武先生的故居里,他在前院与作家协会为邻,我在后院与沙汀、艾芜二先生居所为邻,大家很少往来。有一天他突然从前院来到后院找到我,对我说了一句话:“正成,读了你的《地狱变相图》,我对你刮目相看!”从此我们成了谈友。杨牧先生是四川作协专业作家,他与流沙河先生一样被打成右派,是“左联”时代的老作家,平时不来机关,也是突然到《四川文学》编辑部找到我,问我家住在什么地方,要上我家里来喝酒。他一边喝酒,一边眉飞色舞地大谈我的几篇历史小说,我在猜想是不是有搔到他老先生什么痒处了,浇了他的心中块垒?我怯怯地说,我在学陈翔鹤先生的历史小说。他砰的放下酒杯,拍了我一巴掌厉声道:“你比陈翔鹤写得好!”陈翔鹤先生是川籍老作家,“文革”前即是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我的偶像。我讲这些旧事,并非借此抬高自己之意,而是一直在琢磨自己的写作分别在哪一点上激起了这些前辈老作家的心中涟漪,竟忍不住屈尊来找我倾谈?
关于这一点,吉狄马加先生在他的序言中似乎也为我作了精彩的回答。他说:“刘正成结集出版的历史小说一共有八篇,篇篇皆有极花峰转之处。每篇看似写历史人物,其实也是站在文人在场的角度与方位,对人们内心的一次次超越与观照。”我在二版序中交代了写作这批历史小说的时代背景和心路历程,这个时代背景即是“文革”后几代文艺家对所经历苦难的刻骨铭心与共鸣,这个心路历程即是我对“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模式的扬弃和文体的个性化追求。前者容易理解不用赘述,关于文体问题我想多说几句。
我熟读过《庄子》内篇、外篇的所有文章,我说庄子其实是2000年前最伟大的小说家。他所有的哲学观念都演绎于他所叙述的寓言般的故事之中,记不清古代哪一位文艺评论家说过,也许是金圣叹吧,他说庄子的文章会“飞”。《庄子》所叙述的一个个“故事”的情节与结构特征确实在“飞”。所谓“飞”,即是它并不遵从他所描绘的故事情节、细节循序发展,而是遵从故事人物即庄子本人内心逻辑跳跃前行,让人感觉像飞一样。当代音乐中有“小众”趣味的流派,比如曾风靡于20世纪30年代的爵士乐,一些上了年纪有老上海经历的人现在总爱去外滩和平饭店咖啡厅听老派爵士乐,演奏者似乎也是当年人物装束,让人陶醉迷离。大家想想离世不久的陈逸飞在他的油画中所塑造的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那些历史人物,让人回味无穷叹为观止。为什么?有这样阅历和人生经验的人不需要你一五一十地去讲上海滩故事,他会一点九头窍,去品赏其中韵味。
佛教思想在阐述六道轮回要义时有句话,叫“人心即地狱”,这与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近义。我的《地狱变相图》也曾获过奖,峨眉电影制片厂和西安电影制片厂都曾约我把这篇历史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我均拒绝“触电”。人心的思维跳跃如电光石火莫名其妙,我无法用严丝合缝的故事情节去复制,如同吉狄马加先生在序言中引用《半山唱和》中王安石和苏东坡的禅宗偈语对话一样,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者也!这或许就是传统文体中草蛇灰线似的《南华经》一脉?
当然,在今天知识爆炸的年代,聪明细心的年轻人亦可以成为我的知音,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人心与人心之间真不能触发和共鸣,人类就不会有理性存在了。我向读者提一个建议,不要把我的历史小说带到迪厅去阅读,而是带到公园茶馆去消遣,在平心静气的环境中,也许我将获得许多没有阅历却又无比聪慧的青年读者知音。哈哈,我期待着!
(摘自《地狱变相图:刘正成历史小说集》,刘正成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