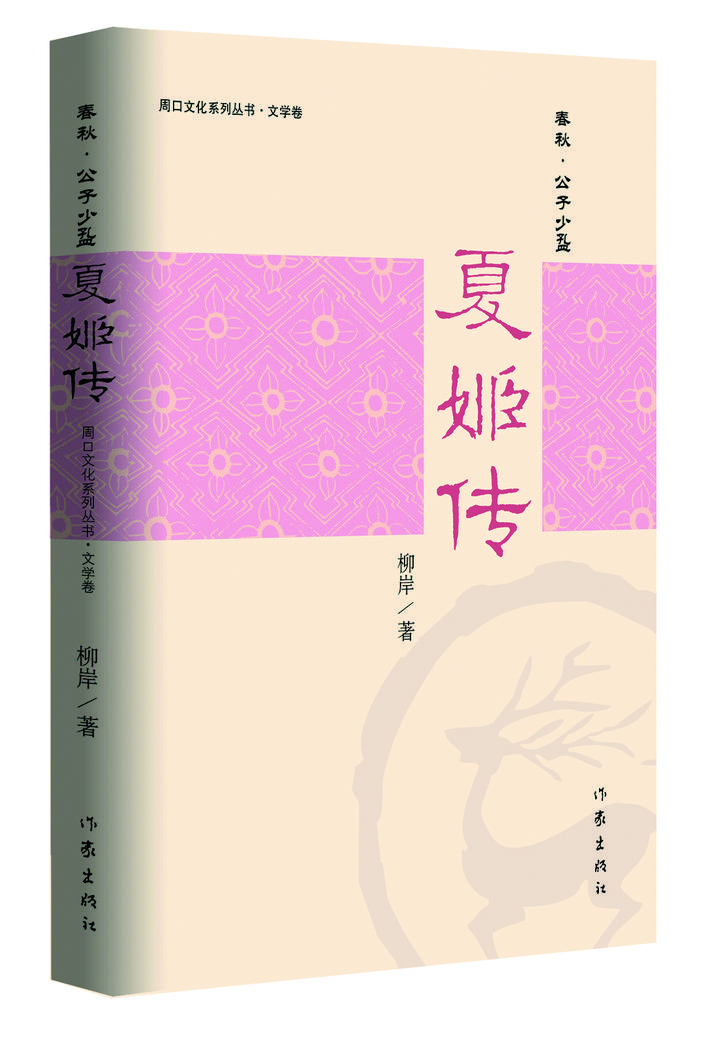
中国历史上,夏姬被描述为第一妖姬,第一艳妇,她美艳动人,曾与多位诸侯、大夫通奸,引出一连串历史事件,“杀三夫一君一子,亡一国两卿”,成为一种特定的人格与文化符号,近似于西方的海伦。海伦故事其实没有夏姬故事丰富生动,但因一部《伊利亚特》四海皆知,所以,中国也应该有类似的著作。柳岸这部长篇小说《夏姬传》,就是今人为夏姬纪传的一种努力。
仅就题材而言,估计这部作品也是不缺乏读者的。
男欢女爱,历来是文学创作无法放弃的描绘内容,它是人的感性生命冲动的投射。实际上,只有文学作品,才能将这一对象淋漓尽致加以表达,这是因为,文字激起的想象,以及心理刻画的细腻书写,才能使这一对象得到较全面的呈现。
然而,自从人类组织为群体后,男欢女爱便不再简单表现为生理的宣泄和繁衍的需求,被赋予种种社会与文化的束缚和规范,每个时代的人们,遵从着不同时代价值观的制约,对两性关系做出不尽相同的评价。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又需要不断回溯历史,以现世的目光反省人类自身的文明与演进。
于是,夏姬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公子少即夏姬。写公子少前,柳岸写了《公子桃花》,挖掘和塑造出古陈国息夫人即息妫的形象,其间接触到夏姬的事迹。息妫是春秋中早期人,夏姬是春秋中晚期人,两人都是陈国人。而且,与夏姬近似,息妫也是海伦式的人物,因其美貌改变了历史,先后有三个国君和一个大司马倾情于她。她嫁过两个国君,大司马向她求爱的时候,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后来,作者发现,把她们再加上春秋早期的文姜、春秋晚期的西施,四位传奇女竟可以勾画出一部春秋史。她于是制订了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春秋名姝——四位传奇女,一部春秋史”,《夏姬传》即成为计划实施的第二部作品。无论如何,应该祝贺柳岸的发现和绝佳的创意,她的工作将重建对春秋时期四大美女的认知,有助于再次燃起人们对春秋历史的兴趣。某种程度上,四个女人可被视为四位形象大使,她们周身散发着那个时代才具有的浓郁气息。感受这些气息,可以从另一方面体会到春秋年代的真实社会氛围,生动地进入历史场景。
我们已经看到,《夏姬传》的写作是颇为扎实的,下到了功夫。柳岸书写夏姬,并不像通俗小说家们那样肆意生发,而尽量做到笔墨所及皆有出处,想象与铺陈也只是依据史料提供的线索合理发展,这首先就赢得了读者之“信”。她再现历史,严谨周全,使作品成为一部集中在陈、郑、楚、晋、宋等国范围内的春秋断代史,仅此一点,已使这部书具有重要价值。当然,小说主要是通过夏姬和围绕着她的男人们的纠葛写历史,包括历史因她而发生的转折,就更使历史叙述化入文学的魅力情境。
还应该注意到两件事。其一,作者柳岸为女性;其二,作者自己也可以算作陈国人,她生活在周口。这两个因素,解释了她为什么想写夏姬与息妫,也使她的写作有得天独厚之处。
读者可以注意到,柳岸笔下的夏姬与男人笔下的夏姬是不一样的,男人们渲染夏姬的“淫”,而柳岸重视夏姬的本真、率性、自由与爱,是对这位传奇女子的一种重塑。
要知道,夏姬生长在“一个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转轨时期,没有儒家对女人三从四德的要求,没有贞节烈妇的婚姻观,没有汉对先秦的收敛与规范”,故此,她没有“从一而终”“一女不事二夫”的思想。这一点,从书里所有君主臣子对她的态度上也能看出。他们对她皆十分钟情,但没有谁计较过她曾经有过几个男人(读者也不至于批评作者这样写)。同时,夏姬也未曾计较过君臣们有三妻四妾。她甚至主动将自己的女仆荷花配给丈夫夏御叔,后又把荷花收入丈夫屈巫房中,做得心里毫无芥蒂。实际上,早在她还是少女时,就与堂兄公子蛮有过恋情,她的叔叔公子宋也未因她是同宗血亲的晚辈而放弃对她的追求。这正说明,春秋之风,是带有野味的,很是开放。作者见怪不怪,平静地娓娓道来,将人们带入远久真切的古风之中。
这还意味着,春秋年间的人们只是放荡不羁,全无道统,那时候的婚姻,遵从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书里也写,夏姬的儿子夏征舒长大后,听到株林民歌,眼见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君臣三人同时与母亲有染,并在庙堂之上炫耀,深以为耻,后怒不可遏,将陈灵公在株林庄园射杀,便说明夏姬的有些行为在当时也是难以见容于世的。以后,楚王熊侣捕获了她,被她的魅力所倾倒,一度想将她纳入后宫,被屈巫劝阻。而后,楚王将她赐予老鳏夫襄老,她也没有抗拒。这些,都容易引起人们侧目。不过细细来读,又可知晓,在陈国,夏姬先与孔宁相好,是由于夏御叔身亡,“多亏了孔宁帮忙,才能勉强维持夏府日常用度”;她厌恶陈灵公的腋臭,却还愿委身于他,缘由是逃不过他的掌控。为了救儿子一命,她也曾期盼自己打动楚王,纳入后宫;嫁给襄老是无法抗拒楚王赐婚。就是说,在毁灭还是委曲求全的选择之下,她选择了生存。对于一个弱女子来说,这本无可厚责。
至于对待仪行父,却有不同。史料记载仪行父身材高大,鼻准丰隆,来亲近她时,使她心生好感。以后仪行父广求助战奇药献媚于她,令她心津摇荡,这大概属于她真正的“淫”。而这个淫是要加引号的,出自女人的自然需求。重要的是,书内写得很清楚,在婚姻中时,她并无绯闻,“桃色事件”只出现在她居寡期间。其实,那时她愿与谁交往,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都与他人无关。很难说她爱过仪行父,只是喜欢而已,夹杂着性爱的因素。性爱与情爱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夏姬的观念太大胆,也许表现在,她有时能重在享受性爱,这成为她好“淫”的证明。于是很难说,以后她与多个男人的交往,都只是出于现实考虑,并不夹杂欲望的诱惑。回避这些,也写不出夏姬。
但柳岸更深刻地写出了一个绝色女子的无奈与宿命。她太迷人,倾国倾城,近50岁也惹男人发狂,只要她出现,就会生出争夺,甚至引起战争,正所谓红颜祸水。可是像她这样美丽的女子世间罕见,本身便容易成为事件,但发动事件只能归罪于男人们,她并没有策划过一场战争。
柳岸对夏姬的写照,最尽力在对她爱情生涯的描述。夏姬是有爱情的,自少时春浴节上相会,她便朦胧地爱上了后为楚国大臣的屈巫,以后两人几次得机会相见,结下难解之缘。可以感觉到,书中有两种文字,每当写到夏姬与屈巫时,作者的文字便飞扬起来,温馨细腻,华丽悠远。一部《夏姬传》中,屈夏之恋成为贯穿始终的故事主线,双方关系曲曲折折,备经磨难。屈巫为同夏姬圆梦,处心积虑,终于不惜背叛楚国,与夏姬私奔;夏姬一度误解屈巫用心,几欲含泪将其毒死,后嫌隙化解,不顾一切随屈巫投向他国。整个经历起伏跌宕,感人颇深。显然,柳岸认为,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夏姬,一个终身追求至爱的春秋女子,她有过的一切苟且风韵,大都只是身不由己。于是,夏姬在柳岸笔下得到完整的复活。
这不是作者一厢情愿的编排,史实记载也是如此。自夏姬跟了屈巫奔往晋国后,便再未传出任何绯闻(如果有,一定会留下记录)。她在40多岁上还与屈巫生下一女,其女后嫁与晋国著名贤人叔向。大约,夏姬的结局是幸福的,她得到了一个女人真正想要的东西。作者想说,爱情,才是女人心中至善至美的圭臬,不论是谁,也不论男人愿意怎样想象。
这就是柳岸带给大家的一部殊为难得的作品。它很值得写,也耐人琢磨,打通了春秋与现代的隔膜,沟通起历史长河中人类绵延的情愫,意味隽永。柳岸抓住了好的选题,人们有理由对她“春秋名姝——四位传奇女,一部春秋史”的第三部《文姜传》(公子青鸾),第四部《西施传》(越女夷光)怀有期待。
(《夏姬传》,柳岸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