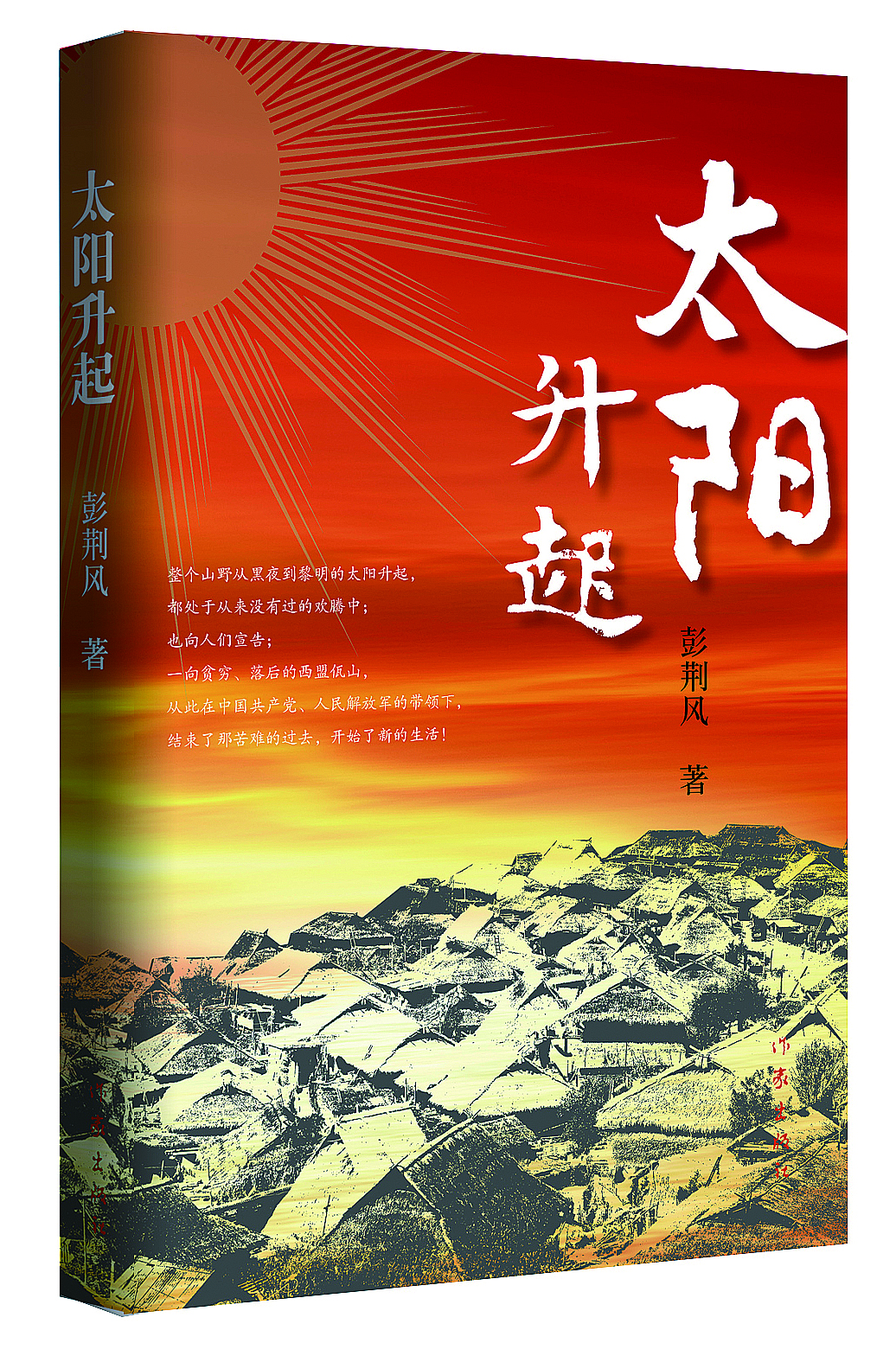
1952年夏秋,我们步兵第一一五团二营,结束了澜沧大黑山的剿匪战斗后,在黑山附近的小集市新营盘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又奉命在12月初,进军西盟佤山。 西盟佤山是个聚居有六万余佤族人、山势险陡的边陲要地,如今正被匪众屈洪泽部占据。
1952年冬进军西盟,是人民解放军第二次解放西盟。
一年前,当时的中共澜沧县委,曾派出区长唐皇一行十余人,进入西盟去建立区政府。由于人枪过少,又缺乏在佤族地区的工作经验,唐皇等人进入西盟不久,就被匪首屈洪泽啸聚境内外千余名反动武装围攻。唐皇等人在苦战几天后,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西盟又沦于敌手。
盘据西盟佤山的匪军屈洪泽部,约有七八百人,平日还能耀武扬威,一得到我人民解放军将进攻西盟的消息,自知力量对比悬殊,哪里还敢抵抗,在我军还未攻抵西盟前,就急忙利用浓雾的掩护遁往境外。 于是我们部队不发一枪一弹,在1952年12月20日清晨收复了西盟。为了巩固西盟的民族工作,上级特意从部队中抽调了一批干部、战士,组成几个“民族工作组”,派往西盟、大力锁、永别烈、岳宋、马散等部落(这也是后来西盟各个区、乡政府的前身)。 当时我为了写作边地生活,从昆明军区文化部到第一一五团二营五连工作近一年了,对边地民族工作已经有所熟悉。我就被抽调出来担任营教导员兼西盟工委书记侯立基的“联络员”,背着一支卡宾枪、四颗手榴弹,依次去各个“民族工作组”了解收集材料,然后在月底回到西盟,向侯立基汇报,作为他一个月召开一次工作会议的参考。
侯立基同志说:这样我可以在会议前,就了解各个 “民族工作组”的近况,你也可以获得大量的写作素材。 有这样的深入生活条件,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这也是后来的一些作家临时去佤山采访所不能比拟的。
我也从中感悟到,生活极其丰富多彩,作家不仅要积极投入,还要在工作中加强了解,用心思考,才能够比一般的人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其中的特异之处。 这“特异之处”也就是其中不同一般的故事、人物、事件。
所以那几年,我能够比那些只去西盟采访的作家、记者了解得深入、透彻,写出了短篇小说集《边寨亲人》《卡佤部落的火把》等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并与人合作了电影文学剧本《边寨烽火》《芦笙恋歌》,从而成了早期云南边地文学创作的主力。
有这样良好的生活条件,我本来可以写得更多更好,但不幸的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一起,我被那几个自己有“右派言论”的军区文化部领导人所陷害,沉入“右派”的陷阱22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劳动改造”中度过,既不能正常去边地生活,更不能写作。直到1979年冬得到平反,才重新回到文坛。但是身心被长期折磨后,已经极为憔悴,又得费很长时间去慰藉、调整。这真是作家的不幸! 所以,我的创作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2年春至1957年秋,第二阶段是从1979年冬重新开始。
在那22年间经受了包括7年监狱生活的折磨,在年过半百后,身心大不如前,我还是经常带病深入边地生活、写作。 这很艰难,但是因为我能尽力拼搏,在1979年至2018年的30余年时间里,仍然出版了长篇小说六部、长篇纪实文学4部、中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8部、散文集两部、评论集一部,还有大量的短篇小说、随笔待辑录成册。
这些作品多数发表在全国有影响的刊物上,并获得国家级的重要奖项:如短篇小说《今夜月色好》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红指甲》获得首届“金盾文学奖”,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另外几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滇缅铁路祭》《旌旗万里》《挥戈落日》,不仅填补了中国文学全面、系统描述那几场大战役的文学空白,还因为材料丰富,描述生动,深为关心那段历史的专家和读者所称道。
但是经常使我念念不忘的还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辟西盟佤山的工作经历,那是云南边地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壮举。
过去的西盟佤山,由于佤族对外民族过于畏惧、警惕,一向是与外隔绝,很少与别的民族交流;对内则由部落的大小头人简单、粗暴地统治。政治、经济长期处于保守、贫穷落后的状态。直到1952年冬,人民解放军向西盟佤山进军,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才得到大的改变。
如何真实、详尽地描述从1952年冬以来,那一段既艰难又极有历史意义的变革过程,一直是我这个曾经参与进军西盟、并在那里的几个民族工作组工作过的亲历者的愿望。关于那段往事,由于各种原因,我的这一写作计划耽搁了60余年,也思考、梳理了60余年,如今才形成了这部长篇小说《太阳升起》。 我真实地叙述了佤族人苦难的过去,也形象地叙述了佤族人在内外压迫下苦苦挣扎的状况。虽然有些事件,在过去是所谓“写作禁区”,但是为了把历史的真实呈现给后来人,我还是按照历史和生活的真实状况作了描述。这虽然比较麻烦、又有风险但这是一部描述处于特殊地域、特殊民族、特殊时代的作品,不大胆面对真实,就会使这一作品失去其不同于一般的意义。
如今长篇小说《太阳升起》,终于在我90岁时完成。虽然时间过去多年,回忆、整理那些历史事件,并演化成文学作品是一项颇为吃力的事,我还是坚持利用对云南边地的了解,以及多年写作的经验,尽力写好这一作品。
我把那段在西盟佤山的工作往事,在记忆中保存了60余年,是因为那段历史太精彩、太不同一般了。现在好不容易写出来,这是用心提炼、剪裁后的故事。我相信,即使是如今身在西盟佤山的年轻读者,在读到这些60余年前的事时,也会惊讶那年月的西盟佤山怎么会那样与世隔绝,社会的变化是何等不容易!
如今的西盟佤山已经跻身于正在发展的现代社会,与全国各民族共同前进,这当然是过去和现在在西盟佤山工作的人们辛勤劳动的成果。 这是一本用文学方式描述特殊的边地、特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书;我想,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一定会深感真切而有兴趣!
(摘自《太阳升起》,彭荆风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