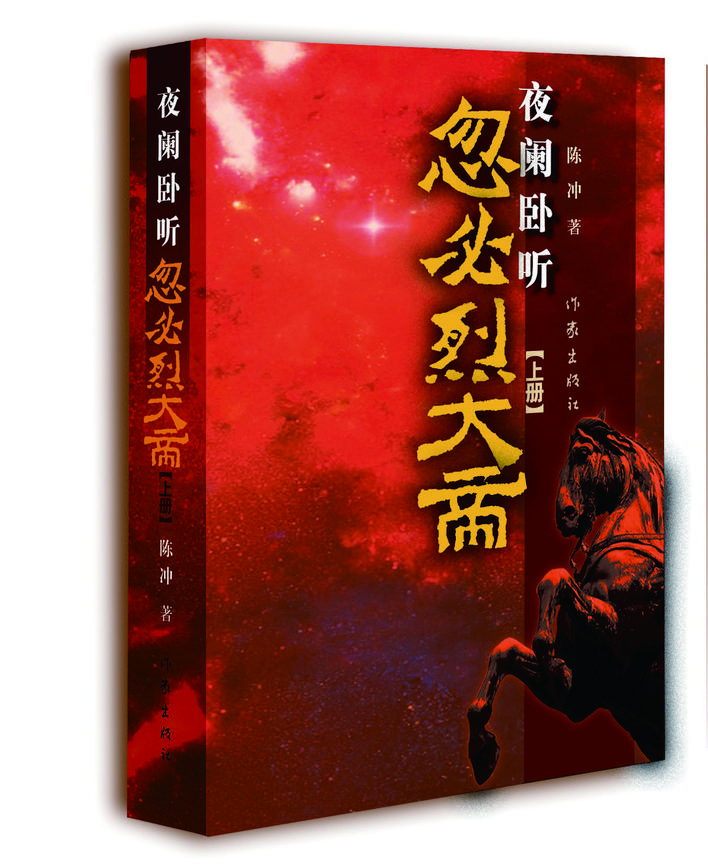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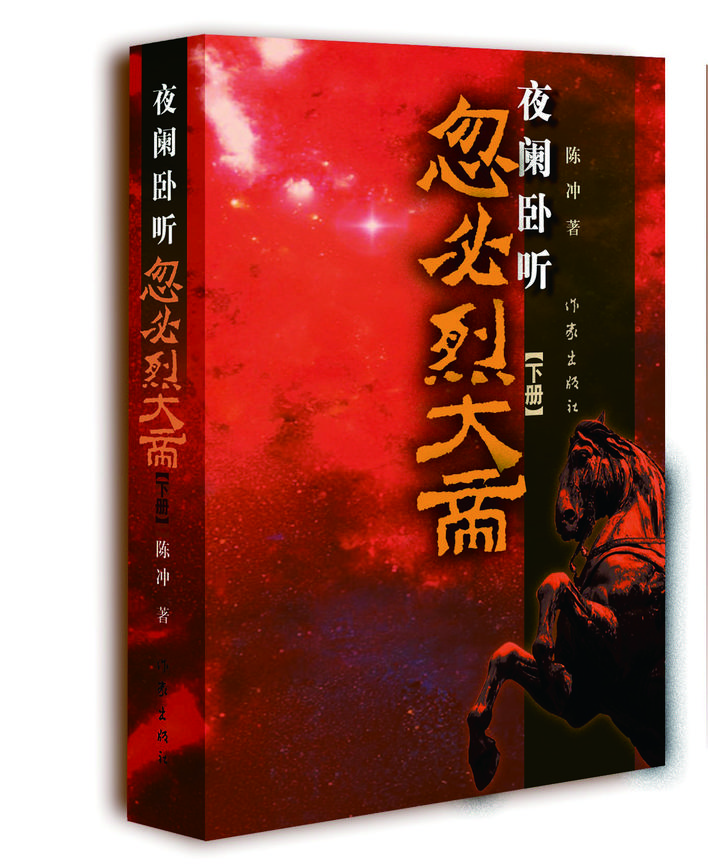
所有的故事都是因忽必烈而发生,而存在。他年轻时的一句“思大有为于天下”,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天下。而当天下被他改变了以后,他的生命轨迹也变了。曾经几乎战无不胜的他,在崖山海战之后,再也没有在战场上取得过真正的胜利。
他多次派遣规模不同的军队远征东南亚诸国,包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等国,战斗互有胜负,但最后总是又被赶了回来。尽管这些小国最终都一度成为大元的属国,但主要都取决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的政治权衡,而不是战场上的胜负。
他的第二次远征日本是在至元十八年,即公元1281年,同样以失败告终,而且败得很难看,几乎全军覆没。它还是一场在政治上受到严重质疑的战争,因为人们怀疑,以他的识人的眼光,挑选范文虎来担任远征军中汉人部队的统帅,是不是压根儿要的就是一场大败仗。这支部队其实是由“南人”,即原南宋的降军和俘虏组成的,而在远征中又被用来作为主要的作战部队。忽必烈创造的这个模式被后世继承下来,每当一次内战结束,胜利者就把失败方的降兵和俘虏,用于一次胜负难料或关系不大的对外作战,把他们消化掉。
而真正残酷的战争是在蒙古人之间——或者不如说是在成吉思汗的孙子们之间进行的。那些与忽必烈为敌的蒙古人,虽然不相信儒学,也没受过正心教育,但显然比南宋政权难缠得多。伯颜为他打了不少胜仗——单论两军对阵,他们没人能成为伯颜的对手。伯颜打败了昔里吉的军队,但昔里吉是蒙古人,不会像汉人那样死守某一个地方,他的背后还有辽阔的草原和沙漠。在有关这种战争的记载中,对胜利者的描述总是把敌人赶到了哪儿哪儿,例如说“伯颜在鄂尔浑河畔打败了昔里吉,把他赶回到也儿的石河畔”。打了胜仗不等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昔里吉叛乱的最终解决,还是因为叛乱集团发生了内讧。昔里吉、脱脱木儿和撒里蛮之间发生争吵,昔里吉处死了脱脱木儿,然后撒里蛮活捉了昔里吉,向忽必烈投降,并把他交给了忽必烈。海都比昔里吉们更难缠,而且在性质上也更高阶——那是窝阔台家族与拖雷家族之间的不可调和的争斗。为了对付海都,忽必烈甚至在72岁高龄时还御驾亲征,在满州打败了海都的盟友、以乃颜为首的几位成吉思汗的侄孙子,生俘并处死了乃颜。因为是成吉思汗的侄孙,乃颜受到了优待——可以不流血地死,所以他是被用毡毯闷死的。但是这对海都的影响并不大。他仍是杭爱山以西的西蒙古和突厥斯坦的君主。忽必烈派他的孙子甘麻刺去守卫杭爱山边境地区,结果却被海都打败,并被围困在色楞格河附近,好不容易才得以逃脱。已经73岁的忽必烈,决定亲自前去扭转形势,听说海都已经“远遁”,也就是说你要打他得到很远的地方才打得到他,只好作罢。忽必烈终其一生,也没能看到海都的失败。
至元三十一年,即公元1294年,忽必烈撒手归西,在位35年,享年80岁,要算相当地高寿了。也正因为这个,他十分喜爱并早早就被他立为太子的真金,却先于他去世了。他册立太子,意味着已经废除了成吉思汗建立的库里勒台制,改用汉制了,但在真金死后,他并没有按汉制在众王子(他共有10个儿子)中另选一人为太子,而是将原来属于真金的“皇太子”印玺,转授给真金之子铁穆耳,相当于册立他为“皇太孙”。这或许是因为他太喜爱真金了,但也可能是出于对那木罕的失望。那木罕虽然被放回来了,可是有了那样的经历,也确实不太适合当皇上了。但是铁穆耳是真金的第三子,并非长子。这也不符合“传长不传贤”的汉制。无论如何,忽必烈终是开国之君,自有其权威在,铁穆耳最终还是继承了皇位,是为成宗,只是那过程已经算不上一帆风顺,因为受到他的胞兄、真金的长子甘麻剌的挑战,曾经出现过“神器虚悬”三月之久的僵持局面。而在位13年之后,到了他交班的时候,麻烦可就大得多了。他也立了太子,但那娃娃没福气,先他一年多死了,而重病之中他也没来得及再立太子,驾崩之后,就又出现了一个皇位虚悬的局面。临时摄政的皇后卜鲁罕,联合了掌握实权的左丞相阿忽台,准备拥立成宗的堂弟阿难答,因为他是忽必烈诸孙中年龄最长者。这个标准一听就不靠谱。这时有个叫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是成宗的亲哥甘麻剌的小儿子,与其母答己以奔丧为名回到大都,带领卫士闯入内廷将阿忽台和阿难答逮捕并处死。这次出奇制胜的政变,保住了皇位留在真金一脉,也使他距皇位只有一步之遥,可是这时他的哥哥海山也来奔丧了。海山奉成宗之命在青海一带守边十年,军功显赫,部众精良。他名为来奔丧,却是带着三万精兵来的。五月,大军进至上都,眼看又一场“两都大战”一触即发,多亏这哥儿俩的母亲答己出面,派人去上都与海山谈判并达成协议,先由海山当皇上,立其弟为“皇太弟”,叫“兄终弟及”,等弟弟当了皇上,再立哥哥的儿子为“皇太侄”,叫“叔侄相传”。海山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皇位,是为武宗,登基后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他的亲叔伯婶儿卜鲁罕皇后杀了。他在位4年,其间也曾想废了“皇太弟”,立自己的儿子和世为太子,但受到右丞相康里脱脱的坚决反对,只好维持原状。康里脱脱是达成那个协议的谈判代表,维护协议的执行也在情理之中。
一个大臣不按皇上的意思办事,尽管有理有据,终究不合常理,早晚有顶不住的一天,幸亏武宗“好内”,只当了4年皇上就一命呜呼,爱育黎拔力八达得以顺利继位,是为仁宗。仁宗在位9年,有足够的时间闪展腾挪,废掉了“皇太侄”和世,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并且把皇位传给了他。他即位时年方18岁,是为英宗。
英宗被认为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皇帝,他能得到“英宗”这个庙号也说明了这一点。但他所实施的一些改革新政,触犯了很多贵族的既得利益,他执政的第三年,在一次由上都返回大都的途中,于南坡店被人刺杀,史称“南坡之变”,享年20岁。
遇刺身亡的皇上年仅20岁,显然没来得及对身后之事做出安排,诸王大臣等拥立也孙铁木儿为帝,改元泰定。也孙铁木儿是甘麻剌的儿子,血统上也还说得过去,如果在位时间长,有可能把合法性的问题摆平,可惜他只当了4年皇上就死了。他一死,就出现了皇位之争。他的从侄图帖睦尔夺取了他的儿子阿速吉八的皇位。人家要建立自己的权力合法性,就剥夺了他的合法性,认定他的即位属于非法“自立”,结果他身后甚至没能得到汉文的庙号、谥号和蒙古汗号,史书只能以他的第一个年号称他为“泰定帝”。
实际上,阿速吉八还是过了一把皇帝瘾的。他本来已被泰定帝指定为皇太子,只是朝中握有实权的大臣知枢密院事燕帖木儿迟迟不立年幼的太子阿速吉八即位,反而把阿速吉八赶到上都,然后在大都拥立元武宗之子图睦帖木儿即位,是为元文宗。不过,有向灯的,也有向火的,一直服侍阿速吉八的丞相倒剌沙,听说大都有了皇帝,就在上都将刚满9岁的阿速吉八拥立为帝,改元天顺。天无二日,文宗派燕帖木儿进攻上都,再次上演了一回“两都之战”,倒剌沙战败身亡,阿速吉八下落不明,不知所终。阿速吉八只做了一个月的倒霉皇上,同样没有得到庙号和谥号,只能称他天顺帝。不过他比他爸待遇稍微高一点,好歹得了个汗号,叫阿里加巴。
燕帖木儿拥立图睦帖木儿的理由,是仁宗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不合法,违背了当初与武宗达成的协议,所以现在皇位应该交还给武宗的儿子。虽说是陈年老账,却也言之有理。问题是图睦帖木儿只是武宗的小儿子,武宗的长子是和世,而且和世还是武宗指定的隔代继承人。燕帖木儿考虑得确实很严密,他宣称因为和世当时远在碛北,而国不可日久无君,所以先让图睦帖木儿即位,待日后将和世迎回,再将皇位转让给兄长。他也真这么办了。遵循天不可有二日的原则,和世先回到哈拉和林,这时文宗图睦帖木儿在大都宣布逊位,然后和世在哈拉和林即帝位,是为明宗。明宗起驾向大都进发,准备去履行他的皇帝职责,走到旺兀察都,遇到前来迎接的逊帝图睦帖木儿和燕帖木儿,是夕欢宴诸王众臣,而当天深夜明宗驾崩,享年30岁。因为没有正式的调查报告,史书只能称明宗暴崩“疑”系文宗、燕帖木儿所为。可怜明宗当了一遭皇帝,却不曾在金銮殿上体验过哪怕一次临朝理政的感觉。图睦帖木儿回到大都,宣布复位,重新做了皇帝。
做过两回皇帝的文宗,两回相加总共在位四年,享年29岁。据说是因为良心发现,死前遗诏将皇位传给了明宗的次子懿璘质班,时年七岁,是为宁宗。宁宗也是个没福气的娃娃,登基后只做了53天的皇帝就病死了,连年号都没来得及改。
到这时为止,元世祖忽必烈之后,39年里,元朝已经有过9个皇帝,进行过10次权力更迭了。
然后就轮到妥欢帖木儿了。他是明宗的长子,宁宗的哥哥。从顺位上说,他接掌江山倒也不算旷外,而从能力上说,文宗没有让他接班算得上识人。与他的9位前任相比,他至少有一大优点,就是活得比较长,享年51岁,在位37年。虽然谈不上有何德政仁政,起码避免了为争夺皇位而产生的那些政局动荡和血腥残杀。他其实也不笨,只是他的天赋不适合当皇上而适合当木匠。他亲手制作的一台时计精妙绝伦,堪称举世罕见的旷代珍品,故有“鲁班天子”之称。把朝政交给大臣们去处理,自己躲在后宫做做木匠活儿,自得其乐。他最后成了大元朝的亡国之君,只能说是入错了行,也没有赶对时间。他病逝之后,得到的庙号是“惠宗”,但后人多称他为顺帝。顺帝这个称呼,是取代了大元的大明皇帝明太祖朱元璋赏给他的。人们愿意采用这个称呼,并不是因为它比“惠宗”更具有合法性,而是因为这个“顺”字确实画龙点睛地概括了他的最值得称道的德行。除了少数几个被自己的权臣逼着交出权力的皇帝之外,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愿意向敌人和平交出权力的君主。用后世的眼光看,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很识时务、很有慈悲心肠、很有政治风度的政治家。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子民时,他选择了放弃,而不是让千百万民众以其身家性命来保卫他的权力。后世大清朝有个叫顾炎武的说:“保国家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不干匹夫们的事,他提前300年就认识到了。
而南宋的赵即“宋主”,也从忽必烈那里得到了相当人道主义的待遇。至大都朝觐了忽必烈之后,他被封为瀛国公,后来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元二十六年(1289),他19岁的时候,忽必烈给了他一大笔钱财,资助他去了西藏。他在西藏萨迦寺出家,法号合尊。在学会藏文以后,他把两部汉文佛教著作《百法明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译为藏文,对佛教做出了贡献,被尊为高僧。到了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不知他脑子里哪两根弦没有接对,写了一首诗,经人揭发检举,报到英宗那里,英宗大怒,下令将他赐死,享年53岁。那首要了他的命的诗,共4句,20个字:“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大略说来,不过是首感怀伤旧之作,语调亦称平和,英宗自己也不是什么好鸟,不让赵活了,说不定另有原因。而后世的一些爱国主义者,却认为这首诗“表达了赵对当年元朝政府无理进攻南宋的谴责”。您看出来了吗?若果如此,赵倒真是闲着没事儿自己找死了。
无论如何,跟他的两个弟弟赵昰即“宋主”和赵昺相比,他总算有过自己的人生,实现过自己的价值,至少没有成为别人借以表现大忠义大气节的道具。
应该说,有一次他确曾与这类角色擦肩而过,是文天祥成全了他。这也是文天祥与张世杰、陆秀夫的不同之处。他是全心全意地忠,不掺任何私心杂念——如果不把“照汗青”仅仅视为一种个人愿望的话。他被俘后,张弘范不敢擅专,向朝廷请示如何处置,忽必烈说,谁家没有几个忠臣?让张弘范待以礼遇,将其解到大都,再耐心劝降。张弘范知道忽必烈的意思,用后世的说法,就是要抓一个死不肯降但死劝活劝终于被劝得愿意投降了的典型。后世的爱国主义者想改变这种性质,说“世祖爱其才”,才不忍杀之,还许诺只要降了,仍用为丞相。这也太贬低忽必烈了。以他的知人善任,怎么可能估量不出这个人的文武才具,估量不出让他当丞相会有什么结果?忽必烈就是想要一个典型。而文天祥被囚禁了4年,任凭忽必烈用尽了千方百计,就是不肯投降。这中间,忽必烈用过一个绝招:让赵去劝降。这使文天祥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而一身正气的文天祥经受住了这个考验!他用的也是绝招,而且有两个。他的第一个绝招是“北跪”。他不是朝着赵,而是朝着南方下跪,跪的是大宋天子,不是大元的瀛国公。他的第二个绝招是连声高呼圣驾请回。那真是声震天地,令人无法不为之动容。“圣驾请回!圣驾请回!圣驾请回!圣驾请回!圣驾请回!圣驾请回!圣驾请回!圣驾请回!圣驾请回!……”绝对不给赵开口说话的机会!一旦赵开了口说了话,无论他说了什么,都会让文天祥处于无法应对之地,同时也有损大宋天子的声誉。若说“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才是值得历史永远铭记的一幕。它几乎涵盖了那个时代忠君爱国理念的全部内容。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八,忽必烈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很明显,这是在走最后的程序。此前,整个劝降工作,基本上是靠那些投降了的原南宋高官们去做的。也只能由他们去做,因为忽必烈也不想让自己的臣僚们认为战败投降是可以接受的选择,所以也不让他们去说这种话。而那些南宋的降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也没有把事情弄好。南宋为什么会亡?就因为它长期施行的那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选人机制,最后选中了这些人。他们办什么事都办不好,这个劝降的事也同样。文天祥已是阶下囚,不足为患,本已没有非杀不可的紧迫性,不投降,关着就是了。促使忽必烈动了杀机的,是这些降臣们的一个建议:能不能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不要求文天祥公开表示归降,相应地朝廷也不正式给他官职,找个地方让他“闲居”,如对朝政有什么想法,可以建言献策。这个建议书还附有说明,说曾向文天祥有所暗示,看来他有可能愿意接受这种安排。这个建议跟忽必烈的意图驴唇不对马嘴,反倒让忽必烈意识到,不能让人觉得朝廷拿文天祥没办法了。忽必烈不需要文天祥建言献策,需要的是一个典型。如果得不到一个经过力劝才肯投降的典型,那就退而求其次,要一个宁死不降的忠臣典型也好。死不投降,该杀还得杀,不杀不足以震慑敌人。杀了以后,还可以肯定他的忠,这对自己的臣僚们也是一个正面的教育。大忠臣的典型,对所有皇上都是有用的。
这时的文天祥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一身正气地去见忽必烈,长揖不跪,忽必烈也不计较,就让他站着跟他说话。话不多,但都很坦率,所以忽必烈很快就听明白了,也想明白了。这个人是不会投降的,他看重的不是荣华富贵,更不是苟且偷生,甚至不是建功立业,而是青史留名。那句“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也觉得确实是难得的佳句,而这个人,以其智慧和才具,能够拿来“照汗青”的,也只有“丹心”了。忽必烈决定成全他。当然,忽必烈会告诉自己的臣僚,你们靠这个是不会青史留名的。文臣要靠政绩,武将要靠战功。文天祥说得明白,只有在“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时候,才能留取丹心照汗青。
第二天,文天祥在菜市口从容就义。死后,人们在他的身上找到了他事先写下的绝命词:“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在这方面的认识真的很深刻。读圣贤书,能学到什么?就是这个。
(摘自《夜阑卧听风——忽必烈大帝》,陈冲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