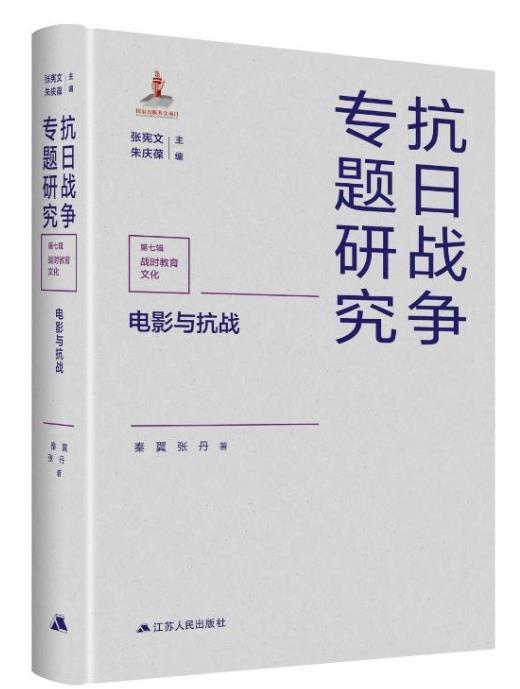
提到电影与抗战,不知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地道战》《地雷战》,还是《红高粱》《八佰》。秦翼、张丹合著的电影史研究著作《电影与抗战》讲述的却并不是那些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抗战题材电影,而是抗日战争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中的中国电影,比如1935年出品的《风云儿女》(主题曲之一《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我们的国歌);比如1938年出品的《八百壮士》(与1975年台湾版《八百壮士》、2021年上映的《八佰》一样,都是以在抗战史上写下光辉一页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为题材);比如1943年摄制完成的《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后来更名为《南泥湾》并在片头加上了毛主席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电影与抗战》既是对1931年至1945年中国电影的历史述说,也是对那场战争真实面目的部分还原。
在计划出版100部著作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中国抗日战争专题研究》丛书项目中,这个选题是个不太起眼的存在,像《八一三淞沪战役研究》《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这些,可能才是更受关注的学术议题,引发热烈而广泛讨论的焦点所在。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的“或许在历史学领域的研究看来,电影史是一个再微小不过的问题”,抗战时期电影史又只是中国电影史中一个短暂的特殊存在,然而,所谓“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透过抗战时期中国电影业的艰难求存和电影人的跌宕命运,何尝不能够展示一幅波澜壮阔的抗战全景画卷?
至少,任教于南京艺术学院的秦翼教授和张丹博士通过此书的撰写,实现了以详密史料编织历史现场、弥合电影史研究“黑洞”的野心。主流中国电影史研究往往有意无意地将“沦陷区”“敌占区”电影排斥在抗战时期电影之外,仿佛宇宙中出现“黑洞”,又像是拼图缺失了一两块,中国电影史版图因此不再完整。可是历史有其连续性和传承性,历史的某个车轮是与其他车轮发生联动、相互作用的,“无论是从电影生产的地域、环境、受众,还是从产业、文化、艺术的延续性上考察,包括沦陷地区电影在内的抗战时期电影,无疑都与抗战前后的其他中国电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电影与抗战》中,作者念念不忘的是身为电影史研究者的责任:“构建完整的中国电影历史叙述,找寻存在于其中的种种传承和连接”。为达成此种完整性、全面性和连续性,作者作出了种种努力,呈现给读者的是14年抗日战争中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整体脉络。
全面抗战时期和非沦陷区的电影史是《电影与抗战》书写的重点。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上海和香港两个租界区,电影坚定了宣传抗日的方向。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奔赴后方和前线,投身于中央电影制片厂等电影公司的工作,于艰苦卓绝环境下摄制了《热血忠魂》《保卫我们的土地》《抗战特辑》等正面宣传抗战的故事片、纪录片。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电影事业也开始建立和成长,在几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起步,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等纪录片、新闻片,为根据地生活和斗争留下了珍贵记录,还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储备了人才。在沦为“孤岛”的上海和香港,《木兰从军》《摩登地狱》《孤岛天堂》等一批或借古喻今、或讽刺批判、或寓意深远的影片,包蕴爱国情愫、反映社会现实、保持艺术水准,可以说是侵略者铁蹄阴影下的抗战电影,时至今日仍值得尊敬。
对中国电影在抗战之前的整体样貌、局部抗战时期的转变过程,书中亦加以深入详尽的介绍和分析,而对于战后电影产业、艺术创作的变化及其影响也有一番总结和思考。“将电影发展放入宏大宽广的中国近代历史背景中去描述,使我们有可能获得更为深入的电影史阐述角度”,秦翼老师在导论中如是说。抗战形势下电影界关乎“软硬”之分的激烈思想论争,国民政府从制定电影法律法规到成立审查机构的一系列举措,无不深刻影响了之后中国电影的历史走向。1931至1937年,从“九一八”到“一·二八”,电影始终在场。费穆导演的《狼山喋血记》、吴永刚执导的《壮志凌云》、“诗人”导演孙瑜作品《小玩意》,在银幕上发出了救亡的呐喊,回应日益深重的国难。电影的历史不只包括电影。大卫·波德维尔在《世界电影史》中提出:“通过研究社会和文化对电影的影响,我们更好地理解了电影承载制作和消费它们的社会印迹的方式。” 战后的中国疮痍满目、百废待兴,坚持长期抗战的中国人发现,历经劫难后迎来的并不是期盼中的幸福安定生活,气质忧郁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天堂春梦》堪称抗战后中国社会的缩影。
弥合“黑洞”的工作体现在“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苦闷与挣扎”和“伪满、华北的电影文化侵略”这两章中。在上海、东北、华北三个沦陷区,电影命运多舛。从一度繁花似锦的上海电影业在沦陷后如何因材料供应断绝、发行渠道萎缩而被日本侵略者扼住咽喉、全面吞并,到沦陷区电影中备受争议的中日“合拍片”(如1943年的《万世流芳》和1944年的《春江遗恨》,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先生坚决不认同其为“中国电影”,傅葆石等学者却认为这两部“汉奸片”中隐含抵抗策略),再到日本人在东北、华北沦陷区发动的失败的“映画战”,书中重现了彼时侵略者步步紧逼,中国电影人不甘束手、抗拒挣扎、沮丧屈辱、无奈妥协、消极应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保存中国电影业火种的波折历程。观滴水可知沧海,从中不难窥见抗战时期沦陷区民众的普遍生存状态。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指出,在强权政治压迫下,村民的反抗更多的是以类似偷懒、装糊涂、假装顺从、装傻卖呆、暗中破坏等日常形式的斗争来进行。在那个极度黑暗时期,沦陷区百姓面对绝对强权时隐晦曲折的反抗方式,或许才是当时民众政治表达的主要方式之一,是谓“弱者的武器”。
如今日渐丰富的网络数据库资源降低了文献搜索和史料收集的难度,然而史料的愈益充裕固然有助于拓宽加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却也对研究者的资料辨析和处理、追问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电影与抗战》中涉及史料数量繁多,从前人文献、后人回忆、书信日记、历史档案等庞杂琐碎的材料中,梳理各类影片及其背后中国电影业的兴衰、嬗变与发展,探究电影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及叙述方式的流变,是对研究者素质与功力的考验。可以说,作者并未满足于提取使用浅表文本、拼凑得出简单结论,而是在客观资料和主观立场之间进行了细针密缕的织补融合,展开对抗战时期电影的历史讲述和记忆构建,从而丰富了中国电影史的面貌。
一部电影史也是一部抗战史。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电影从诞生起就始终体现着时代意识和民族精神。中国电影的发展与抗日战争的关系密不可分,电影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中遭遇了民族的创痛、民族的记忆、民族的思考和民族的觉醒。在《电影与抗战》中,无数历史细节及蕴藏其中的情感透射出中国人的不屈意志,无论夜有多黑多漫长,路有多难多崎岖,我们都将坚定前行,“如同河流,在最深的夜里也知道明天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