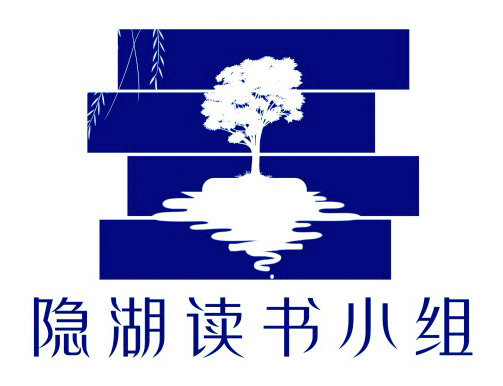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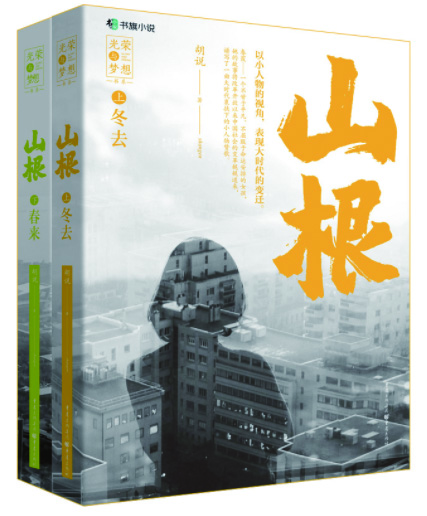
“隐湖读书小组”:2021年10月于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成立,主持人为吉云飞,参与者全部为“00后”本科生。小组以读书会的形式,共读当代新出作品,特别是长篇网络小说。力图在具体的阅读行动中,打破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壁垒,见证网络文学汇入“文学”主流,并在此过程中发掘网络文学真正的独特性。
吉云飞:在近年来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潮流中,胡说的《山根》是最有讨论价值的作品之一。小说以陕北村庄中的“70后”女性春霞为主角,时间跨度自1979年到2019年,地域则集中在黄土高原和深圳特区,尝试用小人物的命运变迁来表现改革开放大时代的不平凡。
小说出自对现实题材的召唤,明显受《平凡的世界》的影响,可以说是其精神续作;但又在努力以网文的方式打动更多读者,处于“大女主文”“年代文”的序列之中。现实主义与网络文学之间或许并没有天壤之隔,现实主义的爽感正在于能够让读者相信:最好的可能是可以实现的,尽管这一可能的实现需要特殊的机运。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能让读者重返一种朴素的理想主义信仰之中吗?网络文学的“爽”和现实题材的“真”又该如何在冲突中共存?
时代机遇与个体命运流转
曾予蕗:《山根》以深圳为核心场所描写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巨变,并延伸至主角所出生的乡村的山乡巨变,在真实性方面对于它的目标读者是可以成立的。《山根》依托改革开放本身所具有的磅礴向上力量,至少让“奋斗就会有收获”的理念重新获得合法性,这也是深圳人非常看重的“实干精神”。不过,小说还是难免架空了更深层的现实逻辑,有意避开了对社会境况更为细致的观察和书写,采用“好人有好报”的传统道德伦理作为小说的基石,这才支撑了这一信念的实现。新的困境更在于,对改革开放精神的描绘仅停留在实现“富强”的层面,主角也是在遵循传统的阶层上升途径,没有直面、更谈不上解决当代国人的精神困境。若只是停留在个人乃至集体生活的改善,似乎对今日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够了,也让网络文学通过平行世界“想象不同于当下的生活”的独特功能无法体现。
许译尹:《平凡的世界》打动人的前提是叙事逻辑能被读者信任,即时代对个人奋斗的许诺可以实现。当然,也离不开将苦难描摹得抒情绵密,并予以主角各种各样的美德,借此呼唤读者的情感认同。这分信任和认同带来的信仰与激情,足以免除对情节过分巧合的质疑。《山根》同样如此,春霞的命运变迁自改革开放来,小说的可信离不开这一时代背景的加持,它为无数乡土青年带来“逆袭”的希望。他们身上顽强蓬勃的生命力与深圳这所城市一切皆有可能的信条不谋而合,个体命运的逆转也随之有了坚实的基点。而当在大城市立足愈发艰难,“打工人”的信心也会随之动摇。作者笔下,以山为根的青年被赋予罕见的生命活力,这种强大的生命能量令人向往,却也根植于时代的机遇。
“爽感”来自网文的“套路”?
梁馨月:《山根》对我来说,更像是一部“年代文”,打动我的主要不是以小人物见大时代,而更多是个体的苦难及其救赎。小说现实题材的部分,体现在书写国民劣根性以构建“真实图景”,最后以理想化的传统美德的感召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核心逻辑似乎是“国民劣根性的显现(现实)——传统美德的解决(理想)”,“爽感”也在这一反复中不断升高。这一“爽感”的深层逻辑在于普通人努力奋斗在激烈竞争中改善生活的渴望;而作者理想化的问题解决方式可能会弱化尖锐的现实矛盾,仍然是为普通人造了一个梦,缓解现实中的“内卷”焦虑,让我感觉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确可以归属为“年代文”这一种特殊的网文类型,内核和套路不变,只不过故事的背景放在了当代。
诸歆然:小说的目标读者主要是女性群体,仍符合网文作品吸引受众的逻辑:在个人生命经验基础上的代入感和满足感。春霞给有相同出身背景的女性带去相当大的共鸣,产生了代入感;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实现阶层腾飞的经历,有物质上的满足感;春霞的形象也符合她们这代人心目中对女性及自我的想象,又产生精神上的满足感。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灰姑娘故事,女主拥有各种美好品质,虽出身贫寒、遭受苦难,但能在男性的帮助下改变命运。不过,与春霞同样有在大城市特别是在商界中打拼经历的女性,或许反而会因为小说描写得不够真实导致难以代入。更年轻的女性读者则有可对过于“圣母”“白莲花”的人设有所反感,另一方面也很难再对灰姑娘故事继续抱有幻想,小说对她们也就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
终究通向“美”和“善”
陈思羽:《山根》是现实题材,但给我更深印象的是它属于网文的部分。在女主春霞的奋斗史中,能清晰地看到“大女主”经典套路:出身卑微但心地善良的女主一路披荆斩棘,在“护花使者”和“贵人”的帮助下走向人生巅峰。生活的苦难像是升级所必须的打怪,春霞需要不断战胜恶毒女配与无赖配角,从而实现成长。这一套路在网络言情小说中屡见不鲜,且已被反复证明能让读者获得阅读快感,但在现实题材中却更容易产生割裂感。一是当小说背景放在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代,读者就会更倾向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去思考情节发展的逻辑,如果小说情节和日常生活经验出入较大,就会产生不真实感。二是《山根》的目标受众是与主角春霞同龄或经历相似的女性,她们可以从春霞的故事中得到共鸣,但大部分“90后”和“00后”,并不能很容易地进入到故事的情境中。三是现实题材似乎很难与网文通行的快节奏写作模式融合,现实题材需要生活本身的复杂和丰富,才能塑造出自然的真实感,而快节奏会牺牲现实生活的细腻。总的结构有点像单元剧,两三章就要出现一个冲突,也要很快把冲突解决,情节就特别跌宕起伏,充满巧合。
刘 鑫:我是很被《山根》打动的,特别是为其中闪烁着的理想主义。但也会有所不满足,小说如何让读者相信有更好的价值和更高的品质始终是一个难题。我想谈一个具体的不太满足的点。小说中的配角大多有点恶毒,会打压女主,当然最后被“打脸”。但他们没有被女主报复,而是被现实报复,最终能够被救赎的又被女主救赎。坏人,不能被救赎的就坐牢去,或者写死;能救赎的,比如说春霞的朋友莹莹,家里父亲母亲就突然生病,然后春霞帮助她,让她到公司做主管,最后拥有幸福的生活。大坏蛋去死,小坏蛋在付出代价后可以得到救赎。这样偏简单的逻辑,让我保持质疑。
吉云飞:《山根》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个中间物,可以从中导引出不少重要的问题。尽管小说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答案,但有时问题会比答案更重要。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向我们提出的一个有待解答的重要问题是,网络文学如何不止于“爽”,也能在快感的基础上通向“美”和“善”,而“美善”正是更高级的“爽”。其中的关键仍在于实现“爽”和“真”的和解,特别是在更高级的“爽”和更深层的“真”之间,如何让读者信服“内心纯洁的人前途无量”。非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所使用的方法是为主角“开挂”,那个好人必须得是个猛人,才能在保有美德的同时获得幸福的生活。“开挂”也是出于无奈,否则就只能靠各种机缘巧合,反而会对小说逻辑造成更大伤害。其实,以“爽”为本的网络文学也在求“真”,因为那个美好的梦如果像真的一样,自然是爽的。从“真”出发的现实主义同样也在求“爽”,“爽”就是小说高潮的实现,告诉读者美好的梦是可以在现实中实现的。求“真”与求“爽”,虽然殊途但或许同归,他日道上相逢,犹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