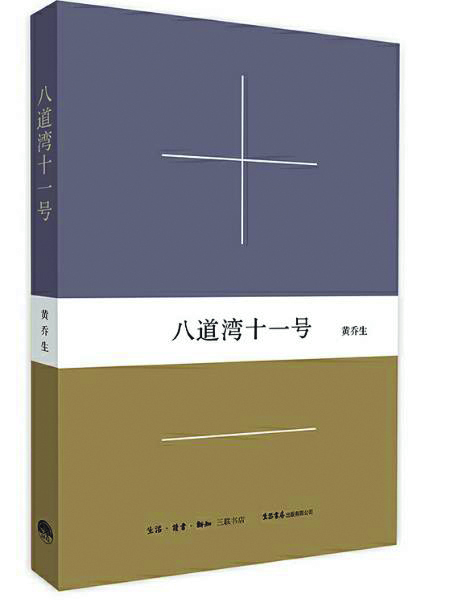
1912年5月5日晚间,鲁迅“约7时抵北京”。此时,31岁的他随教育部北迁,在从天津往北京的车上,“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眼前的自然景象让他失望。
然而,鲁迅在这“首善之区”一住14年,从生命存在时间来说仅次于早年的绍兴时期,而从个体的记忆时间来说则是最长阶段。北京时期鲁迅的现实和心理经历极为丰富和复杂,家庭和爱情、事业和文学、同人和兄弟等多重关系纠结,跌宕起伏。大体上说,鲁迅对北京经历了疏离、融入、反思和告别的过程。
鲁迅到达北京次日入住绍兴会馆,即《呐喊·自序》中的“S会馆”,是他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S城”到“S会馆”的空间表述,隐喻着鲁迅对绍兴原乡逃而不脱、脱而不离的矛盾纠结。从1898年出走“S城”,到留日回国后在“S城”及其周边兜转,现在,他漂泊到了乡音萦绕的北京“S会馆”。虽然在会馆中,他有意将自我隔绝于偏僻的补树书屋一角,但在会馆内外的交游对象仍是“S城”的人。即便鲁迅在将自己沉入“古代”所进行的抄古碑和佛经、整理古籍的工作中,也不乏乡邦文献的整理和编纂。
1917年4月1日,周作人自越至京,兄弟二人“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他们交流使用的应是绍兴话,但这样的乡音却让“S会馆”焕发出新的生机。在绍兴会馆,两兄弟重拾起东京时期的文艺梦想,继续推进被中断的“新生”之梦。1917年底,兄弟二人合撰《〈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在这篇本是公务性质的推介文章中,他们表示“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渗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称赞该书是“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也激励着他们自己的文学追求。
于是,北京成为东京之后鲁迅文艺事业的第二个重镇,是对他在东京所践行的以文艺改变国民精神启蒙理念的深入阶段;绍兴会馆则成为鲁迅北京文艺再出发的始源地,也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原点。刘半农与钱玄同都曾来访,或与鲁迅商讨通过《新青年》“召缪撒”“造蒲鞭”,或鼓动鲁迅加入《新青年》队伍。鲁迅正式接受新文学阵营的邀请,形成北京时期的第一个同人聚合,以文学发出激越的呐喊之声。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为代表的小说同时,也在“随感录”的批评文章中,触及现实,直指社会、历史和文明问题。
1919年底,在《呐喊》的第5篇《一件小事》发表前,鲁迅搬入八道湾胡同11号,至1923年8月,因与周作人失和搬离,在这里度过了近4年时光。38岁的鲁迅得偿三代同堂的愿望,没落于绍兴的家业在北京中兴,大家庭生活给予他极大的精神安慰和鼓舞,一切似乎都欣欣向荣,他在心理情感上完全接纳了北京,以为北京不再是多年漂泊人生的中转地,而是最后的落脚地。
鲁迅有了事业与生活并举的雄心和动力,他计划在“推文艺”道路上开创周氏三兄弟文名,不仅修订重版了在东京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群益书社1921年版),还与两位弟弟合译出版了《现代小说译丛》(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又与周作人合译出版《日本现代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在计划首部创作文集《呐喊》结集出版时,鲁迅在《自序》中正式推出自己“小说的名”,并在文末自注:“1922年12月3日,鲁迅记于北京。”
但以脱离原生乡土,另寻现代城市空间去构建家族群居生活的置换方式是危险的,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时,未能预想到这种历史文化之痛有一日会落到自己身上。北京八道湾胡同11号周宅很快出现危机,首先是周建人在1921年10月离开去上海谋职,已是预警信号。尽管自1922年2月底至1923年4月,俄国盲人诗人寄寓在此,他以丰沛的诗意暂时弥合了成员之间的矛盾。但到了1923年7月,在爱罗先珂离去3个月后,失和爆发,周作人在给鲁迅的信中以一句“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宣示决绝。
8月2日,鲁迅临时租住砖塔胡同61号同乡寓所,开始新的漂泊,但与此前不同的是,他的亲情信念已然轰毁。他一度将私人情感融入到家族生活中,从亲缘关系,尤其是与周作人的手足之情中获得宽慰,但此时陪在他身边的却只剩下朱安。鲁迅在现代文明之都亲手构建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何去何从,他甚至无暇去思考新的人生可能,肺病严重复发的他仍要安顿好母亲和妻子。10月30日,他购置了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的小院,无论地理位置,还是住宅规模,都有别于八道湾大宅院,但足以帮他重新建立起对北京的归属感。
1924年5月25日,鲁迅入住新居。此前4月8日,他购买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9月22日开译,译文自10月1日至31日在《晨报副刊》连载,是兄弟失和后他的第一个译稿);同时,在入住新居前后,他恢复了小说和散文创作。兄弟怡怡虽再无可能,但文艺志业并不因此而弃绝,鲁迅在“推文艺”道路上继续前行,并觅求新的同人。从《新青年》转到《语丝》《莽原》,近10年的时光中,他前后投身于此三刊,践行批评文章,逐渐成就独行于世的杂感文体。
人生的破镜难以重圆,带给鲁迅巨大创伤,但也促成了爱情发生的可能,此前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不能爱的。鲁迅与许广平从通信发展到恋爱,在这一过程中,他爆发出惊人的创作力。在北京最后一处的简陋寓所里,他完成了《彷徨》的大部分和《野草》的全部篇章,以及《朝花夕拾》的前5篇,日后被他称为创作5种的近一半成稿于此。
至1926年8月,鲁迅的事业、爱情等种种问题交织并发,在公共和私人空间中酝酿发酵到饱和,一触即发。是时候向北京告别了。26日,鲁迅南下赴厦门大学任教,开始又一次“走异路”的旅程。
北京14年是鲁迅人生历程和思想发展的重要和复杂阶段,他见证了五四运动从高潮到落幕,亲历了同人的分化和手足的睽离,从文艺到学术,又从学术到文艺,学问文章齐头并进,融会贯通。鲁迅对北京形成独特的心理认知和深刻的文化体验,在南下后及晚年进行的对北京的反刍性书写中,读者既能看到决绝的否定,怀疑的审视,也能感受到深情的眷恋。
(作者系合肥学院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