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腔北调集》,鲁迅著,同文书店,1934年3月初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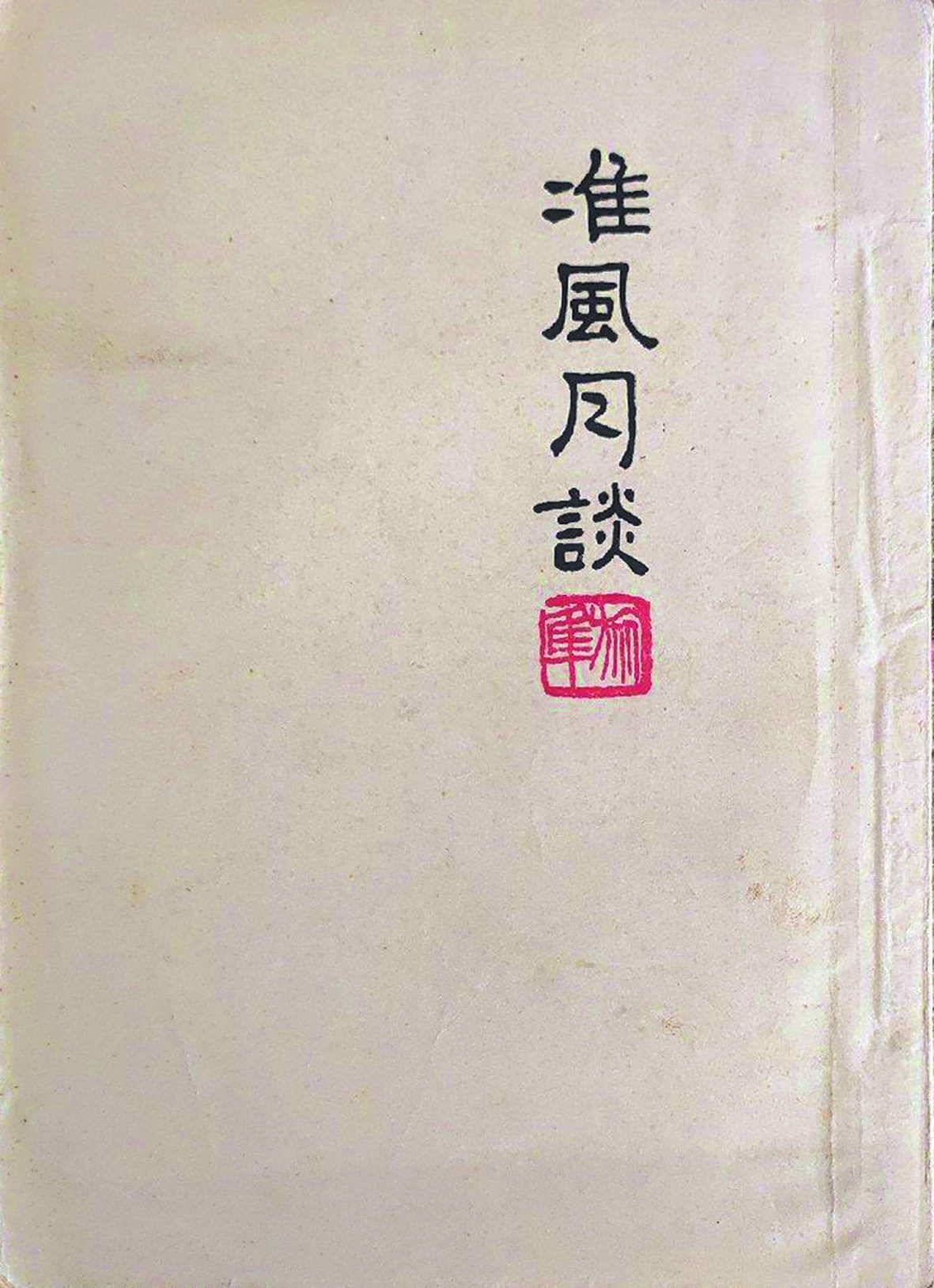
《准风月谈》,鲁迅著,上海兴中书局,1934年12月初版本
1946年,散文家李广田曾谈道:“新文艺作家中有很多写过杂文的,也都发生过不少的影响,而影响最大的,当然是鲁迅的杂文。”这个判断,直到今天仍然不过时。在鲁迅现有的杂文集中,最能体现其后期杂文特色及创作巅峰的,当属1934年出版的《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
有关《南腔北调集》的书名,据该书《题记》所述,源自当时上海一位文学家的“素描”:鲁迅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鲁迅则承认,南腔北调不仅是自己说话的缺点,而且是近几年其文字上的趋势。因此,他将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南腔北调集》。而关于《准风月谈》书名的出处,鲁迅则在《前记》中提及:自1933年5月25日《自由谈》的编者刊出“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很使老牌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了一大阵……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所谓“不能正如尊意”,即这些文章实际上无法做到只谈风月,因此只能算是“准风月谈”。
《南腔北调集》收入鲁迅1932年至1933年所作的文章51篇,其中包含了十来篇序跋文、纪念文及公开信等,因此该书仍然带有鲁迅前期杂文集“杂收”和“杂录”的特色。《准风月谈》收入鲁迅1933年6月至11月所作的文章64篇,皆为篇幅短小的杂感,但“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从编排上看,这两部杂文集都延续了鲁迅此前按照编年排布的特点。其好处,正如他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所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鲁迅之所以强调“时势”或“世态”,自然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宣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均为“反动”,凡批评国民党政策者均为“危害民国”,应“一律禁止”。此后,这一“标准”逐渐发生了效力。1933年5月中下旬,鲁迅所作的《王化》《保留》《再谈保留》《“有名无实”的反驳》《不求甚解》等五篇杂文,因批评国民党当局对内镇压无辜群众、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的卑劣嘴脸,皆未能在《自由谈》登出。这五篇连同此前在《自由谈》上发表的38篇杂文,随后被鲁迅收入《伪自由书》(一名《不三不四集》),当年10月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的名义出版。然而,仅仅4个月后,该书即被当局查禁。
鲁迅的杂文被查禁的原因,与其批判性和战斗性紧密相关。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一向将文学视为改造社会的利器。在收入《南腔北调集》的《〈自选集〉自序》和《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二文中,鲁迅屡屡强调其写作小说的动机之一,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看重的正是小说的社会价值。而对于杂文,鲁迅同样如此。据徐懋庸回忆,当鲁迅看到《大公报·小公园》上有人批评其《打杂集》的文笔时,就特意将文章剪下来寄给他,并在旁边批注:“这篇批评,竭力将对于社会的意义抹杀,是歪曲的。但这是‘小公园’一贯的宗旨。”而在《小品文的危机》中,鲁迅更是反对把杂文变成“小摆设”。他指出,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人民决没有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和翡翠戒指,他们所要的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因为人民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只用得着生存和战斗”,“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
鲁迅的杂文,即是战斗的小品文,即是“匕首”和“投枪”。《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中的各篇,正是对准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小到街头巷尾、市井百姓,大到上流社会、知识精英,都以精炼的语言折射出广泛的社会现状和芸芸众生,使得它们在任何时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价值和战斗意义。而鲁迅杂文的主要战斗风格,即如他在《伪自由书》的《前言》中所说,乃“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具体而言,“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但由于画出了类型,导致某些人“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换句话说,往往因此得罪了许多人,引来一些无端的报复,使得作者经常处于危险的境地。对此,鲁迅自是心知肚明,但他并不因此改弦更张或“洗心革面”,而是坚持写作的初衷,选择“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鲁迅杂文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在其书名和篇名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在《南腔北调集》的《题记》中,鲁迅表示,准备将书名“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配对”。这两个书名,都具有十足的反讽意味与批判色彩。实际上,这种书名上的配对,在鲁迅的著作中并非个例。同一时期的《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以及此前的《三闲集》与《二心集》、《朝花夕拾》与《故事新编》、《呐喊》与《彷徨》等等,大都具有配对的特点。对此,鲁迅的解释是:“我在私塾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种题目之间的配对关系,在鲁迅同一时期的杂文集中,同样并不少见。从写作时间上来看,这些成对出现的文章,多数在同一天内完成,少数则间隔一两天完成,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弊端所发。比如《准风月谈》中的《华德保粹优劣论》与《华德焚书异同论》、《帮闲法发隐》与《登龙术拾遗》、《双十怀古》与《重三感旧》,《伪自由书》中的《从讽刺到幽默》与《从幽默到正经》,《花边文学》中的《“京派”与“海派”》与《北人与南人》、《中秋二愿》与《考场三丑》等都是。鲁迅在给书籍和文章取名时的配对方式,即是修辞学上所说的对偶。一般而言,对偶是用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意义相称的一对短语或句子来表达两个相对应或相近或相同的意思的修辞方式。这种修辞方式的特点是文字凝练,句式整齐,音韵和谐,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同时加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
除了书名与书名、篇名与篇名之间的配对关系,鲁迅单篇杂文的篇名本身,也往往由两个具有配对或对应关系的词汇构成。早一点的有《华盖集续编》中的《古书与白话》《可惨与可笑》,《三闲集》中的《吊与贺》《书籍和财色》,《二心集》中的《习惯与改革》《宣传与做戏》等,晚近的则有《准风月谈》中的《爬和撞》《同意和解释》《禁用和自造》《青年与老子》等。从表达效果来看,这种取名方式不仅体现了鲁迅在杂文语言方面追求整齐、对称的风格,也反映出其对相关话题的整体思考。而这,在开拓鲁迅杂文的批判空间的同时,也确保了其言说内容的系统性与客观性。
鲁迅杂文鲜明的批判性和战斗性,也体现在其使用的笔名上。1933年5月中下旬,由于审查者的压迫加剧,鲁迅的杂文接连无法在《自由谈》上登出。然而他并未就此搁笔,而是改些写法,换些笔名,同时扩大投稿的范围,依然常常登了出来。此后,鲁迅将1933年6月至11月间所作的杂文,编为《准风月谈》出版。与作者之前的杂文集明显不同的是,这部集子中每篇杂文的标题下面,都附上了发表时使用的笔名。从数量上看,《准风月谈》64篇杂文使用了20个不同的笔名,占到了鲁迅杂文所用笔名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这20个笔名中,绝大多数为首次使用。
鲁迅在频繁变换笔名的同时,也往往借助这些笔名,展现讽刺的效果和战斗的意味。《准风月谈》使用较为频繁的笔名有“游光”“丰之余”“旅隼”“洛文”等。“游光”首见于杂文《夜颂》。按照许广平的说法:“在《准风月谈》里用‘游光’的名字写文章的,多半是关于夜的东西。”而从字面上看,“游光”可理解为游荡的光,它是黑暗的叛逆者和破坏者。鲁迅曾在《两地书》中自述,他的反抗,不过是与黑暗捣乱。因此,他以“游光”为笔名撰写与暗夜、黑暗相关《夜颂》《谈蝙蝠》《秋夜纪游》《文床秋梦》等杂文,或许正是为了表明与暗夜、黑暗捣乱和战斗的立场。与此类似,“旅隼”有旅飞、旅行的猛禽之意,以之为笔名,则比喻战斗者笔锋犀利,能深攻入敌且神速勇猛。“丰之余”首见于杂文《推》,系从1928年的通信《关于“粗人”》所使用的笔名“封余”衍变而来。此前,郭沫若署名“杜荃”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把鲁迅当作“封建余孽”加以扫荡。鲁迅把他人的攻击之词稍加变化,用作笔名,显然带有一种讽刺加回敬的意味。正如《关于“粗人”》讽刺的是对《诗经·伯兮》乱加解读的“大雅君子”,《准风月谈》中署名“丰之余”的《推》《二丑艺术》《踢》《吃教》《重三感旧》等12篇杂文,所讽刺和批判的“清客”“阔人”“官商”“骚人墨客”“顽固的遗少群”等,无一不是“穿长衫的高等华人”。同样的,“洛文”则是此前笔名“隋洛文”的简化。后者系针对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一事而起的笔名。作者将当局对其污蔑性的称呼稍加改动,用作笔名,一面以反语的形式达到讽刺的效果,一面也通过笔名记录这段战斗的历史。
在《准风月谈》的《后记》中,鲁迅屡屡在行文中剪贴那些攻击他的文字。对此,他曾解释说:“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从实际来看,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鲁迅在那段时期所写下来的战斗性的杂文,正是其当年所处境遇、战斗技巧和战斗业绩的忠实记录。而他由此编成和出版的杂文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已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