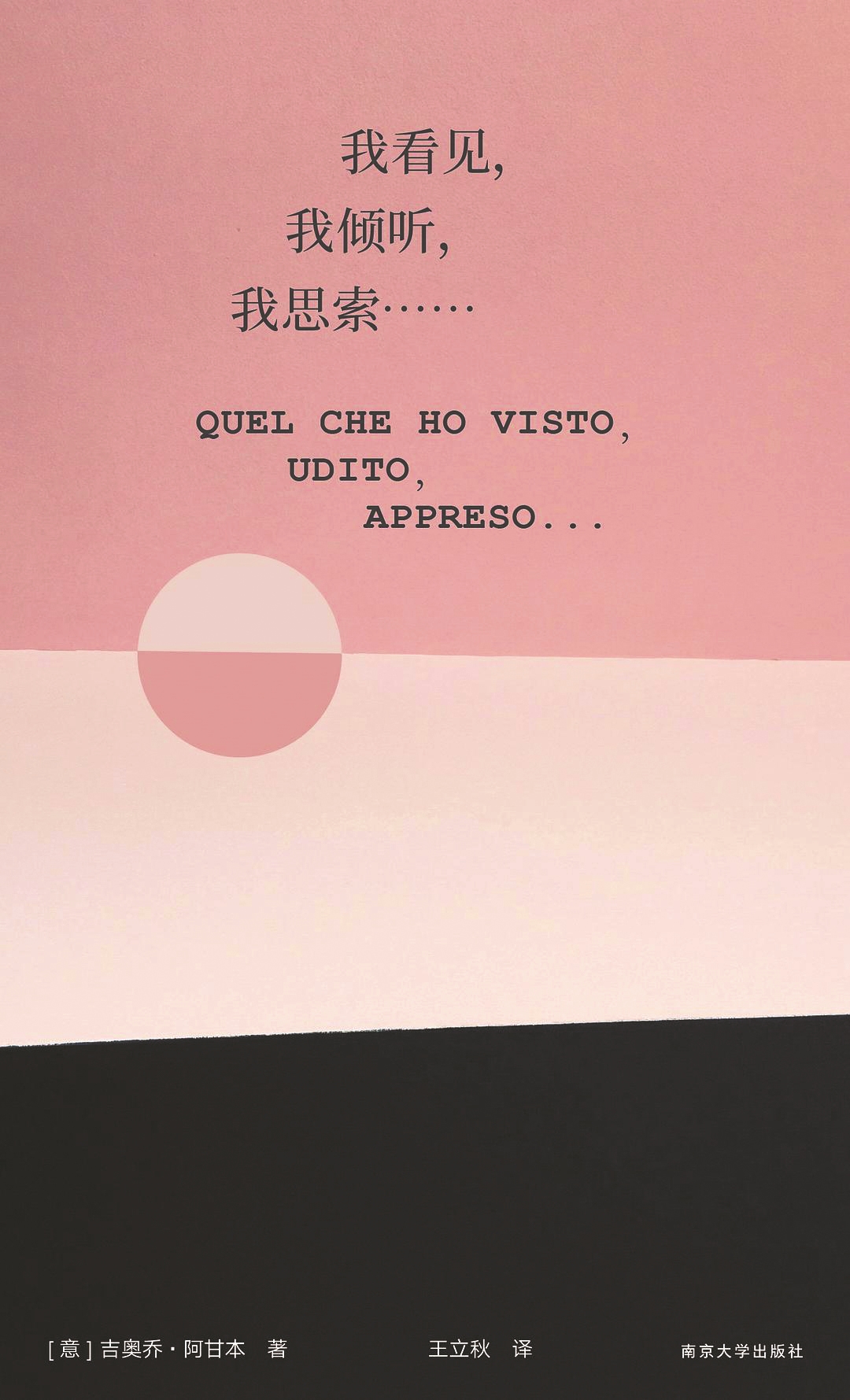
《我看见,我倾听,我思索……》,【意】吉奥乔·阿甘本著,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阿甘本赋予思想随笔以更高形态——再度纯化,上升为一种“哲言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一系列传统:古罗马以来自我书写的记事簿与沉思录;培根与蒙田的论说散文;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箴言体写作。《我看见,我倾听,我思索……》这本小书,努力追求诗思合一的旨趣。他以哲学思索切近生命体验,时空与此在。看见、倾听与思索,形成了写作的链条,其意味知觉感官与理性反思的统一。我将其概括为从身体经验来,到存在之思去。正如海德格尔于荷尔德林诗中的发现,语言是存在的家,诗是纯化语言的典范。
在我看来,作者的思维融合了东方式的顿悟、照会与“现量”。在书中,即时的当下、瞬间的直觉具有极大的能量,成为主体投射于客体,沉浸于审美遗忘的核心。“我看到了佛陀的脸……在我的眼睛开始感受到石头发出金光的时候,我明白了沉思的意义,不只是让心智停止运作,也要让身体停止活动。在沉思的瞬间——永恒——人不再有身心之分。这,便是极乐”。它使我们重新估量沉思的意义,乃是精神与身体的双重修炼。
如果以禅宗瞬间见永恒,万古共一月,庄子心斋、坐忘之论,反观阿甘本的感言,就显得暗合冥契。身心不可分,是中国文人不同于西方哲人的重要分野。所谓极乐,本质是主客融合,身心一元的高峰体验,而书写就是一种实现形式。这种写作始终建立在“凝视”之上。当作者用“我看见”“我学到”贯于章节之前时,其实表明了经验的两种来源:一种是物理意义上的(人在时空范畴中的认知体验),一种则是心理意义上的(以自我体验推论他人体验),两者分别指向有限性和无限性。
阿甘本的洞见,是同时以有限性和无限性看待事物与他人,这源于斯宾诺莎的启示。“在神身上看它们,把它们视为永恒;在时空中认识它们,把它们看作受限的、有限的,仿佛与神切断了联系。但真正爱一个人,意味着同时在神身上和在时间中看他们”。显然,爱欲对象要接受不同的目光投射:既有神性亦有世俗,既有超越也有堕落。甚至,作者在借海德格尔式的言说,对亲密关系进行譬喻。爱人之间“既看到他们此时此地‘存在’的柔弱似影,也看到他们在神身上‘是’如琥珀、水晶般稳固晶莹”。爱欲,显然是依托于现时的此在,同时又通往永恒的存在,爱人们既会被功利性地审视,也会有超功利的目光。
沉默与言说
我更愿将阿甘本视作一个具有悲观色彩的醒世者。这使他能看破写作的命运,劝慰写作者的心灵。“人可能爱上自己的错误,以至于把它们变成生的理由——可说到底,这意味着对我们来说,真理只会作为死的意志出现”,“真理总是最后的,或近乎最后的”。它同样可以推及到作家,作家很可能偏执地把错误变为作品意义,将缺陷视为写作风格,并认为文本里存在真理。事实上,我们必须破除写作中的目的论,艺术和生活一样,都不是为了成功,“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也正是失败”。
换言之,艺术使我们理解失败的命运,不断哀悼失去之物(包含自我的丧失)。失神状态,反而是发现存在,最接近人的本质时刻。阿甘本始终在辩证演绎中探讨写作的秘密、追求与境界。“秘密总是彻底暴露的,同时,被揭露的东西看起来又沉入自身并几乎被自身淹没,向着一个无法说明的中心移动”,“一切都向自身内部折叠、包卷,以便在表现中隐而不显,在一切‘话’中不被表述”。沉默的言说,是他对写作最核心的思索。沉默与言说,形成对立统一,两者相反相成。
一方面,它触及文学中可见与不可见,在场和缺席,意义和言辞的关系。正如在隐匿中显露,才能有中国古典诗学里的“蕴藉”与“隐秀”,才会有言意之辨、意生象外等命题。“我想思考,想说的一切,在我写的一切中都没有被思考,被说,或只被间接地说到”。只不过,阿甘本强调写作是对“界限”的追求,对尺度的摸索。我将其形容为——研究一种“接触面”的及物性写作。他在找寻“暴露与深渊,半影与荣光之间的有空隙的接触”和“接触点上的空白”。
阿甘本认为,写作抵达了这种空无,才能通往一种自然境界。它表现为未经钻研的优雅,并不刻意的漫不经心,熟练的淡定和顺其自然。如同道家思维,天然去除雕饰,写了像没写一样,没说又像说了什么,恍兮惚兮,才是众妙之门。“在不表述的情况下使自己没说的东西显现的方式肯定定义了他所说的一切的品级”,“在每一本书中都有一个中心,为了离开这个中心——在不说它,不考察它的同时又在以某种方式见证它,书才被写下来。声称抓住了必须保持不言而喻的东西就意味着失去了作为作者—见证者的品级,而获得了作者—所有者的法律地位”。
勾勒思想的风景
圣贾科莫德奥里奥教堂的钟声给了阿甘本灵感,“钟声则不会传出需要理解的话;它们不召唤,更不召唤我……然后和响起时一样毫无理由地,毫不突兀地消失。不必说话就可以把一些东西说出来”。倘若以接受美学的文本召唤,读者反应批评反观,就能理解阿甘本的态度——他不试图召唤,也并不希冀得到回应。
作家对沉默的理解,实质上强调了文学中“负空间”的重要。所谓负空间,即不可见、不可说与未经历的区域,它们预留并决定了可书写的部分。“那无法经历的四分之一秒仿佛嵌入了我经历的一切的中心”。当阿甘本从拉丁语“见证者”之意,理解“作者”这个名词时,他意在告诉我们——写作始终要考虑如何把握自己未说之物。可见而不可言说,恰恰反映出这种断裂。如果作家能合理弥合断裂,那么,他就能从一个见证者上升成为“所有者”。
另一方面,沉默的言说又涉及作家能写什么、不写什么的“创作伦理”。它回到前文所言——对及物性界限的试探。“无论如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主体和他没说、没经历东西的伦理关系,是他能写的东西和他只能保持沉默的东西之间不确定的界限”。表面看,写作是自由选择的行动呈现,事实上,它却是被决定的必然。伦理关系既是一种制约要素,同时也为写作提供了确定性。沉默、空白与遗忘,是文字中不同层面的缺失——既有主观上的回避,也有客观上的丧失。
阿甘本从作家的本质需求、动力机制来阐释写作。写作是对经验缺失的弥补,是对记忆丧失的代偿。它建立在某种前提之上:认为存在一种原初的遗忘(空白的记忆),所有书写都是对遗忘的回想。这种观念显然是柏拉图主义的。“我后来写的一切都只是对那个遗忘的补偿,而如今,那个遗忘又像中心处的空白一样刺穿我写的一切,在一切回忆中标记出一个无法追忆的丧失。那段无法察觉的、失去的时光是我唯一真实的记忆”。
有意味的是,他以精神分析中的创伤性经验描摹写作活动。写作过程充满了自我的悖反、刺痛和拒认。我们有理由将书写视为自我疗愈的技术。“如果使我太过于冗长的话语成为可能的就是那个没有被说出的东西的话——以某种方式使它保持未知(暗示但不定义;透露但不说出),我就更能接近它”。我想,阿甘本对语言文字抱有天然的不信任。“我看到,不识字的人比那些号称会读书写字的人好太多了”。写作是迫不得已的方法,它无法解决疑难,只能分享谜题,只会互加修饰。
《我看见,我倾听,我思索……》在这些断章絮语里,传达了一个哲学家对写作的沉思。阿甘本既没有阐释什么理论,也没有讲述什么技艺,而是勾勒了思想的风景。写作不再停留于文艺创作范畴,而是成为重思生存体验、重塑意义世界的路径。虚构和修辞,或许只是生活的慰藉,旨在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确定世界。“只有作为一种戏仿,纯真才是可能的;这也是唯一可能修复受损的幼儿状态的方式。如果你把虚构变成你唯一的现实,那么你会找到确定性,但你也会失去全部希望。”
(作者系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