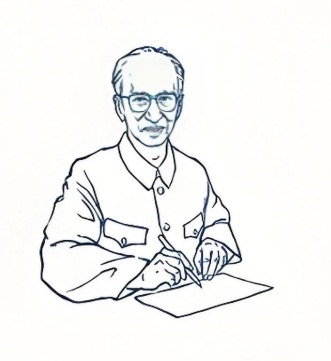
陈伯吹画像 阳卓宏 绘
“凡童心不灭的人,必定对人生有着相当的彻悟”,这对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而言,再合适不过。从1927年出版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到1997年辞世,长达70年的创作生涯让陈伯吹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座灯塔。他的一生经历丰富,胸襟开阔,目标专注。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他沉浸在儿童文学的世界里,用幽默、想象化解孩子们的恐惧,用人物、故事抵达孩子的心灵。
作家们在写作路上大多遇到过伯乐,1922年,16岁的陈伯吹到杨行乡朱家宅小学任教,“讲故事”成为他和小孩互动的教学方式。1925年,他被调到宝山县立第一小学当初级部主任,因遭遇家庭变故而开始大量撰稿。1928年,他开始尝试各种风格,杂文、诗歌、小说皆有所涉猎,并在时任《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的建议下,将重心转向儿童诗,创作了儿童诗集《小朋友诗歌》。之后,他又遇到了文学路上的贵人赵景深,在其大力推荐下,受邀创立了儿童刊物《小学生》。这个一生与童书相伴的“通才”,擅长用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普通事物拟人化,用童心未泯的灵魂,构建起丰富而又有冒险感的童话世界。而两位师者的点拨鼓励加上自身的勤奋,使他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路。
教育和认知、情感和审美、娱乐和想象、求知与探索,皆是儿童文学的指向。儿童文学常常以幽默、滑稽可笑的形式来表现具有美感的内容,充满想象力。陈伯吹不仅创作了一系列的儿童读物,如《学校生活记》《阿丽斯小姐》《一只想飞的猫》《甲虫的下场》《鸡大嫂上菜市场》《井底下的四只小青蛙》《骆驼寻宝记》等,也将理论研究抓严抓实,其《儿童故事研究》《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简论》《漫谈儿童电影、戏剧与教育》《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等陆续出版。同时,不仅创作与理论并举,他还翻译了《绿野仙踪》《小夏蒂》《空屋子》等外国儿童文学名著。
陈伯吹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是文学性、思想性和教育性的统一。文学评论家束沛德曾这样评价他,“在坚持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上,他的态度一以贯之,极其鲜明,斩钉截铁,毫不含糊”。他的创作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比如《阿丽斯小姐》受“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融入了反抗侵略的主题;《一只想飞的猫》窥探到了人性的阴影,故事里那只集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找借口、爱偷懒、不脚踏实地等诸多毛病于一身的猫,其实也是某些人的缩影。陈伯吹认为,“儿童文学主要是写儿童”“要以同辈人教育同辈人”(《论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自觉承担起为未来一代保驾护航的文学使命,他所创造的动物世界,贴近儿童精神生命的“内宇宙”,比如《阿丽斯小姐》的主人公面对轮番登场的各种动物,情感、心理、直觉呈现出差异性,让读者看到儿童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复杂。陈伯吹告诉后人,儿童文学是一种自我发现的途径,正义与邪恶、勇敢与怯懦、冷酷与温暖、真情与假意,皆可在故事中潜移默化,所有年幼的心灵都可以在质疑、思考、共鸣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人和自己想要走的路。
陈伯吹不仅是好作家,还是好编辑。他认认真真写约稿信、给作者回信甚至登门拜访,扶持了很多年轻人。1981年,勤俭了一辈子的陈伯吹捐出自己的稿费55000元,设立“儿童文学园丁奖”(2014年更名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给了许多孤独的创作者以前行的力量。心怀善心,行有大爱,始终对生活、对人类充满热情,正是童心的可贵之处。认真、执着、善良、温暖,陈伯吹把全部的色彩和力量给了小孩,给了他热爱的儿童文学。
陈伯吹业跨教育、文学、出版三界,从小学教员、中学教师、大学教授、教材审定专家、教育家、教育理论家到作家、评论家、期刊主编、社长,一路走来,涉猎广泛,理论扎实,研究深入,热情满怀。“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情怀支撑着他,像一只骆驼,驮来水源,驮来纸张,驮来笔砚,驮来书籍,驮来旅途中的奇闻异事,然后用一次次长途跋涉驮来的所有东西,建造起一个宏大的文学殿堂,那里面有他的理想国,他爱国、爱家、爱小孩的满腔柔情,以及贴地飞翔的五彩斑斓的梦。
陈伯吹不仅关注城市儿童,也关注乡村小孩。他曾对出版社的同事说:“现在出版的儿童读物,都是为城市中小学生写的。我们的作家队伍中,很少有人为工人、农民的孩子写书,书价又很贵,一年有多少本送到农村、工人、矿山去?”温和谦逊的他骨子里有韧劲、有情怀,有担当,还有满满的爱。与乡村孩子相处,曾是他儿童文学的起点,成名后的他依旧怀揣初心,心系乡野。
世事流转,时间会铭记一个人的功绩。一个躬耕儿童文学70年的长者,他思索着教育与文学的双重使命,树立起科学而自成体系的儿童观,在创作中不断突破困境,积极面对转型和跨界,从不放弃学习和思考。正因为有很多像陈伯吹一样的先行者,已走过整整一个世纪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他们执灯前行,用最美的初心、善心打开一扇扇窗,窗里有童话,窗外有净土。
(作者系高中语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