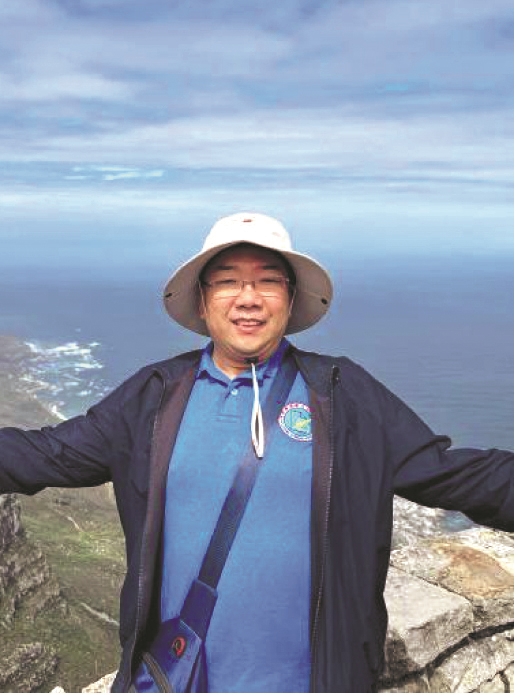
五月的岭南,空气中已经浮动着暑气的前奏。我拖着行李箱站在酒店大门口,抬头望见大堂里悬挂的“第二届东盟青年作家中国行”横幅,心中泛起一丝微妙的涟漪。来自东盟各国的青年作家们正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用英语、汉语或各自的母语交谈着,声音像一串串轻盈的气泡,在酒店大堂的穹顶下飘荡。
欢迎晚宴设在二楼的吉隆坡厅,这名字让我不禁莞尔——在南宁的“吉隆坡”与东盟友人共进晚餐,倒像是某种隐喻。桌上,热烈讨论起各自国家的文坛动态,更对广西的各种美食产生了浓厚兴趣。次日的启动仪式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相思湖校区里,下着不大不小的雨,仿佛老天爷利用东南亚的泼水节活动,来迎接我们的到来。当主办方宣布活动正式开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写作者,此刻正因为共同的热爱而欢聚于此。
漫步在钦州的红树林间时,我感受到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这里有孙中山先生的纪念碑,肃穆仰望孙先生的巨大铜像,心里油然升起对革命先行者的敬仰。
在坭兴陶博物馆,作家们蹲在拉坯机前,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手掌包裹着湿润的陶泥,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泥土的形状。“写诗比这个容易多了,”我听到一人苦笑着说,“至少诗句不会在我手里垮掉。”而此刻,陆陆续续有人已经捏出了容器的雏形。
傍晚时分,我们站在平陆运河的青年枢纽。工程师指着图纸讲解时,阴霾的天气,阻挡了夕阳照射在运河水面,巨大的闸门像断龙石般屹立在河心区,我想象着百年后,当有作家再从这里经过,写下的文字描述,跟我们见到的应该是截然不同。
我们还到访了民族英雄刘永福故居三宣堂,别看大门规模不大,进去后让人眼前一亮,四周的防卫碉楼,内部的暗道,加上刘将军的忠勇气节,让参观者肃然而敬。在充满战乱的晚清时期,中华大地上有着刘将军这样的民族英雄守卫疆土,值得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效仿和学习。
钦州老街的古朴风貌,仿佛将历史画卷徐徐展开,这里文房四宝、茶壶茶杯,与街上的老房子是绝配。行走在老街上,看到村民们聚在一起下象棋、泡茶聊天,让我们这些繁忙于城市的“牛马”欣羡不已。
夜晚的文学作品分享会更是让我领略到各国文学之美,在老街的八号公馆内,各国作家们用自己的本土语言,高歌一曲或朗诵诗歌,也只有文人聚会才会出现这种景象。
佛山的雨来得突然,但供奉着玄天上帝的祖庙,依然游人如织。宋代的雕刻工艺肃穆庄严,经过多个动荡时期依然保存完好,非常难得。印象中佛山是尚武之地,特别是黄飞鸿,在李连杰电影的带动下,在东南亚各国妇孺皆知。在黄飞鸿纪念馆内,我领略了岭南武术与民俗文化的魅力,而梁园的精致园林则展现了“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
樟木头镇的“中国作家第一村”让我颇感意外,想象中的文学圣地竟是如此朴素——几栋普通的民居,院子里的菜园果树,驻村作家的工夫茶,为充满诗情画意的工作室内,增添了几分热闹气息。我对中国作家陈崇正说,作家村是喧闹城市中难得的清净之地,在这里可以静下心来潜心创作,他认同了我的看法。
珠江夜游那晚,游船缓缓驶过广州塔。当这座被称为“小蛮腰”的建筑全身亮起蓝光时,窗外的雨丝毫没有减弱,船上热闹的歌舞盛宴,成为此行最诗意的注脚。
在暨南大学的讲座上,蒋卓述教授讲到中国文学的审美特征,为我们打开了欣赏中国文学之美的大门。听着教授朗诵一首又一首小时候学过的唐诗,那一刻,仿佛有无形的丝线,将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我们串联在一起。
行程的最后一天,我怀着深深的祝福,向各国作家们道别。大家相视一笑,无需多言。短短一周的相伴,留下的是一生的记忆与念想。
返程的飞机上,我翻看着这些天手机中积攒的照片和随手记下的只言片语。邻座小姐姐正在读一本中文小说,边看边写心得,原来文学还是有市场的,年轻人不会因为忙于生活奔波而放弃陶冶心灵的良药。当空乘送来饮料时,我选择了热茶——这趟旅程教会我品味的饮料。
五个城市的行程,十多个文化地标,无数次的对话与静默。我忽然明白,这趟旅程本身就是一篇集体创作的散文,每个参与者都是其中的一个句子,而我们的交流与感悟,则是段落间自然的转承。当飞机降落在马尼拉国际机场时,那些在岭南共同经历的日日夜夜,已经悄然生长为我文学血脉中的新养分。
或许正如某位作家所说,好的文学就像晒制的辣椒,需要阳光与时间的共同作用。而我们这趟跨越国界的文学之旅,正是让各自的文化在交流中晒出更醇厚的味道。我的行李箱里,除了纪念品,更多的是等待发酵的记忆与灵感——它们终将在某个创作的深夜,化作纸上鲜活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