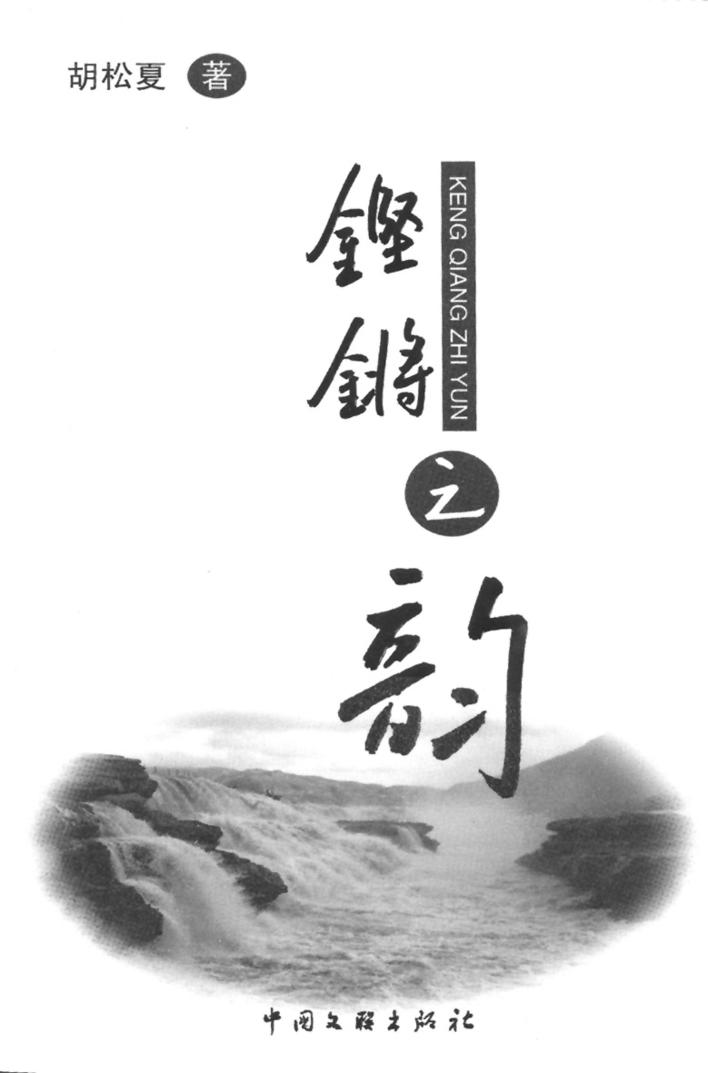古往今来,诗人与哲学家一直都在探寻人类生存和社会生活的意义。哲学家的逻辑是以现实、事实和理智为基础的,因此是更真实和本质的。相比之下,诗人的逻辑是以情感、感觉和想象力为基础的。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荷马和柏拉图,都是平易而深刻的,只是前者更具吸引力更易为人理解罢了,因为它不是以复杂的讨论方式来阐明理论的深刻,而是借助诗的钥匙来开启思维的理解之门。
胡松夏是一名现役士兵,又是一位诗人。他在紧张而有序的军旅生活中,不乏诗的哲思,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还拿起“诗的钥匙”,试图开启现实生活的理想之门。他新近创作的长诗《铿锵之韵》便是明证。尽管还不是臻善臻美,却是他作为一个士兵诗人对社会人生的哲学考量和诗意描述。
诗歌是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的重要途径。《铿锵之韵》写的是共和国国防油料科研堪称辉煌的一段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严寒区内燃机油问世,到成功研制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太空防雾剂,作者以其诗性的语言,形象地刻画出了一代代油研人的风貌。他们临危受命、因陋就简,凭着“一把丁字尺/一只油漏子”,“被时代的巨浪推到了/共和国军队油料研究的‘零公里’处……”长诗以油料科研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段为架构,通过几位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件来谋篇,在诗意的叙述中,将读者引入到哲学思考的层面:“没有超常的思维/就不会有活塞式飞机的横空出世/没有刻苦的钻研/就不会有飞离地球的自由翱翔……”
整部长诗洋溢着一股澎湃的激情,这也许因作者成天与油研人打交道有关。耳濡目染之间产生了诗的灵感,并以这种灵感来表达自己的想象和感受。但是,写诗并非复制事先存在的经验,而是一种创造及其创造的过程。这就需要基于现实并超越现实,使之达到更高、更深的精神层面。荷马描述人类的奥德赛之旅,表现人的魅力和勇毅,就是通过诗意的叙述,来弘扬人性之美,同时也鞭笞恶行、揭示某种兽性的卑劣。诗歌作为一种内在的需求,是一种独特的对自己和世界的冥想方式,如果被类似有同感的读者发现,愿意与其分享诗的意境,那么诗句就会奇迹般地充满生机,在富含强烈情感、纯洁理念和丰富含义的诗中,找到自己的共鸣点,从而产生一种诗的愉悦。显然,胡松夏是深谙此道的,他的长诗《铿锵之韵》也无疑有与之共鸣的读者群,因为军人视“油料”为战争的“血液”,特别是现代战争,更须臾不可或离。我至今仍记得在当年边境作战前线,每每见到藏匿于草丛间的战地输油管线时,那种久旱逢雨般的感觉。古代的战争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现代战争,“先行”的就是“油料”。当然,对于诗而言,“油料”只是一个具象,而诗歌却需要搭建意象之堡垒,这种精神的堡垒,才是诗人安放灵魂之所在。
在长诗《铿锵之韵》中,胡松夏是试图搭建这种意象堡垒的。他借鉴交响音乐的结构,将作品分为五个乐章,前有序曲,后有尾声,其中也不乏华彩乐段。但在搭建的过程中,用的多是具象的建筑材料,缺少意象的空灵和飘逸。这并不是要他放弃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去虚构没有基石的海市蜃楼,而是希望他基于和工作有关的现实和物质,实施诗的重构,将悉心观察、身体力行工作中的种种特征和韵律,以诗的语言和音节记录下来。除了时刻关注那些重大主题之外,在描述它的时候需回归到语言,而语言的开始便是想象,诗的意象则是现实世界的前意象,诗的节奏也是交替着的意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象是诗人的时间光谱。诗说到底其实是内心的建筑,因此,其表述结构、空间布排不应该是平面的,无论是梁、柱、椽、拱,都要通过榫来协调周边之关系,而且要让人看不到钉子,这才是合理的诗的建筑。
我觉得,诗从本质上说不是用来叙事的,其本体首先是人类创造性思维方式的保存形式。因此我认为,诗是应该直击真理和美感的,这样才能触动人们的心灵,通过韵律的脉动,去超越现实的疆界。按理说,长诗是应该靠诸多画面去点亮的,需借助暗喻而发光,从而去显示世界和灵魂的富饶,因为只有这样,诗歌才能完全融入生活并被读者分享。
我们生活在一个用点点滴滴的现实来架构的世界里,诗歌不是逃避现实的手段而是接近现实的手段。《铿锵之韵》对胡松夏来说,意味着他找到了某种诗的表达方式,以便使其他人理解他的一些无法解释清楚的经历、感受和想法。可以说,长诗《铿锵之韵》是他个人经历的产物。作为读者,我们需要以崇高的敬意和热爱来了解他的意图和行为。因为即使最伟大的诗人也往往会低估了能够产生实际行动的潜在的理解和感知能量。
长诗《铿锵之韵》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尽管我们已取得具有挑战性的技术进步,但我们依然面对动荡不安的现实环境。胡松夏的诗呈现出业已存在却无从看见的一切,他用诗的桥梁,连接过去与未来,让我们充满了对前途的信心,这就是诗的力量所在。其实,诗是可以稀释物质世界所带来的苦闷的,我们也可以从长诗《铿锵之韵》中,提炼出一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民族精神。
艾略特说过: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我们的诗,只有在凝聚了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时,才能走向大气与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