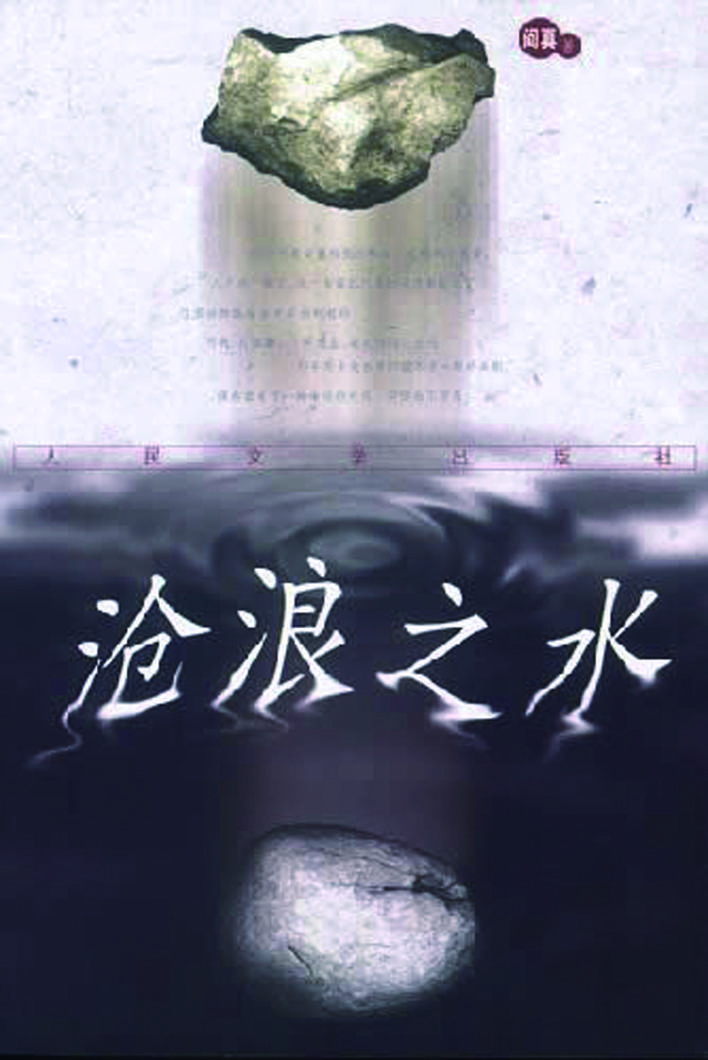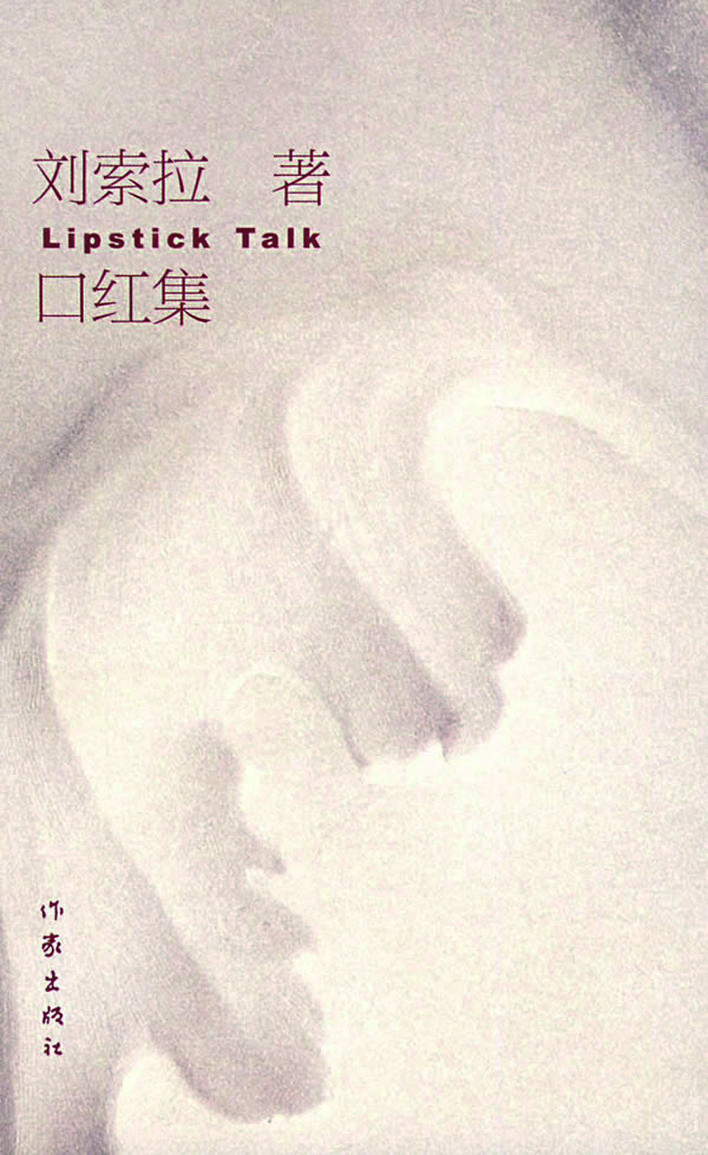“新移民文学”的崛起是20世纪世界华文文学发展中的大事件,它宣告了一个新的写作时代的到来。自上世纪80年代肇始,至今已将近30年,“新移民文学”无论是从概念命名上,还是从主体构成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最显著的现象之一是新移民作家群发生了分化,扎根西方与回归中国,成为“新移民”的两种基本选择,但更常见的情形是当前相当数量的“新移民”作家同时活跃在海外和大陆两个空间。回望2004年,陈瑞琳、张翎、沈宁、少君等创作者组团访问国内,如今新移民作家或以集体或以个体参与大陆的文学活动日益频繁,其中特别要提出的是“新移民作家国际笔会”已在中国(南昌、成都、西安)举办了三届。进入21世纪,我们发现,之前对“新移民文学”的界定已经越来越难以负载华文创作的多元含义。
“海归文学”不是新世纪以来“新移民文学”的特有现象,但它将是世界华文文学领域的一个新热点。20世纪初期,大批海归学人,以其丰富的创作实绩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新鲜与惊喜。我们暂且不去统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多少海归作家,仅仅是现代文学的六大家“鲁郭茅巴老曹”,就都有海外留学或者讲学背景,域外经验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归文学”并不是当前“新移民文学”发展中的新生现象,而可以看做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海归文学”的延续和发展。
今年5月施雨的《上海“海归”》的出版是一个信号,虽然书中的“海归”是有地域性的,但“海归”由“新移民”主体的再次提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考察视点,这既是“新移民文学”研究的一种细化,也是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主动接轨。
刘俊在《“新移民海归文学”:新立场、新视野、新感受、新文学》一文中指出“新移民海归文学”是海外“新移民”作家的一次新出发,是海外“新移民”作家的一次新开拓,是海外“新移民”作家的一次新蜕变、新升华。而这种种新变的发生动因是“新移民”作家的“二次文化震荡”和“二次身份转换”。如果将“新移民”的界定扩展,不局限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大陆移民海外的新移民,而是将这份名单延伸到港台,那么可以说,“新移民海归作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例如,旅欧的刘索拉,回国后创作了《女贞汤》《口红集》;龙应台回台后推出了《亲爱的安德烈》《目送》;虹影常住北京,往返中欧之间,相继推出了《上海王》《上海之死》《好儿女花》;旅美的施雨,今年完成了《上海“海归”》;薛海翔曾经是90年代美国“新移民文学”的重要力量,现居住上海从事影视剧编剧;旅加的阎真90年代归国后更是创作了重量级小说《沧浪之水》。
若将“新移民海归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进行宽泛地解释,目前“新移民海归文学”的对象包括两个作家群体。第一,是指居住国内但已拥有外籍身份的“新移民”;第二是保有中国国籍留学归国的学人。在现代文学领域,为中国文学做出重大成就的学者和作家通常是后者身份。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种身份的创作者将是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潜在的庞大作家群,即“70后”、“80后”的中国留学生,这也就与王列耀提出的欧美华文文学的“后留学生文学时代”相呼应与对接。但就目前创作实绩来说,我们关注的“新移民海归文学”的对象多属于第一种身份背景。
较之“新移民作家”,“新移民海归文学”创作主体的创作视点发生了转移。张翎在2001年出版《交错的彼岸》时说“写作就是回故乡”,她的话道出了一批“新移民文学”作家的心声,他们的共同立场是用文字抚摸故土,相对于大陆文坛作家而言,他们是“离场”者,以隔岸观照的姿态记述中国。而“海归文学”的创作者们已是一群“在场”者,他们以亲历的身份关注中国的文化传承与历史变迁,因此在文学表达上,海外创作最易被诟病的现象,即与中国现实当下之间的“隔”,在无形中就有可能被弱化直至消弭。
从总体上考察“新移民海归文学”,它的文学题材是丰富的,“海归作家”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领域都有积极的文学贡献。中国故事无疑是“海归文学”的创作重点。中国叙事是“海归作家”的主动选择。与之前的“新移民文学”立足于海外生活和域外体验不同,“海归文学”沉潜进中国社会,以中国想象和中国经验为他们的叙述重点。但正如刘俊指出的那样,这类“海归文学”的立场、视野和感受都具有杂糅性和融合性。施雨的《上海“海归”》展示了一种新的视角。她采访的对象都是扎根上海的“海归”,他们已与上海融为一体,他们考虑的事情是如何在中国更好地生活,而不是回归西方重拾理想和抱负。不可否认的是,“海归文学”作家因受中西文化的熏陶,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在潜移默化间渗透着西方的文化视野和自由诉求,因此他们的作品与大陆当代文学作品相比较,具有十分个性化的写作风格和思维角度。阎真是“新移民海归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的一个交集。自加拿大写作“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作《白雪红尘》(大陆版名《曾在天涯》)之后,阎真回国后创作了完全是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沧浪之水》,在自审和他审男性心灵世界的同时,也关注女性,完成了《因为女人》。应该说,阎真的“海归”创作已完全脱离了留学题材和异国图景,而是贴合现实生活,聚集当今中国的热点事件。他实现了从海外华人作家向中国当代作家的全然回归。
“新移民海归文学”在艺术追求上趋向扎实的现实主义。“新移民文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过对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积极追求,如当时美国活跃的“新移民”作家严力的精神分析、戴舫的解构、薛海翔的后设小说。但进入21世纪以来的“新移民文学”越发地回归“现实”,在“海归文学”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也成为很多作家追求的艺术风格。欧美华文文学与“新移民海归文学”共同推出了一批出色的现实主义小说,其中撼动人心的作品正是通过生动的文学想象达到逼近真实的艺术效果。在对中国故事的传达上,两者最大特点就是紧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两个“典型”是作者坚守的艺术原则。
对于“新移民海归文学”而言,我认为描写“海归”回国后的生活是更有新意的题材,也是受众最感兴趣的题材,因为它呈现出一种崭新的生活状态,它解除了“海归”的神秘,破除了受众对“海归”群体的艳羡与憧憬。这是大陆当代文学很难重构的现实体验,也是“新移民文学”无法传达的切身感悟,同时它适时而且恰当地体现着中西理念对新时代“海归”的思想冲击和情感争夺。“新移民文学”描摹出“新移民”“西化”过程中经历的精神阵痛,“海归文学”聚焦“归来的人”再次“本土化”后的生存困惑。钱锺书先生的《围城》正是“海归文学”不朽的经典。从严格意义上看,“新移民海归文学”仍是初始阶段,它还缺少些厚重与深刻,但它折射的西方视野和涵纳的西方文化赋予其思想的亮点,活泼又洒脱的语言表达展示着生气和灵动。目前,“新移民海归文学”还处于个体姿态的展示,即以单个作家的力量实现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对话,它的发展还需要整合更多的创作力量以形成集团优势,从而赢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我们期待“新移民海归文学”成为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