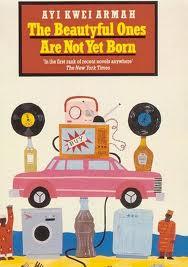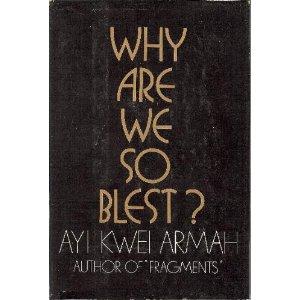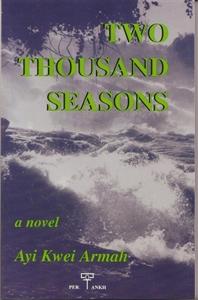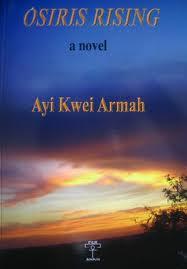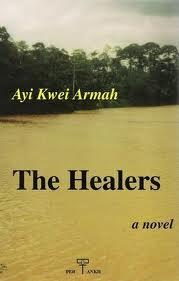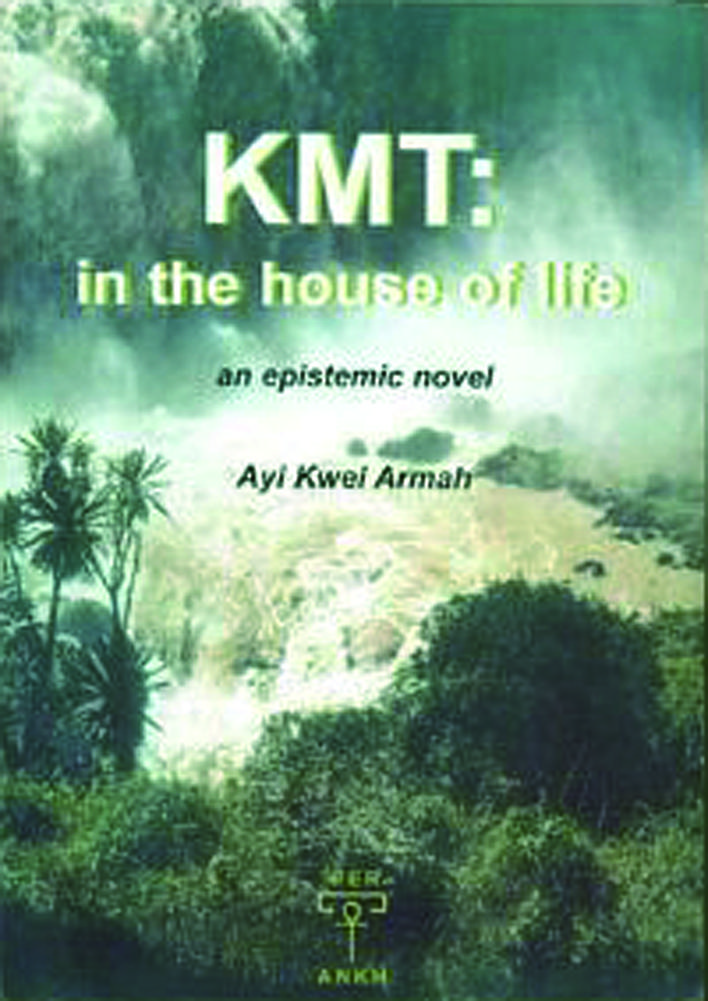英语文学在非洲乃洋洋大观,小国也不乏卓尔不群之人,加纳作家艾伊·奎·阿尔马(Ayi Kwei Armah, 1939- )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阿尔马生于滨海城市塔科拉迪,父母均为教师,但是来自不同的族群。因为家庭变故,阿尔马基本上由母亲抚养成人。他天赋极高,除了母语和英语,还精通法语,懂斯瓦西里语、阿拉伯语,甚至能解古埃及象形文字。阿尔马个性极强,高中毕业后赴美学习,曾拒绝富人资助,宁愿自力上大学。不久,又毅然中断在哈佛的学业,投身非洲革命。然而此行不为人理解,被迫折回波士顿。他对加纳的各方面均不满,学成后避而远之,但是对满目忧患的非洲却不离不弃,四方奔走,最终落脚于塞内加尔,从事创作和出版。阿尔马迄今已发表了7部长篇小说:《美好的尚未诞生》《碎片》《我们为什么如此有福?》《两千季》《医者》《奥西里斯的复活》和《克米特:在生命之屋》,还推出了自传《作家的雄辩》和散文集《牢记被肢解的大陆》。
由于非洲的后起和弱小,优秀作家常常难以独守祖国,故而寄希望于黑人大家庭,普遍具有泛非主义的情结。阿尔马既在其中,又是例外。其泛非主义理想覆盖整个非洲,时间上起古埃及,空间跨越撒哈拉。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首先在于他是跨部族和跨语言婚恋的产物,生来就有超越部族的思想意识。其次,作为加纳人,他对恩克鲁玛——泛非主义的倡导者之一——在本国的实践持完全否定态度,却接过法农的思想,希望通过武装斗争解放全非。最为重要的是,他去了塞内加尔,却并未投到法语区泛非主义统帅桑戈的麾下,而接受了该国埃及学学者契克·安塔·迪欧普的历史观:古埃及是一个黑人国度,其文明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文明的源头。迪欧普还提出了以历史联系为基础建立非洲合众国的设想。阿尔马在此基础上演绎出自己的非洲文学断代史:第一,现代非洲文学;第二,封建时代的口头文学传统;第三,大迁徙时期的传统;第四,克米特(古埃及)时期的手抄本传统。而他本人的创作正好反映了这种文学观。
阿尔马的创作分为前后两段:写个人的存在主义时期和写集体记忆的泛非主义时期。
阿尔玛的存在主义作品有三部。《美好的尚未诞生》不仅使阿尔马一炮而红,至今仍然为非洲存在主义的经典。故事发生在加纳主要海港塞康第-塔科拉迪双子城,时间为第一共和国时期的最后10天,以不具姓名的“人”为主人公。小说没有连贯的情节,主题既像是谴责党政官员的腐败,又像是写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的普通人的无所适从,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与揭露腐败相比,小说写普通人的部分更令人印象深刻。主人公是抽象的,既无身高,也无长相,睡觉时从大张着的嘴里肆无忌惮地流出唾液。“人”有中等文化,在港口铁路调度室上班。在独立斗争中,港口的码头和铁路工人曾给予人民大会党最有力的支持。然而独立7年后,他们连饭都吃不饱。社会上贿赂公行,致使守规矩的“人”成了被指责和嘲笑的对象。
在一片赞誉声中,加纳著名作家爱都和尼日利亚著名作家阿契贝均指出,阿尔马有滥用才能的危险。《碎片》写留学归国的巴科与环境的冲突,具有浓重的自传色彩。不过,与一般人推测的对环境的挑剔不同,巴科的不适应来自环境对他的苛刻要求:亲朋好友以为他会带轿车回来;以为他会在工作方面托人打点。在人才奇缺的祖国,巴科却成了多余的人。他邂逅了生于波多黎各、因为失恋出走非洲的美国人胡安娜,两个受伤的人走到一起。后来胡安娜休假回国,巴科孤寂难耐,精神再度崩溃。据说,巴科的名字来自特维语,意即“一个人”、“独自”,或者“孤独”,与《美好的尚未诞生》中的“人”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人”面临的是如何在污浊的世界上体面地生存,巴科面临的是如何在物欲横流的阿克拉保持精神的尊严。
《我们为什么如此有福?》光题目就是反讽,据说灵感来自于美国报刊上关于有福非福的一段议论: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人是有福的,反之则无福。小说的主人公索娄是归国留学生,属于有福之人。可是,他在西方不能忍受种族歧视,归国后又不能忍受推诿塞责,成了极为痛苦之人。故事取材于阿尔马在阿尔及尼亚的经历,也带有一定自传色彩。小说采用笔记结构,由三个主要角色轮番叙述。故事发生在北非的泪城,时间为独立战争末期。中断留学从欧洲回国抗法的索娄发现,人们并不看重他的革命精神和才华。比之更加不幸的是加纳人莫丁,他放弃在哈佛的学业帮助革命,却被推来挡去。被索娄收留后,莫丁仍不放弃,在苦等多日无果后,毅然抱定必死之决心找游击队去了。莫丁的白人恋人艾梅死死追随他。结果,两人被路过的法军欺骗,男的被折磨致死,女的被轮奸。
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非洲的优秀作家往往遭遇到“放逐”的问题。要么在政治上与政府发生冲突,不得不亡命国外;要么思想与环境格格不入,选择自闭。尼日利亚批评家纳多泽·音娅玛曾分析过阿尔马前三部作品的主人公与环境的关系,指出他们都属于自我放逐类型:身体虽然在加纳和非洲,但精神却游离于其外。阿尔马创造了这些角色,也知道他们的局限性,却不能为其找到出路。
从《两千季》开始,阿尔马进入了以历史为立足点的集体记忆时期,变得乐观起来。加纳只有旱季和雨季之分,所谓两千季就是一千年,指代从阿拉伯人侵略以来的历史。从表面看,小说以阿诺人被迫离开古苏丹的流徙为书写对象,实则借题发挥,广泛指代饱受侵略和奴役的非洲人民千年的历史,洋溢着泛非主义精神。故事依据加纳历史,却隐去其名,多有虚构。就叙述而言,则越往前越空虚,越往后越实在。前面主要传递史事,第四章才出现有血有肉的正面形象。虽然看起来是写人民与外敌的斗争,而于内部敌人着墨更多,显然另有所指。
《医者》的书名兼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所指。小说两者兼叙,但是以后者为主,并且有所生发。故事假借讲故事人世家之口,有一个模拟传统的开头。时间从远古洪荒开始,跨度比《两千季》更大,然后将镜头拉到目前,展现两个王国的内争外斗——其中之一是依据19世纪加纳的第二次阿散蒂战争写成。内部斗争则联系到对白人是抵抗还是投降的问题。不幸的是,投降派最终还是占了上风,英雄们只得潜伏下来等待时机。要理解《奥西里斯的复活》,首先需要了解奥西里斯(Osiris)这个词。奥西里斯是古埃及人的冥神和鬼判,同时又是司生育的女神伊希斯之兄和丈夫。据说在被嫉妒的弟弟塞思等人害死后,他的尸体被肢解了盛在匣子里,顺尼罗河漂流,直至被追踪而来的伊希斯等人连缀复活。从此奥西里斯又成了周而复始的生命的象征。阿尔马借用这个神话,首先用于历史概括,指自埃及开始的整个非洲的被征服、肢解、复活的漫长过程。另外,他还用传说中的关键人物构成了小说的框架,以奥西里斯指男主角阿萨,伊希斯指阿丝特,塞思指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塞思。故事发生于一个讲英语的非洲国家哈珀,重要角色阿丝特除了串联起两个男主角,还有揭示历史的作用:探寻安克的起源,从而为构建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为一体的非洲找到基石。用阿尔马的话说,《克米特:在生命之屋》是本“认知小说”。克米特是古埃及的别名之一,意为生命之屋,指非洲精神的源泉。小说分为三部分:学人、传统主义者、作者,中心思想是认知非洲历史的悠久,推翻欧洲人散布的非洲没有历史的陈说。
《两千季》之后,阿尔马的作品主要围绕清理和重构非洲历史展开,基本特点是把历史小说化。对于这种写法的利弊,最为中肯的意见来自美国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伯恩斯·林福斯。在他看来,《两千季》和《医者》的积极之处在于从个人向集体、从悲观向乐观的转变,缺点是将历史主观化和神话化。而后两部书的优点是在演绎历史的同时,有较为实在的生活描写。
阿尔马为人大胆而直露,笔力放纵,对污秽、死亡、性虐狂等概不避讳,反倒从变态心理的角度加以利用。因为想象力惊人,他的手稿总是能够敲开出版社之门。作为一个守望家园的作家,他在语言、意象、结构、印刷方面都做了民族化的努力,如主要角色的名字大多有加纳或古埃及的寓意,有些书的章节以本民族或者埃及语言词为标题。他还有意识地吸纳口头文学的要素。比如在叙述中适当安排听众插话,让角色具有某种神性,或者将对立面加以喜剧性的丑化等。
阿尔马为人孤傲,既不参加作家会议,也不接受采访,发表的言论不多。可能是考虑到已入老境,近几年接连推出了自传和散文选,豪迈不减当年。加纳文学在非洲和世界有一席之地,首先是因为有阿尔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