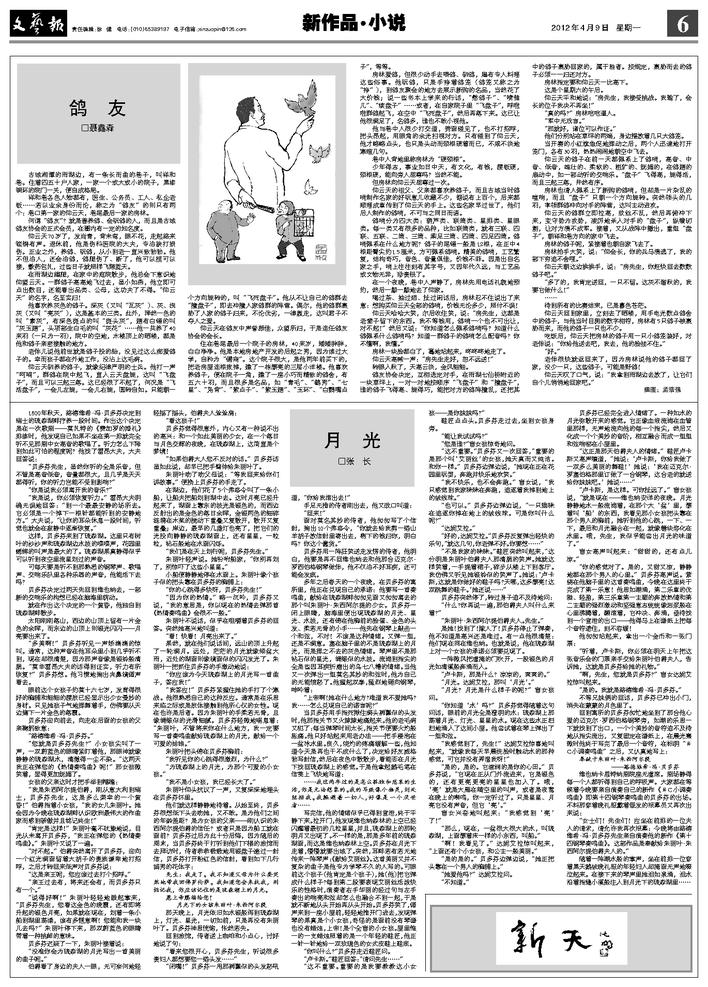1800年秋天,路德维希·冯·贝多芬决定到瑞士的琉森湖畔疗养一段时间。作出这个决定是在一次歌剧——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排练时,他发现自己如果不坐在第一排就完全听不见那剧中女高音的歌唱了。听力怎么下降到如此可怕的程度呢?他找了雷昂大夫,大夫回答说:
“贝多芬先生,虽然你听的全是乐音,但不管是高音低音,音量都很大,且几乎是天天都得听,你的听力岂能不受到影响?”
“你是说我必须离开我的音乐?”
“我是说,你必须恢复听力。”雷昂大夫明确无误地回答:“到一个最最安静的场所去。它必须是一个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到的安静地方。”大夫说,“让你的耳朵休息一段时间,听觉也就会在寂静中逐渐恢复。”
这样,贝多芬来到了琉森湖。这里只有树叶的沙沙声和琉森湖边水波的喋喋声,花园里蟋蟀的叫声是最大的了。琉森湖果真静得似乎可以听到夜空里流星划过的声音。
可每天要是听不到那熟悉的钢琴声、歌唱声、交响乐队里各种乐器的声音,他能活下去吗?
贝多芬决定过两天先回到维也纳去,一部新的交响乐的构想已经在脑海里萌动。
就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一个黄昏,他独自到琉森湖畔散步。
太阳刚刚落山,西边的山顶上留有一片金色的余晖,而东边的山顶上则银光闪闪——月亮要出来了。
“多美啊!”贝多芬听见一声娇滴滴的惊叫。通常,这种声音在他耳朵里小到几乎听不到,现在却很清楚,因为那声音像是银铃般清脆。“莫非雷昂大夫的话得到证实,听力有所恢复?”贝多芬想。他习惯地掏出夹鼻镜循声看去。
眼前这个女孩子约莫十六七岁,发育得很好的胸脯和细细的腰肢已经显示出少女曼妙的身材。只见她孩子气地挥舞着手,仿佛要从天边摘下一片金色的落霞。
贝多芬迎向前去,向走在后面的女孩的父亲鞠躬致意: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小女孩尖叫了一声,一双蔚蓝色的眼睛紧盯着他,那眼神就像静静的琉森湖水,清澈得一尘不染。“这两天我正在弹您的《热情奏鸣曲》呢!”那女孩微笑着,显得更加妩媚了。
女孩的父亲这时才把手举到帽檐:
“我是朱西阿尔提伯爵,刚从意大利到瑞士,贝多芬先生,这是多么荣幸的一个黄昏!”伯爵指着小女孩,“我的女儿朱丽叶。她会因为今晚在琉森湖畔认识欧洲最伟大的作曲家而感到骄傲并且铭记终生!”
“肯定是这样!”朱丽叶毫不犹豫地说,目光从未离开贝多芬,“我正在弹您的《热情奏鸣曲》。”朱丽叶又说了一遍。
“对不起。”伯爵突然离开了贝多芬,迎向一个红光满面留着大胡子的贵族谦卑地打招呼,之后才转回来低声对贝多芬说:
“这是亲王呢,您应该过去打个招呼。”
“亲王过去有,将来还会有,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说得好啊!”朱丽叶轻轻地鼓起掌来,“贝多芬先生,您看这金色的晚霞,还有即将升起的银色月亮,如果就在现在,划着一条小船到湖里荡漾,该有多惬意啊!您能和我一块儿去吗?”朱丽叶停下来,那双蔚蓝色的眼睛带着一种挑衅的意味。
贝多芬迟疑了一下,朱丽叶接着说:
“没准你会为琉森湖的月光写出一首美丽的曲子呢。”
伯爵看了身边的夫人一眼,无可奈何地轻轻摇了摇头,伯爵夫人耸耸肩:
“看这孩子!”
贝多芬觉得很意外,内心又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一个如此美丽的少女,在一个落日与月色交辉的夜晚,在琉森湖上,这简直是个梦境!
“如果伯爵大人您不反对的话。”贝多芬话虽如此说,却早已把手臂伸给朱丽叶了。
朱丽叶吻了吻父母说:“等我回来给你们讲故事。”便挽上贝多芬的手走了。
在湖边,他们花了5个弗洛令叫了一条小船,让船夫把船划到湖中去。这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湖面上靠东的波光是银色的,而西边反射出的是金色的落日余晖,金银两色的细碎涟漪在木桨的搅动下重叠又复散开,散开又复重叠;岸边,最早的几盏灯也亮了,把它们的光投向静静的琉森湖面上,还有星星,一粒粒,钻石般地在水面闪烁。
“我们是在天上划行呢,贝多芬先生。”
朱丽叶轻声说。她吩咐船家,“你别再划了,别惊吓了这些小星星。”
小船便静静地停在水面上。朱丽叶像个孩子似的把头靠在贝多芬的胸脯上:
“你的心跳得多快呀,贝多芬先生!”
“因为你的热情。”略一沉吟,贝多芬又说,“我的意思是,你以现在的热情去弹那首《热情奏鸣曲》会很不一般。”
朱丽叶不说话,似乎在咀嚼着贝多芬的回答。突然她高兴地叫道:
“看!快看!月亮出来了。”
果然,就在他们说话间,远山的顶上升起了一轮满月。远处,茫茫的月光就像倾盆大雨,近处的湖面则像镜面似的闪闪发光了。朱丽叶一把抓住贝多芬的手激动地说:
“你应该为今天琉森湖上的月光写一首曲子,答应我!”
“我答应!”贝多芬紧握住她的手打了个寒战。他很熟悉自己的这种反应。通常是在乐思来临之际或是肢体接触到他所心仪的女性。现在也许是后者。因为朱丽叶的手柔若无骨,且像绸缎似的光滑细腻。贝多芬轻微地喘息着:“朱丽叶,不管将来你在什么地方,我一定要写一首奏鸣曲献给琉森湖上的月光,献给一个可爱的姑娘。”
朱丽叶把头倚在贝多芬胸前:
“我听见你的心跳得很激烈,为什么?”
“为琉森湖上的月光,为那个可爱的小女孩。”
“我不是小女孩,我已经长大了。”
朱丽叶仰头抗议了一声,又复深深地埋头在贝多芬怀里。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待着。从始至终,贝多芬很想低下头去吻她,又不敢。是为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是为女孩的父亲——刚认识的朱西阿尔提伯爵的信任?或者只是因为船工就在面前?贝多芬过后为此十分后悔,因为随后的周末,当贝多芬终于打听到他们下榻的旅馆而去拜访时,侍者恭恭敬敬地用银盘子递过一封信,贝多芬打开粉红色的信封,看到如下几行娟秀的花体字:
先生:我走了。我不知道父母为什么要突然地带我回佛罗伦萨。我知道您会来找我,别惦记我,你应该记住的是琉森湖上的月光。
愿上帝赐福给您!
月光下的女孩朱丽叶·朱西阿尔提
那天晚上,月光依旧如水银般泻到琉森湖上,灯光、星光,一切如前,只是再没有朱丽叶了。贝多芬神思恍惚,怅然若失。
回到旅馆,侍者送上咖啡和小点心,讨好地说了句:
“看来您很开心,贝多芬先生,听说很多贵妇人都想要您一绺头发……”
“闭嘴!”贝多芬一甩那狮鬣似的头发怒吼道,“你给我滚出去!”
手足无措的侍者刚出去,他又改口叫道:
“回来!”
面对莫名其妙的侍者,他匆匆写了个信封,掏出10个弗洛令,“你就去给我剪一绺山羊胡子放信封里寄出去,剩下的钱归你,明白吗?你这个蠢货。”
贝多芬用一阵狂笑送走发愣的侍者,他明白,他要是再不回维也纳去和他那台迈克尔·罗西伯格钢琴做伴,他不仅治不好耳疾,还可能会发疯。
多年之后春天的一个夜晚,在贝多芬的寓所里,他正在兑现自己的承诺:他要写一首奏鸣曲,献给在琉森湖畔匆匆见面又匆匆离去的那个叫朱丽叶·朱西阿尔提的少女。贝多芬一闭上眼睛,脑海里便出现琉森湖的月光、星光、水波,还有倚在他胸前的脸蛋、金色的头发、柔若无骨的小手……他先在钢琴上敲击一个和弦,不对!不该是这种情绪。又弹一组,还是不满意。塞在脑子里的不是琉森湖上的月光,而是挥之不去的灰色情绪。琴声里不是那钻石似的星光,绸缎似的水波。流淌到指尖的全是些因耳疾折磨出的乌七八糟的情绪。当他又一次弹出一组莫名其妙的和弦时,他为自己的无能愤怒了。他握起双拳,猛烈地砸向钢琴,呻吟着:
“上帝啊!她在什么地方?难道我不爱她吗?我……怎么兑现自己的诺言呢?”
当贝多芬用手指死揪住满头狮鬣似的头发时,他那指关节又火辣辣地痛起来。他的老毛病又犯了:每当弹琴时间太长,指关节便要火灼般胀痛。他只好站起来用老办法——把手浸泡在一盆冰水里。良久,烧灼的疼痛缓解一些,他知道今天是再也干不成什么了,决定给好友威格勃写封信,然后在夜色中散散步,看能否在月光下找回琉森湖上的感觉。于是他拿起鹅毛笔在信笺上飞快地写道:
……我这两年过的是怎么孤独和悲哀的生活,你是无法想象的。我的耳疾像个幽灵,到处阻挡我。我躲避着一切人,好像是一个厌世者……
写完信,他的情绪似乎已得到宣泄,终于平静下来。拉开门,他发现维也纳森林的上空已经闪耀着最初的几粒星星,并且,琉森湖上的那轮明月又出现了。不一样的是,那是多年前的琉森湖面,而这是维也纳森林上空。贝多芬在月光下走着,慢慢就要出城了。突然,耳畔若有若无地传来一阵琴声:《献给艾丽丝》。这首美丽又并不复杂的曲子是他专为学琴不久的人写的。可眼前这个孩子(他肯定是个孩子),她(他)把它弹成什么样子?每到第二段要表现艾丽丝活泼快乐的性格时,演奏者右手华丽的经过句与左手奏出的响亮和弦却怎么也融合不到一起,于是就不断地从头开始再从头开始。贝多芬笑了,循声来到一座小屋前,轻轻地推开门进去,发现弹琴的果真是个小女孩,奇怪的是面前没有琴谱也没有蜡烛,上帝!是个全盲的小女孩。屋里惟一的一支蜡烛照着的是一个年轻的鞋匠,他正一针一针地给一双玫瑰色的女式皮鞋上鞋底。
“你叫什么?”贝多芬走近鞋匠问。
“卢卡斯。”鞋匠回答:“请问先生……”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教教这小女孩——是你妹妹吗?”
鞋匠点点头。贝多芬走过去,坐到女孩身旁。
“能让我试试吗?”
“您是谁?”盲女孩惊奇地问。
“这不重要。”贝多芬又一次回答,“重要的是那个叫‘艾丽丝’的女孩,她天真而又纯洁。和你一样。”贝多芬边弹边说,“她现在正在花园里玩耍,奔跑并快乐地欢笑。”
“我不快乐,也不会奔跑。”盲女说,“我只感觉到我家咪咪在奔跑,追逐着我掉到地上的绒线球。”
“也可以。”贝多芬边弹边说,“一只猫咪在追逐你掉在地上的绒线球。可是你叫什么呢?”
“达妮艾拉。”
“好的,达妮艾拉。”贝多芬反复弹出轻快的乐句,“就这几句,你老弹不好。你要想……”
“不是我家的咪咪。”鞋匠突然叫起来,“这分明是朱丽叶伯爵夫人那清脆的笑声。她就这样笑着,一手提着裙子,碎步从楼上下到客厅。我仿佛又听见她银铃似的笑声了。她说:‘卢卡斯,这就是你做好的鞋子吗?天哪,这多漂亮!这双跳舞的鞋子。’她还说……”
贝多芬突然停了,转过身子迫不及待地问:
“什么?你再说一遍,那伯爵夫人叫什么来着?”
“朱丽叶·朱西阿尔提伯爵夫人。先生。”
是她!找到了!嫁人了!贝多芬停止了弹奏,他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有一点他很清楚:他们现在同在维也纳。也就是说,他在琉森湖上对一个女孩的承诺必须要兑现了。
一阵微风把虚掩的门吹开,一股银色的月光如清溪般奔涌而入。
“卢卡斯,那是什么?凉凉的,爽爽的。”
“月光。达妮艾拉,那叫‘月光’。”
“月光?月光是什么样子的呢?”盲女孩问。
“你知道‘水’吗?”贝多芬觉得随着这句问话,眼前的月光全是澄明的水:琉森湖上那荡着月光、灯光、星星的水。现在这些水正汩汩地涌入了这间小屋。他尝试着在琴上弹出了一组和弦。
“我感觉到了,先生!”达妮艾拉惊喜地叫起来,“就像我每天早晨洗脸时触动水的那种感觉,可它并没有弄湿我呀!”
“是的,是的。它滋润的是你的心田。”贝多芬说,“它现在正从门外流进来,它是银色的,还有更亮更亮的星星也加入了。哦,‘亮’就是大雁在晴空里的叫声,或者是夜莺在晚上的啭鸣,你一定听过了。只是星星、月亮它没有声音,但它‘亮’。”
盲女兴奋地叫起来:“我感觉到‘亮’了!”
“那么,现在,一盆很大很大的水,叫琉森湖,上面漂着床一样的小东西,叫船。”
“啊!我看见了。”达妮艾拉惊叫起来,“上面还有个小女孩,和公主一般美丽。”
“是的是的。”贝多芬边弹边说,“她正把头靠在一个男人的胸脯上。”
“她爱他吗?”达妮艾拉问。
“不知道。”
贝多芬已经完全进入情绪了。一种如水的月光弥散开来的感觉。它正像血液流淌在血管里那样,无声地流向他的每一个指尖,然后又化成一个个美妙的音阶,相互融合而成一组组和弦响彻在小屋里。
“这正是那天伯爵夫人的情绪。”鞋匠卢卡斯又高声嚷道,“她说:‘卢卡斯,你给我做了一双多么美丽的舞鞋!’她说:‘我在迈克尔·罗塞伯格那里订做了一台钢琴,这台老的就送给你妹妹吧。’她说……”
“卢卡斯,是这样。可你扯远了。”盲女孩说,“就是现在——维也纳安详的夜晚。月光静静地水一般流淌着,在那个大‘盆’里,漂着叫‘船’的东西,我看见那小女孩把头靠在那个男人的胸前,她听到他的心跳,一下、一下,最后和月光融合在一起,就像糖块溶化在水里。哦,先生,我似乎能尝出月光的味道了。”
盲女高声叫起来:“甜甜的,还有点儿凉。”
“你的感觉对了。是的,又甜又凉,静静地都在那个男人的心里。”贝多芬高声说。萦绕在他脑子里的这首奏鸣曲,今晚在这里终于完成了第一乐意!他思如潮涌,第二乐章的优雅、轻盈,第三乐章第一主题的奔放热情和第二主题的强烈激动和坚强意志统统像岩浆般在心里沸腾着,翻滚着,它冲决、奔涌,亟待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他得马上在谱纸上把每个音符逮住,刻不容缓!
他匆匆站起来,拿出一个金币和一张门票:
“听着,卢卡斯,你必须在明天上午把这张音乐会的门票亲手交给朱丽叶伯爵夫人,告诉她,这就是贝多芬给她的礼物。”
“啊,先生,您就是贝多芬?”盲女达妮艾拉惊叫起来。
“是的。我就是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不等兄妹俩的回话,贝多芬已冲出小门,消失在蒙蒙的月色里了。
回到寓所的贝多芬匆忙地坐到了那台他心爱的迈克尔·罗西伯格钢琴旁,如潮的乐思一下就找到了出口,一个个美妙的音符迫不及待地从指尖流出,又复固定在谱纸上,在晨光熹微时他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音符,在标明“﹟C小调奏鸣曲”之后,又认真地写上:
奉献于朱丽叶·朱西阿尔提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维也纳卡恩特纳剧院座无虚席。剧场静得每一个人都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声。大家都在等候着今晚要亲自演奏自己的新作《﹟C小调奏鸣曲》即第十四钢琴奏鸣曲的贝多芬的出场。不料那穿着晚礼服戴着假发的报幕员又再次出来说:
“女士们!先生们!应坐在前排的一位夫人的请求,请允许我再次报幕:今晚将由路德维希·冯·贝多芬先生亲自演奏他的新作《第十四钢琴奏鸣曲》。这部作品是奉献给朱丽叶·朱西阿尔提伯爵夫人的。”
随着一阵潮水般的掌声,坐在前排一位穿着黑天鹅绒晚礼服的年轻妇人却掩面无声地啜泣起来。在接下来的琴声里她泪如泉涌,泪水沿着指缝小溪般注入到月光下的琉森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