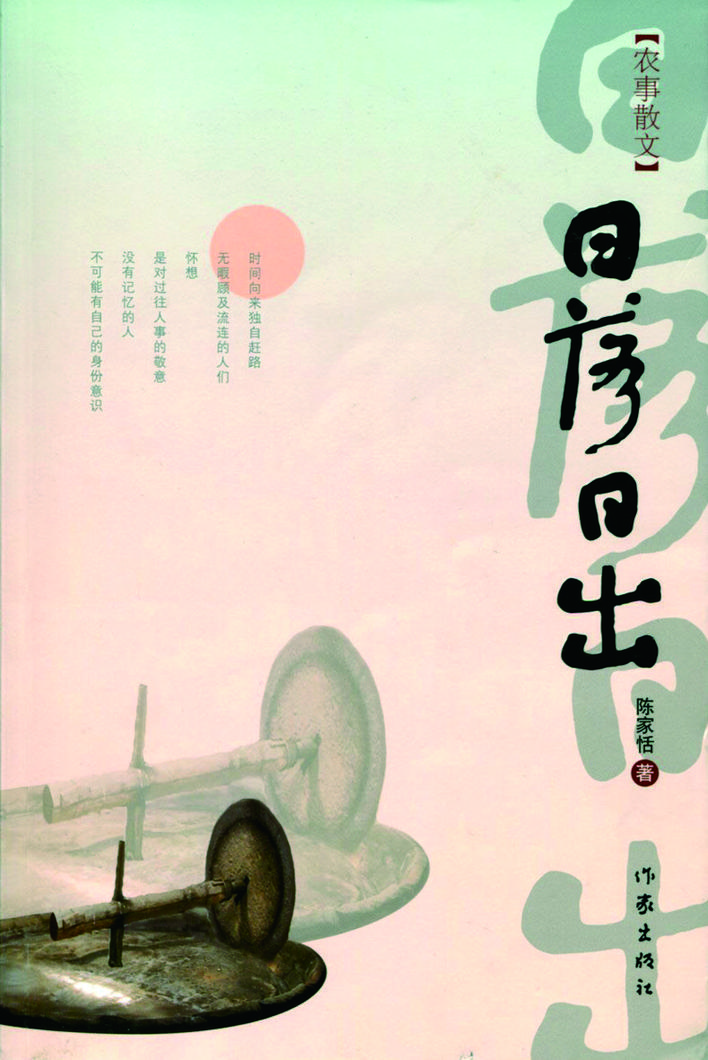作家陈家恬的“农事散文”集《日落日出》,以细腻的语言描写了他所熟悉的农家生活,真实地记录了与村庄、家园、习俗、土地有关的种种人和事。作者以从容的姿态梳理着农事、农具、农物,自然地呈现了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工艺细节,对亲人、朋友以及东南海滨先民们的谋生历程也有着感人的描述。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许多村庄徒存形骸,像空心的老树。这是一本包含着文学特质的类似文化考古的开掘和留存的奇书。作者对历史的回忆其实是对未来的沉思与救赎。书中百余帧插图隐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无疑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番薯啊,番薯
虽说“番薯不怕羞,一直到秋”,但最好的时节是小满、芒种。这时节的雨,似乎明白番薯栽的心事,淅淅沥沥,下过一阵,就歇息了。日头也知趣地躲开,半天不露脸——即便露脸,也只是开些温和的日头花——几多朦胧,几多羞赧,像一群礼仪小姐,奉命点缀,很快又匿影藏形。这是榨番薯的好时光。人们赶紧坌地、整垄,赶紧备好番薯栽,把它榨入地里。
备番薯栽是细活。把细长的往往带着露水或雨水的番薯藤搂回来,堆于走廊或厅堂。搬来矮凳,坐在它面前,或是股川下压着草镰柄,或是右脚尖踩着镰刀柄,刀口向上,尾巴翘起。抽过一条番薯藤,双手大拇指和食指拈着它。从尾部开始,向下轻轻一压,再向前轻轻一推,割下一茎。尾部较嫩,稍长些,四五节。其余三四节即可。有的也用铰刀铰。番薯栽用稻草缚成捆。每捆100条,通常叫“一把”。一把番薯栽能榨多少地,人们心中有数。在描述某处番薯地多大时,乡亲们往往就说“几把地”。
“大自然中,最微小者最卓越。”借用1900多年前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的这句话来评说番薯,也是恰如其分的。番薯不畏贫,不讳贱,随遇而安——只要有些泥土,有少许雨水,有阳光,无论沟墘,还是路旁,它都不会嫌弃,都会愉快地生长,更不用说良田好地了。
不过,榨番薯栽是大有讲究的。左手托一把番薯栽,跨过垄沟,以宗教般的虔诚,弯下腰来。右手抽出一茎番薯栽,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呈捉笔状,拈于番薯栽下端,无名指和小拇指并拢,弯成锄头形,掘下,番薯栽便被带到了适当的地方——抽手的时候,尽量让番薯栽挺立着——倘若歪歪斜斜的,不仅降低成活率,而且多生小番薯。然后在其周围扫些泥土,稍稍捏一下,顺势轻轻压实,保持水分,也耐曝。深浅也要适度——关键看节气,夏至之前,整茎可没入土中;夏至之后,则要伸出土外一节,以利生根发芽。伴随着手指头与泥土摩擦的疼痛,一茎茎半拃长的番薯栽,榨入松软的番薯垄,成为数不胜数的感叹号。
从上述一连贯动作看,其关键在于一个微妙的动词——榨。乡亲们只说榨番薯,而不说栽番薯,不说种番薯,也不说插番薯。这是他们的独到见解,颇具哲理。一个新的生命,往往在一定的压力下诞生。
几天下来,右手手指有的被泥土啃掉指甲,有的被泥土啃掉皮。说实话,如果仅有这些皮肉之苦,尚可忍受——最为痛苦的是不能自由地劳作,自由地榨番薯。父亲说,1959年初夏一天拂晓,他利用生产队的犁与牛犁番薯园,由于过度紧张,犁铧插入石缝,犁镜断裂。被人告密后,父亲遭到食堂堂长呵斥,全家被断伙食3天!翌日一大早,父亲先撩好番薯垄沟,中午再去榨番薯栽。堂长权大,耳朵也长,跑去夺番薯栽,两人各抢一半在手,彼此哭笑不得。堂长极不甘愿,气呼呼地跑到我家,掳走煮饭的铁鼎,掳走积肥的尿桶,意欲釜底抽薪,斩断我们全家的活路,以体现他对集体的忠诚。
如果持续放晴,番薯栽是受不了的。头几个傍晚,最好给它们沃水安根。那是件难事。番薯地大,番薯栽也多。地里没水,去远处的山涧、水渠或泉眼担水,路也难走,有的地方根本没路。好不容易担来一担水,极省俭地沃,也沃不了多少。其实那不是沃,是斟,斟酒似的,对准它们饥渴的小嘴,淅沥几滴。它们感恩似的,“叽里叽里”地鸣谢,又像醉汉打嗝,口气里充满泥土味和幸福感。萎靡不振的叶片,再经夜露的勉励,又焕发精神,舒展开来。
五六天后,它们举着一些新旧夹杂的叶子,酷似漫卷的旌旗。
再过30多天,中耕开始。中耕之说,似乎过于委婉。还是乡亲们说得直白:锄番薯。当然,新地的番薯,即使不锄,不施肥,也会有令人欣喜的长势。而旧地则不然。不锄,别指望有好收成。锄番薯颇有道道。泥土太干燥的,不宜锄,否则会影响番薯生长;太湿的,也不宜锄,否则会造成泥土板实。杂草多的,要先拔除。杂草少的,可直接锄垄底。然后斜着锄头,锄松垄沟两侧的泥土,深度以不伤害番薯栽主根为限。对于番薯头周围的泥土,只能用锄銎轻轻敲松。锄好之后,施些肥,一小撮化肥,一小把土粪,一小墣圊肥,一小瓢粪便,乃至一小束杂草,番薯都会笑纳。最后撩垄沟,不是每沟都撩,而是隔一沟撩,盖住肥料,闷死杂草。
再过十多天,施肥也好,不施肥也罢,都要把另一沟撩起。心满意足的番薯兴奋着,快速发蔸,郁郁葱葱。
番薯藤爱长纤维根,也爱长牛蒡根。这些根须很贪婪,旁逸斜出,吮吸营养,偷生小番薯。主人并不感激,因为它浪费了土地肥力,分散了主根精力,长不了大番薯,违背了主人的初衷。
番薯藤漫爬之际,必须抽出时间,到番薯地里,与榨番薯一样,弯下腰来,拔去所有争夺养分的杂草,托起茂盛的番薯藤,拢一拢散漫的行为,收一收旁骛的心思,扯断藤蔓上的气根,抠去藤头处的副根,预防“计划外生育”。如此这般,每月侍弄一次,共需两三次。细心的人几乎都会把每一垄的番薯藤牵成长辫状,从塍边披下来,或长或短,墨绿墨绿的,在风中飘逸。这叫牵番薯。
牵番薯是一种苦活。别说整天弯腰劳作,单是地里冒出来的热气,就让人受不了。何况还有许多蠓虫。最可怕的是一种土名叫大头垢的蠓虫,吸血手段异常高明,叮人,不痛,也不痒,直到它吃饱喝足,远走高飞了,才会渐渐感到肿痛——长时间的肿痛。还有垄沟里生有孑孓的秽水,也会“咬坏”手脚,先是奇痒,继而溃烂——非用腌制的杨梅或青梅涂抹不可;不过,会被齁得龇牙咧嘴。
七月半以后,有的人开始割番薯藤尾喂猪。那是上等饲料,深受猪的喜爱。有时也择些嫩叶,炒了配饭,味道不错;但吃多了,会腹泻。
中秋过后,三餐难保的人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剜番薯——来到地里,像老鼠一样顺着垄沟,找些较粗的番薯头,从裂缝处插入手指,探索着,触及番薯,食指钩了钩,约略锄柄那么粗,上下刮了刮,摸了摸,不短,甚是欣喜,但又觉得可惜——犹豫之中,番薯蒂却“呱哒”一声断了,探出番薯头来,流着如乳似泪的番薯汁。
进入白露,番薯花盛开,或淡紫,或乳白,或粉红,平添了番薯地的妩媚。那是一种成熟的美。好色的昆虫,嗜蜜的昆虫,不经意间的授粉,也会留下情种——褐色的蒴果。
番薯的成熟是艰难的。除了主人,它的好友仅剩阳光、月亮和雨露。而它的敌人却越来越多。
番薯地常有一种酷似茶籽蛀虫的小虫,俗称茶籽虫。它不过两粒米那么长,软体,苍白,看似孱弱,却是番薯的头号天敌。混账的它钻入番薯,一直躲在里面,搞它的隐蔽工事——开凿隧道,边开凿边享受,给番薯留下一个个臭洞!如此的番薯,即使再多,再大,再好看,也是废物一堆。无论生的,还是熟的,啃上一口,满嘴恶臭,满嘴辛辣,而且有毒。
野猪似乎看透了人的无奈。早已知道那些七倒八歪的稻草人,偶尔作声的破铁桶,统统是吓唬它的把戏。即使光天化日,它们也敢为所欲为,依靠獠牙,拱出番薯,暴食一番,遍地狼藉,惨不忍睹。
豪猪相对委婉。它的前脚仿佛灵敏的探测仪,几乎不做无用功,在番薯头坌开一小缝,便知有无番薯,若有,就继续坌;若无,就咬断番薯头解恨,直到找到番薯,吃饱了,甘愿了,离去。饿了再来。它食量并不大,但由于持续的破坏,枯萎的番薯也是触目惊心的。
比起野猪和豪猪,老鼠的危害则小得多,属于尚可原谅的那种。老鼠以它灵敏的嗅觉,探测番薯,挥动利爪,坌开泥土,大快朵颐之后,使出浑身力气,啃下几块,叼回去,填充空荡的巢穴,满足发痒的牙齿。被老鼠咬过的小番薯,没有断蒂的,依然顽强地长大;断蒂的,有的慢慢溃烂,有的则倔强地萌芽,好比三毛的头发。
番薯像人一样,也会生病,比如瘟病、疮痂病、丛枝病,比如黑斑病、白绢病;也有寄生虫,比如卷叶虫、斜纹夜蛾、天蛾,比如蛀藤虫、象鼻虫……
番薯的成长,要忍受太多太多的疾病折磨,抵抗不计其数的虫害侵扰。
那两只草蜢,可能是番薯地最后的守望者。番薯叶捋的捋,枯的枯,地上巴掌大的油桐叶也无力给予庇护,差一点被威猛的红嘴蓝鹊叼走,被凶残的棕背伯劳啄死。在柔和的冬阳下,它们举行告别仪式:以一片即将掉落的番薯叶为掩护,瘦的那只举起前脚,向胖的那只屈屈伸伸,胖的那只也举起前脚,向瘦的那只伸伸屈屈,相互致意之后,各自走开。没走几步,胖的那只走不动,瘦的那只踅回来,靠近它,耳语几句。
这一小品是偶然窜入我的视线的。我没兴致多看。毕竟我关注的只是地里的番薯,那些目力所不能及的番薯,即将揭开谜底的番薯,是多,是少,是大,是小,有无麻蛆,有无臭洞。
番薯,只有番薯,才是关乎我们生存的基本物质;精神需求的东西离我们还很遥远,无法兴奋我们的神经。我,我们全家人,我的父老乡亲,所有的期盼都归结为——番薯及其衍生物。
“人不亏地皮,地不亏肚皮。”番薯最知感恩。谁付出多少,它就回报多少。一到秋天,“子母勾连,如拳如臂”,从土里探出头来,开口报告的每一句,都是丰收的喜讯。亩产高得很,上好的番薯地一亩可掘五六千斤,中等的番薯地一亩可掘四五千斤,一般的番薯地一亩也可掘两三千斤。番薯成熟时,若从番薯垄踏过,可听见一声声脆响,有如萝卜折断的脆响。
曾经听说一个关于番薯的神话:那茎白薯栽是榨在烧炭多年,堆积许多灰烬,荒废多年的炭窑地的。它迅速生长,粗壮而繁茂,爬满一地,每一节、每一条气根都落下番薯,个个都像金瓠,总共掘出五百多斤!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现实神话。我多么希望自家地里也能长出这样的神话。
线 面
小时候,我常去邻居那里看做面,常在面埕上玩耍,了解做面的流程,知道做面的艰辛。
“欲图二分利,须起五更床。”面匠总是早起的,首先看天,好天,必做面。
起用新面粉,一般要先测它的筋道——拈些面粉,放于嘴唇,舔一下,捻成小面团;黏于食指,大拇指配合食指捏弄,或将小面团置于掌心,用手指头黏吊,面筋如果细如藕丝,就是好面粉,可用来做面。做面使盐——有言(盐)在先,盐是少不了的。具体加多少,要看气温,气温高,就略多些;气温低,就略少些。通常每10斤面粉,夏秋季节加盐8市两,冬春季节加盐6市两,四季不同;配水四五市斤。
正式做面始于和面。面粉倒入大陶盆,打散,加入兑好的盐水,即可和面。面匠双手呈蟹螯状,沿盆边深入,自下而上,由里到外,或搅,或铰,或搓,或搋,或翻,极尽手之能事。将整盆几十斤面粉搋成一团之后,握紧拳头,像练拳击一样捶它。洒些水,即有凝脂般的柔滑。
和毕,上案。将五六十斤的面团搬上面案,谈何容易!最恼人的是,不能双手同时用力往上掇,只能右手扯一下,左手扯一下,左倾右斜,反反复复,就像拔树,使劲撼动,渐渐扯断根须——彻底破坏了面团与陶盆如胶似漆的关系后,双手掌心向上,沿盆边探至盆底,两肘慢慢靠拢,突发丹田之力,将它托起,倏地转身,抛于面案。如此这般,看似蛮劲,实乃巧功——顺势而为。
看着案上的面团,面匠长吁一气,像宰了一头大肥猪。那一瞬间,若拿捏不准,有一缕下垂,就会绊落陶盆。那时一个大陶盆的价值相当于如今的一台电冰箱。
若用木盆和面,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不仅可降低和面难度,而且会出现日本作家盐野米松《留住手艺》书中所记述的那种奇效:“如果和面不用木盆而改用搪瓷盆,和出的面一定不如木盆和出的好吃,因为木盆能吸水,和面的时候,面粉不会粘连在盆上,这一点是搪瓷盆做不到的。”搪瓷盆做不到这一点,陶盆显然也做不到。也许是因为木盆没有经过武火烧烤,它的身上还有活着的树的细胞,而搪瓷盆、陶盆是高温烧制的,它的周身全是死去的泥土,不会有呼吸的可能。即便是再普通不过的木盆,其实一点也不普通!为什么不用木盆和面呢?
随后,面匠将面团切成两块,分别放入两个小陶盆,约略半个钟头。这个过程叫醒面,俗称走剂。“醒”也好,“走”也罢,总而言之,在盐的撩拨下,又经手的抚摸,水的浸润,熟睡的面粉便兴奋起来,扭动起来——面匠的第三只眼睛定能窥见从它白璧般的体内倾吐出来的亿万缕缠绵的情丝。
接下来,面匠抓起一把事先碾细的番薯粉,撒于面案。从小陶盆里倒出面团。摊开双掌,掌心向上,伸入面团底部,用力地抖、抛、抻,使之铺张开来,再擀平。随即视其厚薄,均匀地切成三四指宽的板条。面案右端放一个用于盘条的小陶盆,在它脚下靠后一点放一小碗茶油。准备就绪,可开始搓油条。面匠伸手将板条从头到尾轻轻托一遍,顺势将它挪到便于搓条的位置。搓条时,两手与肩同宽,掌心向下,前后搓搋,同时自右向左移动。左掌将板条搓成圆条坯,右掌再把它搓成锄柄大的均匀而光亮的圆条——通常是手移而人不移,当右手向左搓到尽头时,圆条也就成形了;然后给圆条抹些茶油,再搓搋,使之均匀后,抛向小陶盆脚边。搓完油条,盘满小陶盆,搬到面案左边的矮凳上,盖上麻袋。约过半个钟头,开始搓粉条。面匠坐于面案左边。面案中间放一小堆番薯粉,右端放一个盘粉条的小陶盆。搓粉条时,面匠左手将油条抽到面案上,稍加搓搋,右手使劲把油条搓成小拇指那么大——搓时由外往内,搓一大节;抛时又由内往外,但见油条仿佛跃动的银鳗从胸前倏地飞出,“噗”的一声,滑过番薯粉堆,穿过应声而起的“白烟”,蹿到小陶盆边——晶亮的油条已成雪白的粉条。助手连忙它把盘入小陶盆。抛条与抽条同时进行。搓完一条,右手捏住粉条的头,左手从小陶盆里拈起另一个油条的头,黏接好,继续搓。整个过程,亦动亦静,有形有状,声色俱佳,美不胜收。粉条由助手盘满小陶盆,盖上麻袋——如果空气干燥,要先遮塑料布,再盖麻袋,让它继续走剂。
早饭后,着手绕条。面匠站在一个叫羊头的木架前,中间隔着小陶盆,两根面箸插到羊头架横杆上,拈起粉条一端,黏于面箸里头。两手轻轻托住粉条,呈“8”字形,由左到右,穿梭似的,由里而外,一条条绕满面箸,少则五六十目,多则八九十目,因面粉筋道而异。持续同一姿势站立,双手轻巧、迅捷,其间辛苦,非亲历者不能知。
绕满一箸,松櫼,退出右边的面箸,让其自然下垂。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左边面箸的前端,拔出,插入羊头架最左边的圆孔。松手,用嘴衔住,双手握住下面的面箸,向下抻一抻,挂到面斛里,盖上麻袋,继续走剂。
面条在幽暗的面斛里舒筋伸长,渐渐下垂,宛如生根,盘曲于跳板,仿佛曳地的裙裾——该捧去面埕了。
捧面时,左掌侧立,大拇指竖起,与食指成直角。右手逐一拈起四根面箸的一头,依次摆于左掌虎口。右掌托起面箸的另一头,双手将粉条捧出面斛,此时的粉条婀娜着,引领面匠疾步走向面架。
面架摆于面埕,为两根扁柱,顶着一根横楣。横楣下有三根扁平横杆。扁柱、横楣、横杆均有两排可插面箸的圆孔。上面四根面箸插于横楣。下面四根则嵌于两手指缝间。随即展开拉面的一系列动作。
第一个动作:破面。双手稍稍向下抻一抻,向后退一步,两步,退到第三步时,猛地向下一抻,犹如饿虎扑食,紧张而又用力;向前三步,向后退三步,猛抻一下,响起“噗”的一声;向前三步,向后退三步,猛抻一下,又是“噗”的一声。破完面,手里面箸也插上面架。
第二个动作:回面。动作与破面相似,只是力度没那么大,但富有节奏,极具美感,既有形体之美、阴柔之美、速度之美,更有力量之美。回面像蚕在吐丝——细如针线,长达两丈多。此时的面条比五线谱更灵动,还有夸张的弧度,浓郁的麦香。面匠是舞者,也是歌手。舞台是大地,镭射是日头。拉面舞也许脱胎于此。
第三个动作:开面。拿两根面箸,开开合合,将依偎在一起的面条轻轻拨开,若即若离。
第四个动作:胀面。拔出一端面箸,轻轻拉直面条,面箸由上而下分别插入横楣和横杆,使面条处于平行状态,再拿一根面箸从中间压下,并插入横杆,固定片刻,增强线面筋道。
第五个动作:剪面。由下而上依次拔出面箸。向前跨几步,让面条舒缓下垂。将上面的面箸插在后面,将下面的面箸插在前面。如此一来,线面中间自然形成铰刀状,聚拢在一起。差不多干了,拔出面箸,揽于前臂,轻轻盘入公式。面箸整齐地叠着,成田字状,外圆内方,方方圆圆,颇具哲学与美学意味。叠满一公式,盖上麻袋,保持湿度。收完整埕线面后,抬回厝内,剔去面头。分成一束束。每束掐成七八截。一截截绾起,两头朝里,交叉着绾成“8”形,即成一只线面。每只重约四市两。叠入面,洁白,整齐,精美,犹如饰品。
以上是做面邻居留给我的美好记忆。可惜,那些面架早已灰飞烟灭。
分 谷
天色黑透,牛踱回栏里,吃些草料,悠然躺下,闭目养神,缓缓反刍,津津有味,快活如神仙。
而人呢,仍有忙不完的事。身上的汗水来不及擦,脚上的泥土也来不及洗,草草扒拉一碗饭,赶去分谷。
原以为大家忙碌一天,到分谷的时候,会开心些。
会计根据当天进仓稻谷的数量,埋头在隐约的灯光下,“咔嗒咔嗒”,拨拉算盘,计算每个人口的份额。当然不是简单的按人口平均,而是先根据年龄划分成数,再算出各家各户可预分的稻谷。所谓成数,就是16岁以上的社员为十成,也叫吃全成;13-16岁的为八成,也叫吃八成;13岁以下的为六成,也叫吃六成。生产队长也好,会计也好,仓管员也罢,没有谁真正懂得算术,而他们却把运算法则运用到了极致。会计在无比熟练的拨拉算盘的动作中,在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响声中,迅速得出精确的数字。这是穷困所逼的结果。这是他们反复盘算的结果。这是他们无数次面红耳赤争执的结果。与其说是计算、是算术,倒不如说是算计、是心术!若有乡土数学家之类的称号,工于计算的会计是受之无愧的。
我们生产队人多田少,亩产又低,收成又要预留五保粮、军属粮、种子粮、征购粮、回销粮……名目繁多,七除八扣,可分的稻谷所剩无几。即便是好年景,也不过分得100斤田头谷——未曝,也未簸,尚有不少草屑、秕谷和稗子的那种毛谷。所以有的人去分谷,只提一个筥或一条麻袋,不带扁担。
算毕,做阄,拈阄。
在计算与拈阄的间歇,社员们无所事事,有的相互调侃,相互取乐;有的挥舞艾草火把,走来走去,明明灭灭,烟味弥漫;有的满脸不快,大发牢骚;有的沉默无语,枯坐静候;有的则拤着腰,用最恶毒、最粗鲁的土话,无端谩骂,不指桑,不道槐,泛泛地,谁都骂,谁也都不骂。谁都挨骂,谁都愤怒,谁也都不好爆发。
阄是邮票般的小纸片,由会计写上阿拉伯数字,揉成黄豆般的纸粒,或放入竹筒,或撒在八仙桌上。反正要置于三人五眼的虎视之下。即使能避眼,也难以做码。
临近拈阄之际,会计扯开嗓门,征求社员意见,确定几号搅谷,几号铲谷。所谓搅谷,就是用锄头搅拌如山的谷堆,使干与湿,饱与瘪,这个品种与那个品种混合均匀。所谓铲谷,就是分装稻谷,以备过秤。这么简单的事情,往往也要经过几轮激烈的争执,方可尘埃落定。
拈阄不分先后,谁要先拈都行,或举箸从竹筒里搛出一粒,或伸手从桌面上拣一粒。有的仿佛在下赌注,异常谨慎,举棋不定,挑挑拣拣,选中一粒,慢慢摊开,凑近光线端详,若非搅谷、铲谷的阄,便笑逐颜开,否则就满脸乌云。人间的公平,只有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犹如夏日的阵雨,往往只淋湿小路一边,另一边好像跟它不共戴天,一滴也不下——那边的庄稼也渴望雨呀。拈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最原始,也最公道。可是,也会发生同一人接连几晚都拈到搅谷或铲谷阄的怪事。阄是自己拈的,还能怪谁?但很少有人自认倒霉,大多一边忙乎,一边牢骚。
搅谷、铲谷是吃力不讨好的苦活。仓库低矮,窗户狭小,空气不能对流,本来就闷热,加上稻谷散发的热量,整个房间简直成了蒸气房。进去的人每隔一会儿,就要溜出来,透透气。无论是谁,搅好一堆谷,铲完一堆谷,都会一身大汗。说不定还得挨骂呢。那么大堆的稻谷,谁能保证搅得绝对均匀?那么多次的铲谷,谁能保证哪一吊不会多几片草屑?
称谷大多由保管员负责,称一吊,合计一吊,连称几十吊,总数报给会计,居然斤两不差。保管员算个奇人。
“人心不公,人心都公。”父亲的额头从小就錾着两个闪光的字:诚实。村里村外,无人不晓。1973年一个夏夜,有个老头居然妄说我的父亲捻阄时做码。多少年、多少事逆来顺受的父亲,不知哪来的勇气,第一次用犀利的语言,捍卫自己的尊严,并且引来平时畏惧这个老头的社员们浪涛般的声援。
节外生枝的事情,像混乱的风蚊,从来没有止息过。
分几斤谷,却要熬到半夜,根本没有效率可言。
社员陆续散去,而队长、会计、出纳、仓管员则留下,准备吃点心。大多煮粉干或熻肉饭。偶尔也有较高级的,比如搅番薯粉或煮白糊。也不是每晚都吃,隔三差五吃一次。看似吃公家的,其实都是吃社员的,只能像老鼠一样偷偷摸摸地吃。他们当中也会有人去扯一下临走的搅谷或铲谷社员的衣襟。被扯到的心领神会,默不作声,留下。
说来脸红,在父亲当生产队长的那些日子里,遇到分谷的夜晚,我躺在床上,也会奢想那些点心,乃至舌底鸣泉。迟迟没有等来,昏昏欲睡,不时拧一拧大腿,强打精神,但十等九空,好像只吃到一次——半碗的肉饭!
“鸭母蛋再密也有缝。”不管多保密,偷吃点心,总会走漏风声,少不了挨骂。“饿狗扑屎”、“吃爆肚”、“蚀骨虫”、“祭尾顿”,诸如此类的恶语,利刃般乱飞。吃得再多,也是没补的。
好在不日即可到口的米饭会冲淡此前发生的一切不悦。
(节选自散文集《日落日出》,陈家恬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