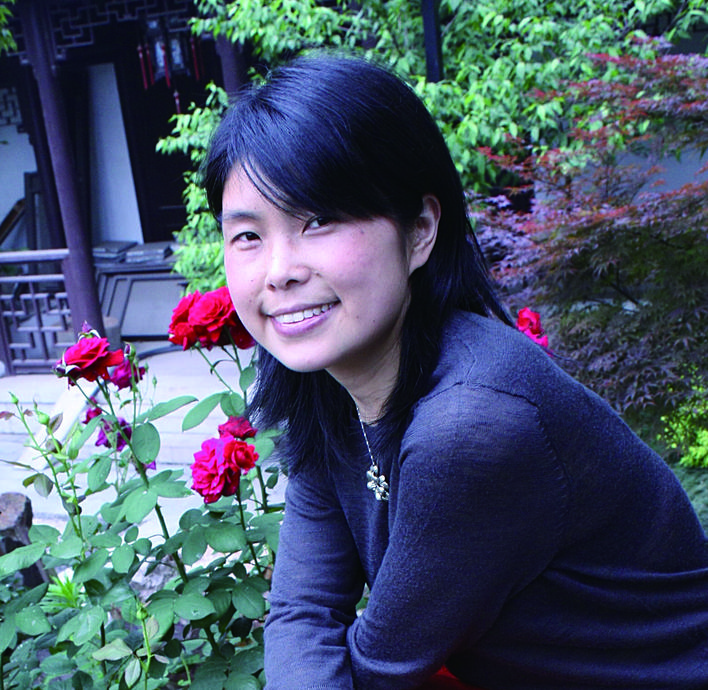鲁敏的作品,并不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取胜。她的文字细腻、精致,恰如一块针法讲究、色彩清雅的苏绣。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这位江苏女作家历时3年潜心完成的长篇小说《六人晚餐》。作品讲述了两个单亲家庭六位主人公的艰难与分合,以及他们在这个“唯成功论”年代中的困境与突破。故事所蕴含的社会问题和大众情绪,使得不少读者“心有戚戚焉”。
6月29日,在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江苏省作协、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人民文学杂志社为《六人晚餐》举办的研讨会上,评论家们提及最多的是小说精益求精的语言、别出心裁的结构,以及对人性的细微洞察。谈到自己的新作,鲁敏说,这是一份献给爱和残缺的“晚餐”,为社会上所谓“失败的大多数”而写,“这是文学应该到达的角落,也是我致力到达的地方”。
记者:您大概是一个“梵高迷”。6年前为了他的一幅《邮递员罗林》,您写了一部短篇小说《致邮差的情书》,主人公罗林在您的笔下化作一位生活在当下中国的邮递员。而您的新作《六人晚餐》,据说也是从一幅梵高画作——《吃土豆的人》中得来的灵感。一幅百年前的画作,以及一部反映当下人们生存状态的小说,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鲁敏:灵感有时候不讲道理,在某种特殊情境的触动之下也就来了,但静下来细想一下,也不是偶然。这幅梵高画作是家人们在灯下晚餐,色泽黯淡,人物表情拘谨而关切——令我心有呼应。这个场景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在永远地进行和发生着,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场景,却蕴含着无数值得放大和深究的密码与信息,深藏有世事的起伏进程、个体的上升或下沉、聚散离合等。世界上所有的晚餐在要素构成上大同小异,无非是食物与一盏灯、几个人,但每张餐桌上的氛围、前因后果、来路去程、所苦所思却大相径庭。
从这个角度上看,梵高的《吃土豆的人》、冯内古特的《冠军的早餐》或是我的这本《六人晚餐》,都是如此。每一顿餐食都是平常的,也都是意味深长的,一个细节就可透露出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境遇与生存况味。
记者:《六人晚餐》的情节并没有太多戏剧化的冲突,却给人一种饱满、有回味的阅读感受。您曾提到书中那次“十字街爆炸”,源于现实中一场与您擦肩而过的真实爆炸,这次突发事件似乎带给您很多思考,也直接促成了《六人晚餐》创作过程中的大修改。
鲁敏:我这个小说从2009年4月开始写,时断时续,进展缓慢,中间又穿插有孩子升学、到德国讲学、家人患病等,初稿写到14万字,停下来,觉得很不满意。2010年7月,我所居住的南京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化工管道大爆炸,因为离得近,我家也受到影响。回去打扫碎玻璃时,我产生了一个幻觉,好像听到整个城市里的人们都在唰唰唰地挥动笤帚。我强烈地预感到,我的小说里、那个分布有诸多化工大厂的郊区,也会发生一次爆炸,书中六个人的命运将要因此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中断了的小说由此获得转折的力量。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大爆炸从来就不是偶发与孤立的,它是后工业时代的一个衍生物,也可以说是近20年城市快速发展后产业转型期的一个踉跄背影。一直到现在,大爆炸依然从各个工地上轰然响起,从被遗弃的化工区响起,从迷宫般的管道深处响起,伴随着黑红色的瑰丽云烟,许多人在那些瞬间永远失去了他们的晚餐。
记者:这部新作描写了人们面对梦想与命运的无奈和挣扎。这样一个关于“纠结”的主题,有很多人都写过,而您的作品给人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大家说得比较多的一点是书中独特的结构。有人称您的《六人晚餐》的结构像“六扇门”、“六棱镜”、“立体魔方”,以不断跳跃、闪回的时间轴,用六位主人公的视角描画出底层生活的“浮世绘”。您是怎样酝酿这样一个有创意的叙事结构的?
鲁敏:说来这个酝酿过程真是一个“自我折腾、自找麻烦”的过程。原稿在写到五分之三时,都还是传统的全知全能视角、并且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一路写下来。但回头审视时,突然感到一种厌倦与不满意。小说中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孤独、隔阂而又充满热烈的幻想,我的视角不该全知全能,那样太简单也太冷淡了。我必须全心全意地化身为书中的人物,从他(她)的身影里出发,成为一个局限的、被蒙蔽的人,我们要一起在暴雨中淋个透。由此,我决心推翻、打乱重来,以表面上的第三人称、从每一个人物的个体视角分为六个篇章,不同的事件、情节、因果由不同的叙述主体去承担推进与展开的任务。
同时,在六人视角外,我还随时加入画外音,一个即兴展开议论与感慨的叙述者之声——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写作特点,以前在中短篇里就有多次尝试,这次继续毫无保留地加以放大。我一直认为,写作手法永无定式,需要各种现代性的打破与加入,需要强烈风格化的尝试与发挥。
此外,这个六人视角恰好还解决了小说里的时间轴问题。《六人晚餐》前后跨度近20年,简单的顺序或倒序都不足为奇,也是对难度的放弃。而通过六个人物的视角就可打乱这种固有的模式,叙事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进行跳出、闪回、插入、展望与回忆,形成一种自由而曲折的命运感——当然,这个在写作中是相当困难的,我前后六稿,有一半的工夫就是在时间轴与人物视角上折腾、取舍和覆盖。
说到底,技术上的舍易求难不仅是对自己能力的挑战,其实也是对长篇这一体裁应有的敬重。很高兴我的这次尝试得到了肯定。我相信,更多的读者会在《六人晚餐》的阅读中感受到一种智力上的愉悦。
记者:中短篇小说一直是您的强项,这次的《六人晚餐》,也有评论家认为从书名到故事含量都有中篇的味道,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鲁敏:哈哈,我早预料到会有这样的观点!我其实也懂得“周全”、“稳妥”的长篇策略,包括出版社多次建议过,换上一个“鸿篇巨制”的名字什么的。但是,什么书名更“像”长篇?《爱玛》《高老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庄重的“人名”就像?而《一个人的好天气》《周末》《罗杰教授的版本》《三个六月》这些就不大像?再说到故事,《邮差总按两遍门铃》《我的米海尔》是否也会因为不够复杂而更“像”一个中篇?一个作品是平庸还是优秀,跟这些并无关系。
在我们的长篇样本里,跨度巨大、人物众多、故事复杂的优秀作品,其存量已经足够丰富,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即使从生态种类讲,我也情愿“不走寻常路”,为其增添一些现代性的品种。小说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却也是不断爆发新鲜力量的艺术。我希望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力量,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小小追求,能做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个问题,但我要求自己这样。
同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对小说的理解与理想,并在寻找着最适合自己的路径与样式。沙雕很大,微雕很小,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美,从来就没有轻重好坏之分。归根结底,还是要独立地看作品本身。总之,我不意外《六人晚餐》所带来的审美意外。我想我们的小说需要更多这样的意外。
记者:您曾说自己是从期刊成长起来的一代“70后”作家,对文学的感受很复杂。“70后”作家在您看来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您认为这一代作家在成长道路上面临的主要问题或挑战是什么?
鲁敏:关于“70后”的话题已经被谈得足够多,表面上看好像有点儿不幸:写作履历平淡,才华不得张扬,既不如上一辈享受过文学大热的荣光,也不如后来者火速赢得市场碰头彩,像是身处冷水域与暖水域的交汇处——此处,营养最为丰富,命运也最为叵测,搞不好会在中途沮丧至死,或许会顺流而下远离航道。但我坚信,优秀者正可以将势就势、回到文学深处,真正做得好了,一定会是强健有力的。
关于这一代的问题,肯定有,可能问题还不少。但这一点不可怕,因为每一代、每一个个体都会面临着各自的局限性,但艺术尤其是文学就是一个不断与弱点、困境和局限作斗争的过程,重点在于,我们在写作中有没有明确的自觉意识,有没有逆流而上的能力和勇气。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70后”作家的个人记忆和前辈相比呈“碎片化”,格局偏小,鼓励他们“往大气象走”,多多着眼于大的时代场景。也有评论家表示“个人经验中同样包括公共经验,时代与历史就在每个人意识深处”,不用刻意靠近“大历史”。您个人认为小说应如何面对时代和人心?
鲁敏: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私人记忆与大格局大历史,这是理论界的重要命题。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真说不出什么的。
从我的阅读体验来看,小说最终所呈现的,都是取之于时间大河的“小我”及其周遭环境的样本,即人物与环境。《红楼梦》《西厢记》《呼啸山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追风筝的人》,在当时当地,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体验,讲述相关一些人的关系、进程与命运。可以想见,在同一时代,还会有各种其他的样本,通过千百年的阅读与传播,不断地淘洗、沉淀,有的作品很快消失了,有的最终留下来,成为文学中“这一个”,具有了“时代和人心”。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也有一些“公共代表性”、“历史时代感”极强的作品,在当时名声大振,时过境迁却又不足为道,这样的例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很多——能否代表“时代与人心”,似乎不是立刻就有结果的事。时间会是最好的试金石。
总之,目前就我来说,就是在写作阶段尽我所能,努力提供“人物与环境”的样本,把我在世界的位置、我与世界的关系、我对世界的思考呈现出来。
记者:《六人晚餐》是您潜心创作3年的作品,那么下一步有什么创作计划?
鲁敏:左三年,右三年。嘿嘿,又要等一阵了,目前还处在调整与酝酿阶段。可以确定的是下一个长篇还是当下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