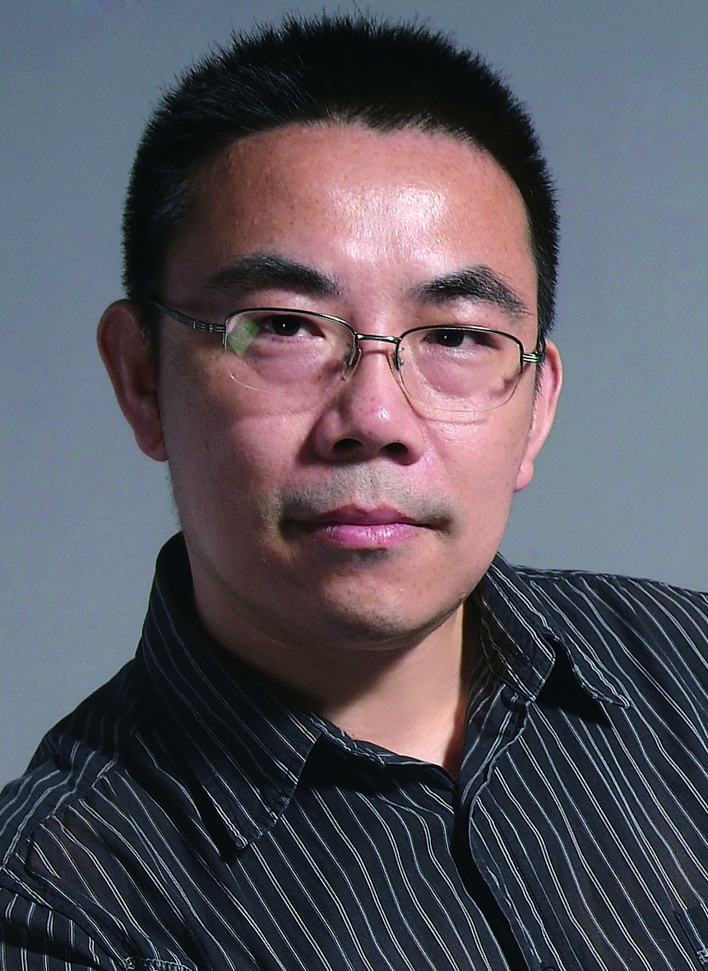言说。我写作,本质上是有话要说,有话想说。我希望我的写作是对自我的梳理和记忆,是我对我自己、对世界和人类的真切表达。我希望我写下命运和感悟、深思和追问,我希望我写下我的幸运和痛苦、爱与哀愁,写下天使的部分也写下魔鬼的部分。我希望,我写下我对人生的理解、世界的理解、命运和时间的理解,它,能说给那些懂得聆听的耳朵。如同普鲁斯特所说的那样,“假如天假以年,我会给我的作品打上时间的印迹”。
智慧之书。我迷恋它——智慧,我愿意把它放置于我写作的核心。即使在故事中,我也希望我的态度是沉思、挖掘和反问,运用属于文学的魔法使问题成为问题。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以前那些作品的回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以前全部小说的经验——我深以为然,并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汇入到复杂性和持续性中,能够做出自己的提供。剧作家奥尼尔有过一句片面但深刻的话,他说,不和上帝发生关系的戏剧是无趣的戏剧——它当然有着显见的片面,但对我来说,却有着特殊的心领神会。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和上帝发生些关系,如果他因此发笑……
野心。我从不讳言自己的野心,我承认,我就是博尔赫斯笔下那个野心勃勃的“创造者”,希望用毕生的精力绘制那张“按照真实比例”完成的世界地图。它足够巨大,巨大到足以吞噬掉我自己。我说过,我好像一直在令狐冲和岳不群之间挣扎,而岳不群的成分更大一些——正是这份野心,让我在日常中或多或少甘于某种的自虐,正是这份野心,让我敢于在没有灯盏的路上一意孤行,不计利益钝害,让我不被汹涌的洪流轻易裹胁……几乎是每年,至少有半年的时间我又会陷入到对自己的深深怀疑之中,怀疑自己的想法、能力、才气,怀疑自己所做的有效——“他笨拙地努力了一生,写下一些无趣的、毫无创见的文字。他,是一个呆板的好人”,“你李浩一直以为自己是野兽,其实,你早已是家畜了”,“我……”种种的怀疑自然会加重我的自虐,它能够轻易从底部毁掉我建立于沙砾上的城堡。在某些早晨,某些黄昏,我,不得不用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对破碎的修补,其中的痛与苦,不足与外人道也。
创造。这也是我一直迷恋的词,正如我迷恋幻想和梦,迷恋无中生有,迷恋突然的溢出和灵光一现。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创造”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世界,一个自我的世界,一个具有玄思和彼岸感的世界,一个与我们的世界平行、处在疑虑中、并不幻美和许诺的世界……在这里,我可以略有骄傲地宣称,我的确拥有无中生有的手指,我懂得某些魔法和技艺。在这个“非我创造”的世界里,我是那么笨拙、愚蠢、怯懦和无能,而在那个属于我创造的世界里,某些状态或者能得以改善,我觉得。
无限,少数。两个词,不过它们的联系过于紧密,所以我将它们放在一起。少数,是一个问题,它要求一个人的写作从一条惯常的、习见的、“正确的”、属于时代流行思想的大路上岔开去,“一意孤行”,将自己放置在一种恒定的幽暗之中;所谓少数,它并非是有意选择,只是甘于接受这一“必然后果”,它要求写作者遵从内心,遵从艺术,勇于探险,而不是曲媚,无论是对大众、权贵、利益,还是对文学史,甚至另一个“自我”,都得抱有些警惕。写给无限的少数,是一位我忘记了名字的作家的话,这句话,已被我重复多次、无数次,都像是我自己说的了。是的,在中国,做普及工作的作家一向不少,不缺我一个,我还是将自己放在少数中,放在一个更恰应的位置上吧。
先锋。先锋不是旗帜也不是姿态,至少,它不应是旗帜和姿态,而是骨血,在我看来是文学最本质的诉求。先锋,最重要的是意识,是前行和探险,而不仅仅是某种的技术标识,虽然技术标识一向重要,不容轻视。继续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话,他说,“发现是小说(或一切文学艺术)惟一的道德”,没有独特发现的小说或一切艺术都是无效的、“不道德”的:因为你违背了艺术创造的内在诉求、本质诉求,因为你把它拉入到庸俗平庸的泥沼里。我还听过一句片面深刻的话,他说,所谓文学史,本质上是文学的可能史。我极认同那种对可能的强调。他的意思是,一切优秀的、有所提供的文学都具备先锋性。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在思考上、在对母语的丰富和拓展上、在对自我的认知和对抗上提供新的可能。
其实还有一些词。譬如说问题、怀疑,譬如说古老的敌意,譬如说思想、人类、价值、艺术感,“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毒蛇和毛毛虫公平生活的宪法”,譬如说“作家是人类的神经末梢”,譬如说……我会借用另外的文字另外阐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