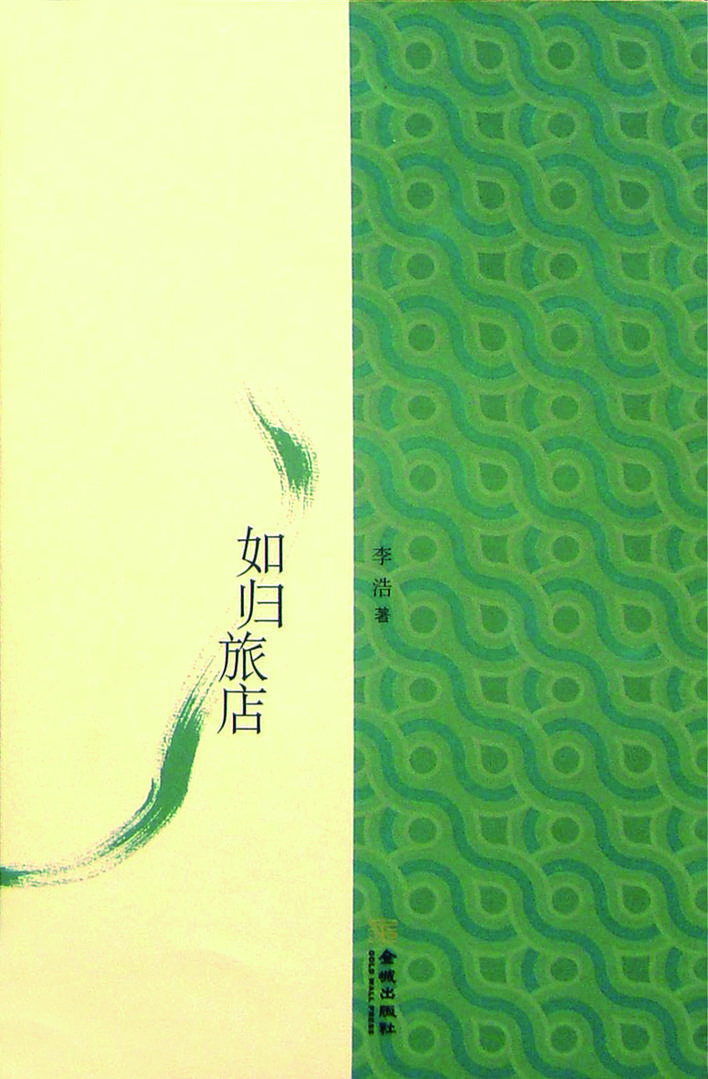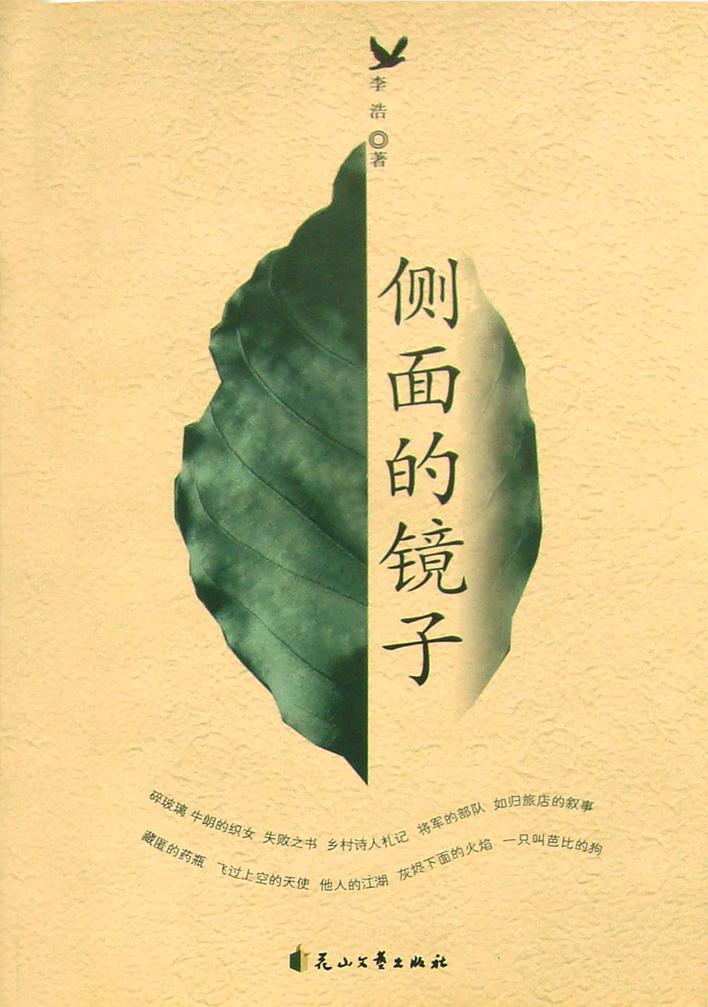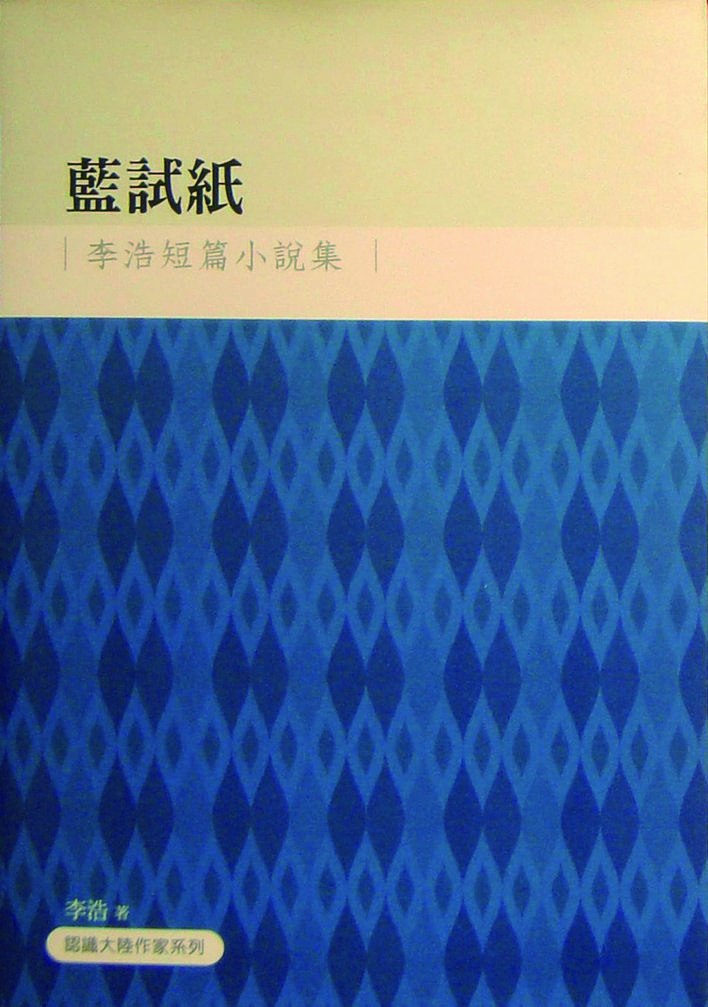李浩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是一个敏感者、观察者和思考者。在严谨理性的写作姿态中,他的创作显示出小说家对于当下生存的知性反思。节制简约的文本意识,呈现出技巧层面的多样性,表现了对于小说整体诗意境界的追求。精准的用词造句和冷峻严酷的文本情境,都将一个有别于日常性写作的作者推到评论者的面前。他的小说带着浓浓的非日常性,却散发着属于一代人独有的精神气息。在沉默低吟的倾诉中,呈现了一个被自我照亮的世界。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是沉默的,因为他们不具备所有可以发言的条件。同时社会文化情境对于所谓的美女写作、欲望化写作的过分关注,在凸现一部分“70后”的精神生存面貌的同时,恰恰忽略了属于更多“70后”的生存经验和精神气质。即便在同代人中间,他们的身份认同也是多元和自相矛盾的。因此,他们的声音无疑是凌乱、琐碎与犹疑的,于是沉默成为一种常态出现在一代人的生存、话语和文本之中。然而,这一代人的确有着他们对当下的复杂经验世界的独特感知,且以一种被压抑的沉痛之音存在,李浩恰恰是在这样一个维度上出场的。
村镇视角与写作视域 “进城”绝对是中国城市化过程的最重要的记忆之一。在转型过程中,写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写出了如何“进城”,但是却没有及时地反观这种转型期独有的精神气质和特征。李浩站在村镇意象的视点上,较为精准地提出了他对于这个时代作为小说家的看法和观点。作为城乡中转之地的村镇与村镇的文化形态(包括县城和县级市)应该是透视中国乡土社会转型时期精神气质的绝佳视点。以村镇(包括县城)为视点的作品不可谓不多,但是大多仅是现代文学以来的乡土文学的继续。然而,在中国乡土文化发生重大转型和断裂的当下,如果继续使用这种叙事,小说创作显然已经和当下与历史的精神气质南辕北辙。
李浩选取了村镇作为观察中国社会的原点,将对于当下与历史的思考融入村镇日常生存的打量与拷问中,同时又因受到西方诸多流派小说的影响,他笔下的乡土社会在少年“我”的眼中是变形的,没有一般意义上乡土社会的人伦法则和熟人社会的纠葛纷争。这个乡土仅仅是“我”眼中的乡土,以至于成为在“我”之外别人甚至都不会认同的乡土。因此,拨开了日常的琐碎的乡土叙事,直观地表达了小说家对中国当代乡土的认知,甚至是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某种认知,因为对于传统中国来说,乡土就是中国。
《如归旅店的故事》不仅仅是用一个旅店的逐渐衰败来隐喻农业文明的式微和近现代中国乡土文化的多灾多难,更难得的是,文本中对于式微文明挽歌式的同情,以及同情中清醒的认知和解构色彩。对于“70后”来说,剥离和梳理传统的过程,就是和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决裂的过程,于是我们在叙述和写作的时候,连同自己一起成为了迷惑、怅惘和拷问的对象。小说细节的处理、意象的运用,都是有意为之,比如门上的铃铛、城边的乌鸦、旅店床铺……父亲小农的理想、对于乡土农业文明的自觉遵从和维护,这些渗入到日常生存的一切层面,而成为一家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又是禁锢下一代的根源。
李浩在想象的镜像中告诉阅读者:曾经有过以及可能继续发生的历史场景和当下生存,带着严厉气息,让文学疆土在一支枪和一个旅店中扩展至肉身、心智乃至灵魂。他显示出了现代人对于“自我”的感知和确认,他的写作视域也因此敞开了自身的现代性身份与资源。在对于中国当代乡土社会的生存、人性和命运的现代性叙述中,他的文本突兀地体现出某种和西方现代小说可以媲美的品质。
“多余人”与《乡村诗人札记》
对于“70后”来说,我们大多承认自己是父亲的儿子,但是父亲那儿似乎并没有可以继承的传统。丰富的中国传统知识思想资源在父辈那里彻底断裂了,因此才会有我们对于父辈犹疑的审视目光。这种审视绝不是先锋小说中的嘲讽与背叛,因为对于没有任何思想和行动能力的父辈来说,真的是无可背叛。李浩笔下无能的时常企图自杀的父亲、一辈子无所事事的二叔便是代表。在那个时代,有一点思想和行动能力的人都会被视为怪异和不正常。同时,作为接受过理想主义教育的一代人,传统在这些人心目中依然占领着灵魂最后的一隅。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历史和当下,父辈们很难理直气壮地作出“我是我自己”这一现代性的回答。
在小说集的大部分文本中,“我”都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这个少年所关注的并非是自己青春年少的苦闷,也非对乡土社会丝缕的记忆与回眸,而是非常年代小人物的非日常的行径。小说中,村镇作为背景,少年则是活跃在这个背景上的摄影者。《乡村诗人札记》叙述了一个司空见惯的乡村教师,因为是“我”的父亲,“我”剥离了乡村教师身上所附着的价值伦理和社会文化身份,用儿子的眼光打量家庭中乡村教师的日常生存。20世纪80年代很多部家族史的长篇都会刻意摹写教化乡党的乡村私塾先生,他们是集儒家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的人物。而李浩解构了传统文化与伦理中的乡村教师,顺带也消解了师道对于民间乡土社会的影响。
在父亲这一代人身上,历史的沧桑、现实的感悟、理性的觉醒似乎都停滞了,只剩下对于生活被动的应付,以及为着自己残存的爱好的一丝激动和兴奋。写诗和打麻将成为能够引起父亲兴奋和激动的两件事,偏偏他连自己最喜爱的两件事也做得不伦不类,不成气候。而父辈这一代人非但和古典传统断绝了可能的联系,也和“五四”的启蒙理性隔着千山万水,对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改革与市场经济同样瞠目结舌……惟一让他们身心安宁的是对生活的认真和对家庭的责任。在前辈和后辈眼里,除了善良的无能和幼稚的理想主义,这一辈人对于当下乡土社会文化思想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李浩通过“悯父”的主题,阐释了属于中国社会巨变中的多余人形象,这类乡土经验社会中的多余人,代表了一个时代被动生存和被动生存中灵魂之不死,尽管这种不死以一种可笑的无意义的甚至虚妄的方式存在。在怜悯的回望中,小说家写出了中国式的多余人形象。这种多余人切实地存在于中国转型期的乡土,在无所作为的人生处境中,以无能的可笑的方式延续着某种对于生活可怜的激情与幻想。怜悯的感情是一种让人感动的情怀,尽管我们大多数时候已经不会怜悯。
精神后撤与《失败之书》
《失败之书》叙述了哥哥的失败,哥哥对于绘画的追求可以算是对于艺术理想的追求,而经商则是对于金钱的追求,当二者都无法实践时,他无法接受平庸的人生,彻底陷入一种非常态的生活。哥哥是时代中勇敢而盲目的实践者,他们那种生猛的实践从某种程度上给了这个时代急遽变化加速度的推力,历史在哥哥眼中就是一轮又一轮的向着理想的行动以及行动之后的失败。这个文本从侧面还透露出对于所谓理想的揶揄,在这种揶揄中,可看出李浩一代人建构自己理想的企图。
李浩探讨了对于时代气息异样敏感并将其付诸实践的一代兄长的失败人生,无疑是一种“弑兄”的行为。在对兄长严厉的审视中,小说家表达了这一代人鲁莽前行的草率,这种草率带来的挫折感是如何一步步浸淫到日常生存的精神罅隙里,甚至于在这种罅隙里生根发芽。兄长的挫败感让懵懂真挚的“我”和愚拙朴讷的“父辈”陷入人生焦虑的精神困境。相比较获得世俗成功的兄长们,失败的“哥哥”无疑是被时代和历史遗忘的,但是成功兄长们依然没有解决失败的“哥哥”所未能解决的诸多问题:艺术、理想、精神建构……“哥哥”的失败隐喻着一个时代青年触目惊心的精神上的后撤与颓败。
成人世界的消解与《碎玻璃》
《碎玻璃》表层的故事是专制的乡村教师和有个性的学生之间发生的事情,实质上则是通过这样的故事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村镇青少年贫瘠的文化生存和孤独无助的成长环境。这是一个向成人的所谓威严和专制挑衅的文本。但是李浩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他的叙述和前辈的“弑父”有所不同,采取的视角是冰冷而温和的,是犀利而悲悯的。因为一颗洞见生存本质的心灵,李浩对于父母一辈人是宽容的,理解了他们一代人的孤陋寡闻、短见小气,甚至于他们的专制与无知。正是因为同情的理解,他笔下的父母辈人物才会在冰冷的底色中闪现出那一辈人的善良、无用和盲目的理想主义的坚定。那份坚定以及坚定中的从容恰恰是李浩这辈人所匮乏的,这一代人可以算做是坚定的怀疑论者。
《碎玻璃》整篇都是少年视角,但是它的隐喻则毫不含糊地指向成人世界。小说描写了“我”对于生活真相的质疑,从碎玻璃的隐喻中,小说家从少年记忆中走向了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学校教育的反思。对于成人世界现代知性水平的拷问,在某种程度上凸现了李浩对于当下成人世界心智认知水准的考量。
“死亡”主题与《邮差》
《邮差》显示出李浩冷静的洞察能力以及写作上的野心。写的是小人物,但是尽量用大手笔去勾勒。在一个没有稳定职业的小人物的眼中,世界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目?《邮差》描写了一个死亡的信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本。多数普通人会被日常生活所淹没,投身世俗同时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世俗。而邮差一开始是厌恶这种常态生活的,文本不厌其烦地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邮差日常的工作,但是邮差尽管身在其中却冷眼旁观,以旁观者的身份介入日常,因此,他和一切的日常就有了一段诗意的距离。邮差实际上有普通人的很多特点:好奇心、同情心、善良以及某种道义上的坚守与责任。但是他的这些特点又比一般人要多上几分,尤其是相对于他卑微的社会身份与地位来说,这些特点在他的身上往往不能作为一种美德或者一种能力的体现,而成为一种令人侧目或者难以理解的行径。由此他才有可能在送信的过程中,面对死亡对于人的逼迫和打压,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包括丢弃信件、延宕、和马面谈判等等。死亡不可逆转,人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邮差在心力交瘁的时候,竟然梦到了马面给自己传递死亡的信息,就在这一刻,小说急转而下,回归了日常,母亲唠唠叨叨的责骂声让邮差结束了关于死亡、诗乃至孤独的一切,还原了生存的真实。生活原本就是在俗世中浑浑噩噩,但是不排除这种日常生存的浑噩中,有着直面死亡和苦难的努力。
《邮差》的主题是古老的,又是我们恰恰在当下容易遗忘的。在物质发达的当下,人类似乎忘记了自己命运的时限性和作为物种的命定性。邮差无疑是当下情境中的惊醒者,带着忧郁和神经质的言行,让沉溺于世俗情境的人们反感而厌恶。因此,在抱怨了李浩的冷酷之后,我还是应该感谢他的《邮差》给当下文坛带来的哲思气息。
谈李浩的写作无法不提《将军的部队》,“将军”让文学界认识到李浩作为小说作者的重要性。李浩的小说集中呈现出小说家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揣摩与思考,在对于欲望、男女和世情经验的叙事中,他的写作却在对历史的文学性把握中走向小说本身。独特的少年视角下却蕴藏着宽阔的写作视域,努力而执著地把握一代人精神气质和内心世界的隐痛。在传统与现代两端,他苦恼于自身的现代性身份确认,于是在对父辈悲悯而犀利的解读中,写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土中国的多余人。他为一代无所作为的父辈立下了一个天真而无能的影像,隐喻了一个时代被动生存和被动生存中灵魂之不死,且假定了这种灵魂心性之不死对于“我”的意义。投身当下的社会情境,李浩在“弑兄”的主题中,表达了对于兄长们生猛前行的犹疑与担心,由此也确证了“我”一代人冷眼旁观的身份定位。李浩对于成人世界的知性水准和群体性生存的个人性考察等,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认知。他在属于“我”这一代人温和的视角中,打量着尚未成长起来的中国人的现代知性、教育、文化、自尊乃至无法向死而生的懦弱和自卑。李浩对于当下写作的意义在于让小说走入文学性的难度和高度,同时又蕴含着属于一代人沉痛之音的现代性思考。李浩自身的局限和困窘也无可避免地一一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