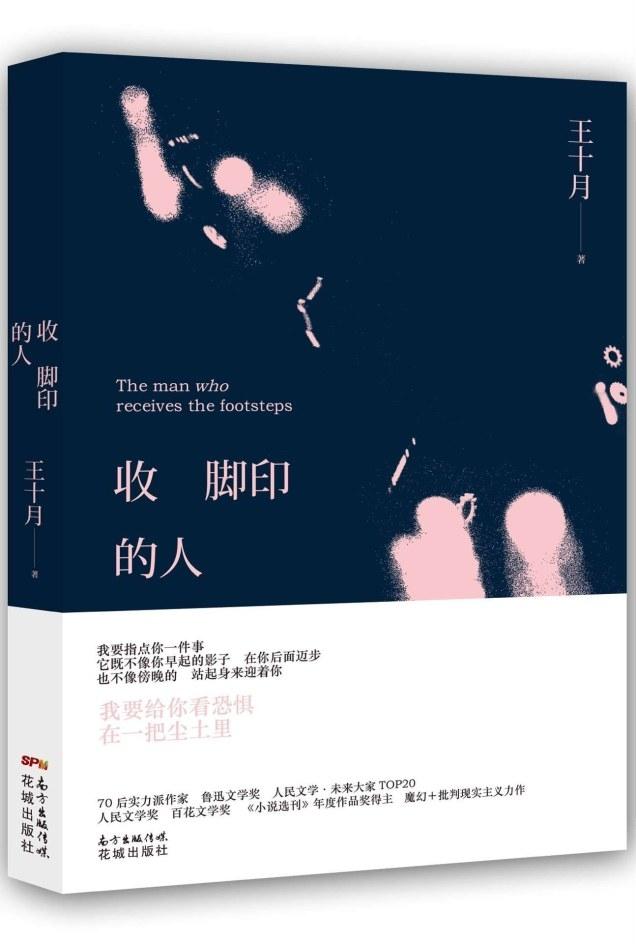《收脚印的人》以一种现代现实主义叙事的手法,铿锵而笃实地书写了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那段隐痛的时光和经验,树起了一面精神之镜。他的思考和陈述直刺那些被我们不敢正视、咫尺天涯的道德问题,喷薄出对人性底层的深切关怀。他“以一部薄薄的小书为自己作祭”,也是用一个作家的勇气为那莽撞的时代作祭。
王十月是从底层脱颖而出的当代优秀作家。他的生活经历注定了他的书写,必是扎根中国这片肥沃的现实土壤之上,必是带着亲身体悟之后的苦痛感。这种苦痛被时光抽丝剥茧般消磨,被庞大的打工人群所默然忍受或主动遗弃,林林总总的际遇,或好或坏,或痛或伤,终是倒映成时代巨轮驶远后遗落的一幕剪影。但也有人会永生铭记,王十月是铭记者之一,他带着省思、自讽、悲伤、忏悔,再度与那些曾被侮辱和损害的人相遇,把经历过的一帧帧光影铭记。
“女士们、先生们”,这个多么充满庄严仪式感的开场白,置首《收脚印的人》的每一章节,把我们带入“王端午”的叙述场域。我特别明显地感觉到,仿佛王十月就坐在我对面,坐在我看不见的房间的某个角落,神情凝重或低落懊丧地讲述一段真实的社会与个人记忆。这记忆的起点是一个人临死前去“收脚印”,去勘察自己的来路,这虽是个民间说法,但具有了魔幻般的色彩,可以构成极富想象力和冲击力的文学手段,这也是王十月在这个新长篇中所赋予的新鲜血液。
“收脚印”这个充满魔幻色彩的元素,无疑将现实映照得更加惊心动魄。一个人一生要走多远的路,你我无法确知。道路像叶片上的筋脉,分岔、延伸,直至消失。脚印里写满时间,也写满生命中不安的悸动,那些欢悦、悲伤、彷徨、坚定、轻盈、沉重,摇身一变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主人公王端午向那些“脚印”靠近,他小心翼翼地把“脚印”拾起,放在手心,握紧拳头。他从“脚印”中看到卑微的过往,看到人性中的怯弱、复杂、黑暗、残暴。在王十月收集的错综复杂重重叠叠的“脚印”背后,一个叫“收容遣送”的词浮出来。上世纪90年代心怀美好生活梦想而外出闯荡的人们,谁也不会对它陌生。王十月也是被侮辱过的千万人群中的一员,身为作家,他必须为这段历史进行一次书写。于是,我们得以紧随一个亲历者与观察家的腾挪身影,进入他为我们作出筛选的记忆之城,那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过往,令与这一时代有过亲密接触的麻木窥者扪心自问,胆战心惊。
那一角镜头所映射的是南方城市打工者都不愿回望、撕裂破碎的境遇,更是把似曾相识的一切尽收眼底,把人的卑劣之心、生存之艰、角斗之魂利刃刮骨般地剖解。在王十月笔下的人物身上,可以窥探查获“人类的每一个标本”,可以勾连唤醒我们最痛的记忆。痛以类聚,他在长久的思考之后积聚藏于现实的强大力量,勇敢陈列出被遮蔽的疼痛与尊严,为一代人的苦难史作出血证。
下面我们再来研究这份“证词”。时间是上世纪90年代,地点是南方,东莞的樟木头镇,一个看似虚指的实地。在“证词”中出现的主要人物有作家王端午(知识分子)、区公安局长黄德基(官员、权力掌控者)、企业家李中标(财富创造与支配者)、打工仔马有贵(身处底层的可悲者)。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轨迹,但一段共同的际遇,将他们的生命绞锁在一起。这一际遇的关键点落在与一个叫北川的女孩的短暂相遇里,他们犯了罪,他们的过错导致了北川的死亡,虽然他们都侥幸逃脱了。逃脱了的罪如何惩罚?王十月进行了精心而巧妙的设计,作家认识到罪行后开始救赎之举,企业家认识罪后以慈善之行表达忏悔之心但逃避救赎,官员拒绝并阻止忏悔与救赎,身处底层的打工者浑浑噩噩意识不到罪。这些各异的姿态,使得故事性与可阐释性充分打开。很明晰地就能看到,《收脚印的人》一书主题依旧是多少年来横亘在人类面前的永恒考题——罪赎。强者勇敢站出来忏悔与救赎,弱者茫然逃避,狡者欲盖弥彰逃之夭夭。
如果真有上帝,他定是宽恕的,但逃脱者如何面对自己,又如何攒取自省的勇气?尤其是曾在底层苦苦挣扎得以脱身的人们,所需点滴勇气又何其巨大;那些被雾霾之毒从生活的呼吸道奔袭噬咬的人们,何以驱散侵蚀心灵的恶霾。王十月在小说中原文引述了一篇自己写过的随笔:“没有身处底层,如何真切体会到这种切肤之痛,这种痛后带给人的麻木?有‘层’的存在,就有隔膜存在。每个层与层之间,隔着的正是一道道的南头关。有形的南头关并不难拆除,然而无形的南头关,在可以想见的将来,还将横亘在人们的心中。”“南头关”貌似不复存在,但对人的道德和行为的永恒拷问不会消失,那些蒙昧心灵的恶霾还未散离。四处寻觅,现实的铜墙铁壁阻隔了风的来袭,一人之力虽弱,即使如西西弗斯般受伤,但每个人不能自我毁灭推动的勇气。每一时代都需要有王十月这样的勇敢者,回望与审视,然后站出来真诚袒露,向他者更是向自我,践行一次如王端午般不悔的自我救赎,哪怕现实中会遭遇诸多的挫折、打击和失败。
雾霾终将让位于碧空丽日。王十月和他的《收脚印的人》以一种现代现实主义叙事的手法,铿锵而笃实地书写了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那段隐痛的时光和经验,树起了一面精神之镜。他的思考和陈述直刺那些被我们不敢正视、咫尺天涯的道德问题,喷薄出对人性底层的深切关怀。他“以一部薄薄的小书为自己作祭”,也是用一个作家的勇气为那莽撞的时代作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