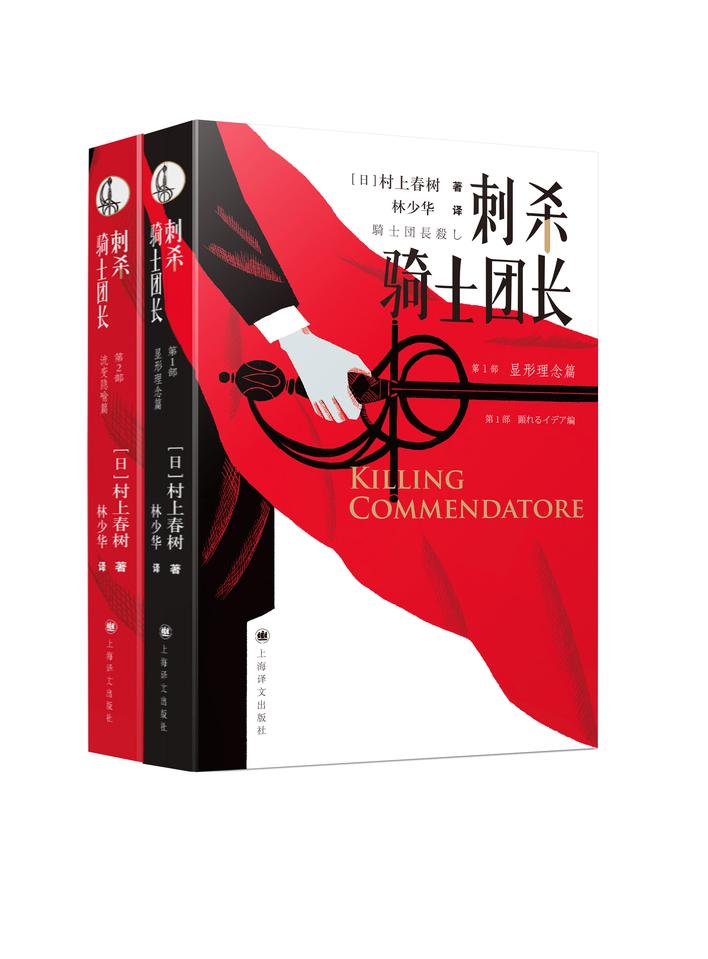第一次听说村上春树的名字,我还在中文系读书,大约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内正流行读米兰·昆德拉,他的媚俗之说,好像引起了诸多严肃作家和诗人的讨论,俨然成了重要的文化现象。当时我听一个老师说除了米兰·昆德拉,还有一位后现代作家村上春树,也可能会在中国流行,便对这名字留了点儿心。后来在海淀图书城,看到一本封面类似低俗小说的《挪威的森林》,注意到作者的名字是村上,买回来看了一眼,觉得也就那样。不久,又看到一本《跳跳跳》(也就是后来的《舞舞舞》),观感为之一变。
此前,国内能看到的带有魔幻色彩又试图展现当代历史深度的外国小说不多,我印象里写得好又好读的就两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差不多都被我翻烂了。所以读到《跳跳跳》,自然有些兴奋,主要是它的魔幻还带有东亚神秘主义的色彩和节奏,同时又有一张西化或现代的壳,对我这种看着西游、封神、聊斋以及类似《白蛇传》这一类民间故事长大、又接受了大量西方现代知识的人来说,尤其亲切。这之后只要村上出新作,我都会找来看一看,其中尤其出色的《舞舞舞》《奇鸟行状录》和《海边的卡夫卡》可能还不止一遍。读村上因此成了一种习惯,跟好不好已关系不大,就像你老去一家饭店吃饭,那里要添了个新菜,你就忍不住要跑去尝一尝,然后品评一番。
这个过程中,我还有个比较有趣的经验,就是阅读心态上的变化。刚开始读村上的时候,好像他还是被当作严肃作家来看待的,所以跟人说起正在看村上时,会比较理直气壮。后来连看言情小说的人都开始读村上,甚至谈论村上了,再跟人说在看村上,就难免羞涩,尤其对我这种认为自己也在写点所谓严肃小说的人来说,真的很难说出口啊。日常的身份政治,在阅读经验里有极为常见的运作,我们通过告诉别人自己在读、听和看什么,宣告自己的身份归属,以生成某种潜规则式的身份同盟。所以流行或者不流行在身份政治的世界里,都是危险的事,都意味着将被另一种身份所拒绝。
说起村上的流行,很多人会归因于他的时尚感和言情元素,但在我看来,村上最强大的技术其实是对悬念的娴熟运用,这让他小说里相对晦涩的当代隐喻有了强有力的支撑,以悬念的欲罢不能,威逼利诱他的读者深入到对政治、历史和文化的隐喻之中。好像村上自己也不止一次承认,美国硬汉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是他最爱的小说作者之一,感觉村上的悬念技术,应该跟他这部分的阅读经验有关。但在《刺杀骑士团长》这部新作里,他似乎在有意淡化小说的悬念色彩,虽然小说的内容本身足具悬念,但不像村上以前的长篇那样,把吊人胃口的点计算得如此精确。在减弱悬念的同时,他又将絮叨的思辨加强了,这一倾向好像在《1Q84》里就已有所呈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多年陪跑诺贝尔奖,让村上下意识地想把自己打扮得更严肃一些。当然这事情无法坐实,写作中作者下笔处某些不经意的变化,极微妙而隐私,可能作者自己都未必意识到,这是阅读中偷窥之乐的一部分,只能猜,不能证。
《刺杀骑士团长》有点像费里尼拍《八又二分之一》,小说中很多意象和叙述都是村上以前长篇里意象的重现或化用,如一开始与妻子莫名其妙的分手,几乎是《奇鸟行状录》的再现,尤其那个莫名其妙让人顿悟的地洞,不就是《奇鸟行状录》里的那口井吗?然后作为意念显现的骑士团长,难道不是《海边的卡夫卡》里那位山德士上校的再现吗?还有那位灵气、神秘却能和主人公无话不说的秋川麻里惠,是不是《1Q84》里的深绘里的另一个分身呢?人妻女友这个情节,难道不也是《1Q84》里已经出现过的吗?还有免色和《舞舞舞》里同样喜欢开高级跑车的五反田也是否有着某种对应关系?
村上为什么要这样露骨地重复自己的写作?江郎才尽是一种可能,而且还是最大的可能。我们谁都不知道,会在哪个时间点,被某个身体或精神上的疲倦点打败,对某件事情终于失去了热情,却还要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只是不想出局而已。在创作上,这样的情况不是最可能发生的吗?也许村上早就如此了,只是靠着勤奋在维持他的写作?为什么这部小说,不会是某个或几个熟悉村上作品的枪手,以村上特有的味道和人物原形代笔的呢?就像村上在他的小说里所反复表现过的,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里,这样的事情不是很平常吗?
说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一向对此腹诽颇多的村上,在这部规模庞大的小说里,似乎也在淡化这个主题,甚至是在有意识地避开小说的社会和历史维度,虽然小说中也曾提到南京大屠杀,或者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入侵之类的事,但就其在小说中所占的比例和力度而言,可能只是推动情节和人物发展的噱头而已,其反思的力度、素材的丰富性,跟《奇鸟行状录》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比,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还有小说基本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小说中人物与外部社会的关系不是被抽离就是被淡化,为数不多的主要人物的共同点,就是都住在同一座临海的零星分布着高端住宅的山上。在长篇小说里,一向以冷淡的态度与热腾腾的世界保持联系的村上,为什么要突然变得如此封闭而个人?
好吧,或者可以换条路径,以最大善意来揣测这种变化的动机,《刺杀骑士团长》是否可能是村上为自己写的一部精神自传:所有以往小说意象的变体再现,都是他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一次探索和袒露。毕竟1949年出生的他,已年近70,应该已经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衰老的脚步了,也许他真的需要对自己的创作生涯作一次必要的总结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很好解释,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为什么是一个画家,难道画家不是一种与小说家很相似的身份吗?里面那位画家的画作有很好的商业价值,这难道不是村上自身的映射吗?还有画室原来的主人,丧失了记忆的雨田具彦,会不会是村上对未来衰朽的想象呢?要知道雨田正是小说的同题画作《刺杀骑士团长》的作者,小说中,在躯体和记忆即将耗尽的时候,雨田以阴魂的方式,回到画室凝视着被藏在阁楼里的《刺杀骑士团长》,这是否和村上写这部小说的行为也有某种相似之处?而且小说的主人公,也在后来把隐藏着自己心结的几幅画作,藏到了雨田隐藏《刺杀骑士团长》的阁楼上,而隐藏的理由,是因为这些画是画家用来解开自己心结的,不适合拿出来示众。阁楼这个文学意象,资深的文学读者非常容易联想到另一个重要的文学意象——阁楼上的疯女人。而且小说中的阁楼上还藏了一只猫头鹰,而猫头鹰可是一个黑格尔式的意象,它是罗马神话里智慧女神密涅瓦的伴侣,按黑格尔的说法,这是“反思”的隐喻,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它是只能在薄暮来临时悄然起飞的。这是否意味着村上在暗示,他以往的小说里,隐藏着太多他个人的心灵秘密,那是他对自己灵魂的疗治,也许这些东西过于疯狂和晦涩,是只适合藏在阁楼里,由反思之神秘密守护的。
小说里,除了阁楼和被藏在阁楼上的画作《刺杀骑士团长》,还有一个重要的意象或者道具,就是那个在树林里发现的地洞。按小说里的解释,这可能是以前的和尚用来闭关禅定的特殊场所。正是来自这个地洞的召唤,才发生了后面的一系列灵异事件。后来,画家自己也是在这个地洞里解脱了心灵上的一系列死结,终于弄明白了自己画作的奥义。
其实这样一种类似闭关禅定的封闭场所几乎是村上所有长篇小说里都会出现的意象,在《舞舞舞》里是海豚旅馆,在《奇鸟形状录》里是那口井,在《海边的卡夫卡》里是森林里的小屋,在《1Q84》里是青豆藏身的那间密闭公寓。从村上的简历来看,好像他父亲是和尚的儿子,无论是否主动或自觉,在客观上,村上应该很难不去接触那些具有东亚神秘主义色彩的修行方式: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只面对自己和自己的想象,通过长时间的静坐,获得某种超验的洞察力和智慧。某种程度上,写作对村上来说,可能也是这样一种类似闭关的经验,好像村上自己也表述过,只要在书桌前连续地坐上几个小时,即使无聊、没有灵感也不放弃,然后小说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还有,在村上关于马拉松的表述里,那种最后身体不复存在的体验,也可能是禅修体验的另一个变种。显然这种宁静致远的东方思维,正是村上小说的独特性所在,虽然其小说在意象上与西方小说相似,但与西方思辨传统的不同之处在于,村上显然比西方同行更加直觉和飘逸。
虽然路径上不尽相同,但村上式的地洞体验和小说里阁楼上那只黑格尔式的猫头鹰在效果上却是一致的,我们最后需要完成的不仅是认识和思想,我们还需要去完成“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那是人真正可以超越自我局限的地方。而我们对村上的阅读以及对这种阅读经验的反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