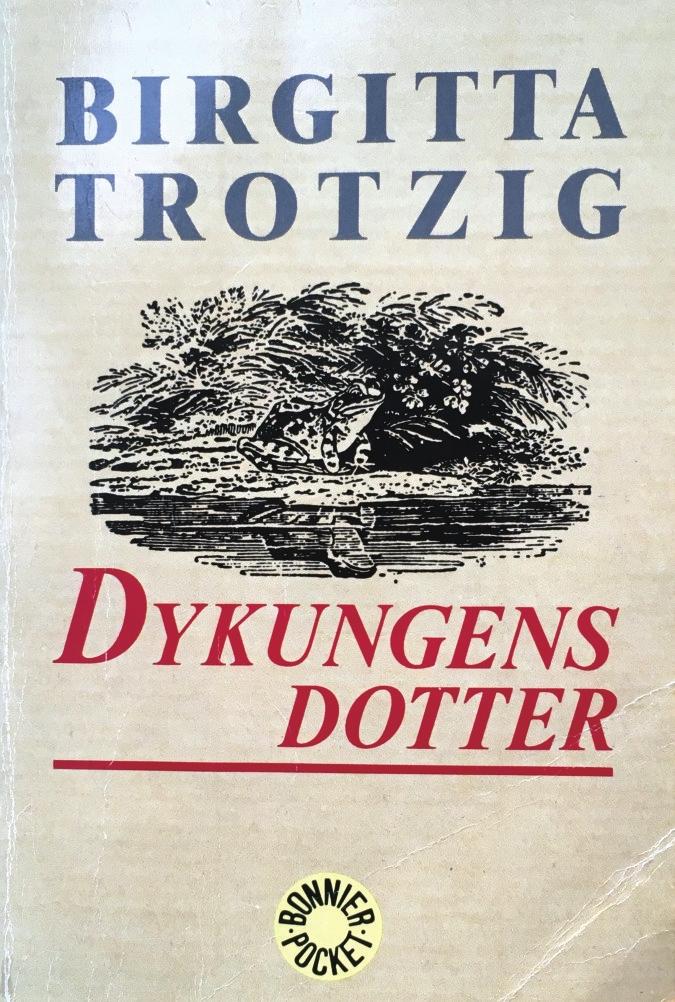对所有登场人物而言,生活好比噩梦。亮光偶尔从罅隙中透入,短暂而微弱。小说不只讲述黑暗命运如何从一个人扩散到一群人;也不只讲述一名乡村女子在1920年代向城市、向现代化和安身之家的迁徙。小说还造出了情境和日子,让苦难居于其中,蕴含了诸多重大人生问题,如裁判、异质、罪恶、谅解,还有爱。
我有一个故事要讲
我有一个故事要讲。一个女人即将跋涉。她来自最边远的乡村,在那里一切都是古怪的笼子。她在去城市的路上。她有她的缘由。
《沼泽王的女儿》这部由瑞典作家比姬塔·特罗泽格(Birgita Trotzig,1929-2011)撰写的瑞典现代文学经典,于1985年问世,书名取自安徒生同名童话。在安徒生童话中,一位公主被拉入沼泽,生下沼泽王的女儿。这女儿被维京人的妻子收养,白日里是美丽而残忍的人,夜晚便成了温顺却丑陋的蛙。
特罗泽格谈到自己如何书写,说是先会有风景、房间和面庞的断片在意识中浮现,其中就包括安徒生的《沼泽王的女儿》。自打儿时读过这个童话,记忆和反射便一直跟随。“这是个故事,关于半人半动物……有堕落和复活……故事描绘了灵魂的变形,我想拿这名字命名我的故事。”她认为,通过童话形式,作家可自由转换于不同层面。有现实主义,但最主要的是,被选择的整体图像借此形式,能成为清晰可见又并不可解的谜,世界变得形而上。确实,采用童话形式往往是为更好地描述真实世界。瑞典作家雍松也曾表示,若要尽可能全面描述一地一人,就要努力拥有足够自由。若作者试图给出全景图,却在现实前变得犹豫不决,便可借童话兜一个圈子,童话是一扇开着的门,它描绘现实社会,更贴近作者的精神体验。
特罗泽格看重安徒生的《沼泽王的女儿》,更因其中有人性和动物性的并存与转换,角色有在不同时空、现实和幻境中的转换。动物和人类说同一种语言,而童话又基于口述。
“没错,从前,一个夏天的早晨,曾有个女子翻过海边的丘陵,跋涉而来。”这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的民间口述之继续,包含历史的回声。述说的是过去将来,读者的时间和故事的时间得以自然连接。而在空间上,小说里的地点虽因文学化而在细节上有偏差,但现实里都还确在,读者的空间和小说的空间基本吻合。读者被自然带入、参与,随叙述者的声音和视线,从“下边”走向“上边”。上下,可指地图的南和北,也可指从乡村到都市。
这女子活在闭塞环境里,那是1920年代瑞典最南部斯科南省东南角的一座渔村。其父是渔民,因一场事故失明。这小地方“一切都是古怪的笼子”,人被生活压垮,连抬眼皮也没空。女子被父母理所当然地当作劳动机器。一天,她遇到个“黑乎乎的吉普赛人一般”的陌生男人,被拖进日常之外的世界,就在沼泽边缘。不久男人失踪,落入克里斯琴城监狱。 这男人就是“沼泽王”。
女子有了身孕,不得不离家到城里去。生了女儿后,女子在书中获得“莫阳”这个名字——其实算不上名字,当地孩子都是用方言这么叫妈妈。莫阳戴假婚戒,入羊毛厂做工,一再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回归正常人群。沼泽王一次次神奇地在夜间突现、扣门——在越狱后、被释放后,而她悄悄接纳。后来,莫阳有了合乎社会规范的性与婚姻,可惜她与丈夫的孩子早夭,丈夫经历抑郁、离家、投身战斗等苦难后死去。
沼泽王的女儿和父亲很像,被城里孩子唤做“吉普赛崽子”,十多岁便在厂里做工,15岁开始出卖身体。生下儿子后没几日便再次和男人鬼混,被母亲剥夺了儿子的抚养权,最后淹死。外孙在养父母那里过得很不痛快,犯了纵火罪;逃出精神病院后,在警察的追捕中遭到枪杀。莫阳在老迈之年,于早春的一天离开城市跋涉于海边,在日出时分看见沼泽王的女儿在沙滩边朝自己走来。从渔村到城市,又回归海边。终其一生,罪责感和谋生之苦压迫着莫阳。她是特罗泽格所谓“在磨盘间的人,那尖叫的谷物”。
对所有登场人物而言,生活好比噩梦。亮光偶尔从罅隙中透入,短暂而微弱。小说不只讲述黑暗命运如何从一个人扩散到一群人;也不只讲述一名乡村女子在1920年代向城市、向现代化和安身之家的迁徙。小说还造出了情境和日子,让苦难居于其中,蕴含了诸多重大人生问题,如裁判、异质、罪恶、谅解,还有爱。
1929年,特罗泽格生于哥德堡。她本姓谢连(Kjellén),父母是拉丁中学的法语和英语老师。1937年,全家移居南方斯科南省的克里斯琴城。她在大学修文学和艺术史,曾给多家报刊撰稿。1949年和画家乌尔夫· 特罗泽格结婚。1951年以短篇小说集登上文坛。50年代中期,皈依天主教。1955至1972年间侨居巴黎。此后定居斯科南省的大学城隆德。她获得过很多文学奖, 1993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除了小说也擅长散文和诗歌。她自述,自己的宗教信仰与诗意的画面和生活状态是一回事,所写故事都设置在斯科南省她成长和生活的地方。
“这是我的天性”
特罗泽格的文字富于乐感和画面,句子曲折。在《沼泽王的女儿》里,她用诗意语言描绘了交织着耻辱和责备的“邪恶童话”,和她的其他作品一样,有无法消弭的沉重和黑暗。
有评论家认为,特罗泽格始终跟随自己的视觉和感知,不放松一分一秒,纯粹而全心地孕育,作品让读者仿佛走在一条布满锐利石子的路上,脚和眼都会流血。在一本诗集里,特罗泽格写到:“这是我的天性,在简单的想法里将前额贴于地板——/上帝怜悯怜悯吧!无论信或不信,世界处于死亡和出生的挣扎中,信或不信,可我的唇是为/那些字眼而生,我的唇是因他人的音和字有了形状,我的唇是为作为工具的语言:怜悯!”
特罗泽格也描摹光芒,但那丝微光不易被察觉,天主教信仰让她笃信,生命从一开始就是生死搏斗,不过,人还是要寻求美好与上帝,尘世间有可能性,有未竟的义务和责任。
有人质疑有宗教信仰的人本该力求喜乐。对此,特罗泽格回应,人在面对神圣的一切时,可以有快乐、忧伤及其他反应。受难唤起悲伤,复活带来快乐,但喜乐不可被用来模糊世界的面目。人有责任跟随世界的步伐,不能随便地说:别那么吃力地承受艰辛的痛苦,天堂里一切会有安顿。“我看见世界是混合的,因此上帝也是。它神秘而巨大。”跟随世界的步伐,生活的步伐,也是这部小说的模式。
特罗泽格相信,人得开心,可抑郁也能产生 “古怪的快乐”。在黑暗中也有一个行动、一条路、一场战斗或其他这类东西。当不知什么是黑和白时,很多人体验到生活复杂而矛盾,看不出何为美好、邪恶、悲伤、喜悦,而跌入一个集体的糟糕的自我感觉。“我为自己写,以便弄清这一切。”
她认为“万物都有内在的喜乐”。比如,沼泽王的女儿作为新生儿,“发亮、闪烁,牙牙学语——这整个的小身体是一块有力而快乐的肌肉。”可她极少描绘喜悦,因为“我什么也不描绘,我工作于生活那整个的一团,那一团里有欢乐和悲伤,是个整体。我书写以便看见,我看见一幅画面并书写,书写以发现它是什么。”特罗泽格自认,所有表达和陈述都是“带着一份快乐倾吐的”,“写作根植于出色的孩子气的快乐,一出游戏”,这一切并非她坐在那里感觉而已,而“自然是一种戏剧表演,一出和玩偶的游戏!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游戏。生活若无语言则无法存在”。
《诗篇》139篇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又说:“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还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些句子几可用作《沼泽王的女儿》的旁白。子宫和胚胎的譬喻常现于全书,黑暗、光明、成形、罪恶等堪称关键词。登场人物是一群不完全具备人形的家伙,他们与内在的“罪”搏斗,希望成形,甚至走向永生。
异常与矛盾
异常可能是异类闯入同质领域,也可能是同质区域里生出变异。小说以蟾蜍作为异质性的标识,而实际生活中有更多哪怕看不见也可感知的异质性。当某集团和人群用约定俗成的尺度来衡量一个对象并判定其为异类时,不可调和的紧张感便油然而生,快速传递给同质和异质的所有分子。异质分子或极力求同化而不得,或全无归化之心,但被驱逐的命运都不可更改。然而,世上几无完全同质之区域,同一人物的内心也绝非均质。特罗泽格笔下从渔村到城市的女子就有明显的内在矛盾,这加大了她自己及其亲人的悲剧性。
因为和蟾蜍人也就是沼泽王的性关系,渔村女被降格成“半动物”,在怀孕后不得不离开乡村以远离耻辱。她继承了原生集团的尺度,又受异质生物吸引。性欲只是原生环境无法提供的所有自由欲望的指代。社会的禁锢和冲破禁锢的欲望相冲突,渔村女的欲望和羞耻与沼泽的淤泥相连。
被吸引又无法让关系见光,沼泽王总在晚间突现,叩响门扉,女子总会为他开门。渔村女在白天和夜晚、现实和幻景、自认有罪和沉溺“罪恶”渊薮间摇摆。她给狱中的沼泽王寄包裹后会立刻后悔;明明在梦里杀死了他,又继续在现实的夜晚为他开门;甚至,在她和别人结婚后,沼泽王还会借幽梦到她身边。
渔村女更对这种关系的证明——“沼泽王的女儿”产生无法控制的厌恶,非婚生孩子时刻提醒着母亲的过失。比如主妇们议论沼泽王的女儿:怎么那么黑,是不同的种类。她们的目光影响了莫阳这个母亲的眼光。她有了奇怪的视线,像是另一个人在看。前一瞬还觉得女儿的眼睛是所见过的眼睛里最美的,下一瞬,女儿的脸成了一摊粘土。她甚至会慢慢伸出手来掐住孩子的脖子。她和女儿去学校,本来很骄傲于自己给女儿缝制的衣服,却被嘲笑。回家后,莫阳看到一件沼泽泥制的衣服;一头动物吃掉了原本给女儿准备的东西。社会的视线是一把裁判之剑,母亲饱受压迫却又积极地把利剑悬于自己和女儿头上。
母亲的异常性与矛盾性也传递给了女儿。沼泽王的女儿在出生时被看成蟾蜍人,面孔如灰灰的面团,没有形状,和人相比自是异类,属“非正常”。沼泽王的女儿一向被孩子们欺负,有时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动物。一天,女儿和一只蟾蜍相遇,有某种神奇的一体感。女儿想按照传说,用同情让蟾蜍获得人形和人的价值,但几番努力还是无法克服厌恶感。蟾蜍死了,她陷入痛苦的自责。
生活就像一只蟾蜍
渔村女是蟾蜍人的女人,沼泽王的女儿是蟾蜍人的女儿,都低人一等,甚至也是“半动物”。渔村女和丈夫的婚生女表面看符合规范,但作为早产儿,智力体力并未达标。渔村女的丈夫是酒精中毒者。沼泽王女儿的儿子有蟾蜍血统。这家人在“正常人”眼里,多数称得上人的“失格”。
只是人多少带着动物性和人性两面。何为合格与失格?谁能说自己完全合格?谁来裁判?为何有人天生就抓握裁判大权,而另一些注定被裁判?这些都值得寻味。广而言之,假如人生而孤独,便都是程度不同的异类,在人生的沼泽里,都是大小不同的黝黑而丑陋的蟾蜍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登场人物在故事发展的长时间内都无姓无名。无名或许既意味着他们的卑微不足道,也意味着一种普遍性。另一方面,一个名字有时难以细腻概括一个大活人,不同时期给对象扣上的代名词及词汇包含的微妙语气会暗含对被说明对象的评定和分类——来自集团的审定。这样的代名词远比姓名更一针见血,有些类似诨名,但也会抹杀个人存在,只剩下社会打在此人身上的标记。同时,人物被笼罩于羞辱中,这份羞辱让他们竟连自己的姓名也无权宣布。
可还是有些姓名出现了,大都是在遇到不幸或死亡后,如沼泽王女儿的姓名是从墓碑上被读出的。活着时挣扎在蟾蜍和人之间,通过死亡似乎现出了人形。如小说扉页引用的东正教复活节前夜仪式上的语句:“基督复活了,通过死亡,他战胜了死亡,而对那些在坟墓里的人,他给予生命。”于是人物的姓与名被揭晓:他们虽死而犹活。特别是全书末尾沼泽王的女儿在海边迎着母亲走来,那时正是复活节,自然复苏的时节。
特罗泽格写道:“生活也就像是一只蟾蜍:既是未成形的孩子,也是黑色的妈妈。”她接着说:“这就是生活,易损伤,未完成,很无助,好像还没成型。一只棕黑色的生物,在夏天的夜晚,总是一动不动坐在台阶的石上。它为何一直跑到了那儿:从什么时候开始,它期待着什么——都不可知。它只是直瞪瞪地坐着,在疙疙瘩瘩的黑皮肤下。眼珠从这一边转到那一边,像血淋淋的眼光。蹼指始终张开,其间潮湿黝黑的皮肤开着,似乎容易腐烂, 像新生儿的目光”,它是“既不像动物也不像人类的,未真正被造完成的生物,无助地希望能完成”。不像动物又不像人类的,岂止沼泽王及其女儿,许多无助的人子,特别是“异类”何尝不如是。
“古怪的蟾蜍人爬行在空旷的街上”——在谈到沼泽王之女后来在夜间卖淫时,这一句腾空而出。可能是童话空间里的画面实录,可能是绝望的象征,传神地表达出无法成为集团的一员,无望地陷于正常和道德之外的苦痛挣扎。
存在主义和基督教思想
天主教徒特罗泽格在1960年代的大都会巴黎目睹了底层人的贫困、社会差异及殖民主义战火下阿尔及利亚人的处境,深受触动。存在主义和基督教思想是她的思想基础。她描写人世间,聚焦困顿于尘世的具体人物,写他们的外在生活状态和内在心理困境。她所处的时代使其有左倾激进倾向,这和她信奉的天主教和存在主义理念交织,让她同情被侮辱、被抛弃和被损害的人,特别是女性。
黑暗层层重叠。被侮辱和损害的滋味,世间之人哪怕处于不同层次,多少都有所品尝。所以,特罗泽格的描述有穿越时间和地域的普遍性,是对存在之普遍特征的呈现。女性和异族等便成了传递媒介和外在表相。
在黑暗中,在身为异类的苦痛里也有快乐,但被抛弃的人无法在苦难外生存,只能在其中彼此伤害。精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情景、个人及社会之矛盾的不可调和被特罗泽格一一暴露。比如,沼泽王的女儿卖淫,与其说是道德上的过错,不如说是母亲和集团的逼迫。特罗泽格写道:“社会是如此的:那些生来要高高在上的高高在上。其他人在底下。那些注定要决定的决定,其他人被决定:他们被使用,他们作为任意一个可被扼住喉咙的人在被使用。”
评论界认为,瑞典文学中鲜有像特罗泽格那样探讨基督和上帝的神秘的,她写得贴近生活又激烈深刻,她呈现从罪恶之根生发的羞耻,并渴求基督的恩典。
特罗泽格让莫阳在医院生孩子,待了6天——好比上帝造万物的6天。她还写道:“上帝造出了黑暗和光明。上帝造出了天堂和大地。他也造出了天堂和大地之间的那些陌生区域。”天堂里的位置,地上的立锥之地一定是合乎规范的,中间地域或许是存在的灰色地带。
“永恒是用怎样的声音诉说的呢?在午夜,他听到一个喃喃的沙哑声音。下雨。树叶晃动并絮语。一只猫头鹰低沉地吼叫,另一只回应。”“蝙蝠穿过黑暗盘旋,无声之音中的一种。”“一切都活着。用何种声音?是谁诉说在牢房中将有一位天使到来,站在那儿说,走,于是牢门会自动打开,只需走出去?”这是一段出神入化的笔墨。牢房该是死寂而禁闭的,作家却说,一切都活着,牢门开着,永恒在诉说。永恒和上帝相关。灭顶的黑暗、猫头鹰和蝙蝠的背景、低沉之音及无声之声,像黑暗还要被细分出层次——其中传来天使的讯息。现实和神秘幻景结合,叫人难以否定其可信性。建立在天主教信仰上的文字,对有无此信仰的人兼具可读性,因为其中闪烁着精神的真实。
魔咒般的语言和神奇的意象
特罗泽格的文字诗意而精准,和故事的黑暗、疯狂混合一处,逼真细节又与离奇想象并列。作者自认有神助,认为是“图像自己找到了那些形式,在一种能触知的喜悦里,我好比是用语言作画,我对自己所写的没有任何指望,只是,在这条路上,我可以遇到那些显示会转换成故事的问题结”。
在她眼里,生活本就是矛盾的,她意识到邪恶和美好彼此连接和相互消费。世界是模糊而流血的混乱,“凶手和圣贤带着不可思议的密切和心里能感受到的连接绑在一起,就好像他们在同一个自我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她所知道的、生活最完整的模式。所以,她描述出复杂生活世界里,有对立,有福音。贫穷、流产、卖淫、酗酒、疾病、死亡等经她串联,散发出恶之花的美。
小说里有很多象征。特罗泽格对大海的看法可用来形容这部小说的特色:难以区分哪里是表面,哪里是深处,哪里是人声,哪里是水声,哪里是自然自己的声响。所有的声音都有节奏,是声之音。
“岛”是全书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既是现实中的岛,也有神秘和宗教的意味。女人带着私生女,不被群体接纳,如在孤岛;沼泽王常提起一座黑色的岛。沼泽王的女儿死后,莫阳看到一个景象:船在夜里划出,船上有一具尸体,一个摇橹的男人,一个在船头举火把者;火炬照亮黑色水面,射向更远的地方——水的源头。文中虽未直接提及岛屿,但不难想象会有所关联,就像勃克林的名画 《死之岛》。
“太阳”也被反复描述。永恒的太阳是上帝的象征。它“永在大海之上。永远射入黑暗”,“太阳如闪电般诞生……在海和地,湖泊、沼泽和城市之上,矗立着这强大而静默的光”。特罗泽格还说,死亡是太阳的阴影,并把月亮唤做太阳死去的姊妹。
双重性的延伸和两个层面
“沼泽王的女儿”在安徒生笔下最终解决了人性和动物性的矛盾,有个美好结局。特罗泽格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观察,无法让沼泽王的女儿在活着时找到出路。同时,双重性在她的小说里得到延伸,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乡村和城市、守规和逸脱、性爱和婚姻。
特罗泽格写道,人的脑子里会有固执想法,它从哪里来?有一天想法就凸显在那里,“就像胚胎:沉重,未知”,也像是有人在描画,在纸上游走——“这是就要来到的世界”。
农村渐远,城市浮现,会有怎样的生活,遇到怎样的人呢?在小说开篇,女子离家出走时,特罗泽格提到胎儿、沉重、未知。一方面,渔村女当时确是孕妇,另一方面,她的未来不明朗,又确实在孕育着某种未来。在新的城市,她首先看到的是监狱的高墙。下意识中走到关押着沼泽王的监狱前也不奇怪,特罗泽格所暗示的或许是,监狱是社会装置,是和乡村生活迥异的新社会秩序的象征。走近现代化和城市不意味着能摆脱苦难。这个有新秩序的地方和她因怀孕而逃离的地方并无本质不同,一样具有“裁判的人和被定罪的人”。“社会是为那些有权存在、那些真正的人所构造的。另一边,就是那些不该来的。”孕妇和她将生出的孩子显然不属该来的那一群。
有社会秩序,就有对秩序的挑战。“性”往往是极易挑战秩序的东西。而沼泽王“所到之处就会带来破坏,一种他不知是如何发生的毁坏”。沼泽王和莫阳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从秩序逃逸和挣脱的关系。莫阳亟需一个集团接纳自己,她的“性”必须躲进合规的框架,才能安全——这是莫阳的婚姻。
沼泽王偶尔在夜间来偷会莫阳。他也曾把脸靠在女儿学校的篱笆上,从栏杆间瞪眼寻找。“这是个黑黝黝的家伙。他一见她就做了个手势。此后,她会在这里那里看见他。”沼泽王的女儿十一二岁那年,他俩又碰上了。他送她一个玩偶,她跟着他:“男人抓着女孩的手,把她拉到自行车后,带入命运的空地。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很模糊”,人们似乎听到一声喊叫,许是鸟叫,一切都在迷雾之中。 然后,他消失了。这也许是一场强奸。沼泽王的女儿15岁开始卖淫,最初的冲动是寻找父亲,更深的原因是她希望被爱、被肯定。 怀孕后,和母亲一样,她也离家出走,到首都斯德哥尔摩。带着儿子回到母亲身边后,这家人第一次觉得,“他们三个都在天堂里”。以为生活终于走上正轨。怎奈沼泽王的女儿又开始在夜间失踪,在家则如同困兽,一个破败坍塌的生活,没法再支撑起来。
此外,贯穿全书,特罗泽格始终呈现了两个层面:蟾蜍的、童话的神秘层面,以及人的、现实世界的层面。
沼泽王的女儿死后的一些年,莫阳找寻到海边。沼泽王的女儿复活了,朝着莫阳走来。宽大的黑面孔平静并闪烁着日出的光芒。她环抱着所有死去了的人。 在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奇迹里,爱的可能性在世上复现,这总归还是一种希望,哪怕生活真如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人的周围。这部主题沉痛的小说,有乡土气息浓厚的逼真细节,有历史和幻境。包含情感的沉郁文字聚焦于苦痛和脆弱,聚焦于爱的死亡与复活,让人体验到一个神秘又宗教的整体,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故事结束于1980年代的斯科南省。而罹患帕金森症的特罗泽格,于2011年病逝于隆德。有瑞典评论家认为,并非很多作家都能把人的最纯净和最黑暗的两部分都揭示得那么深刻,特罗泽格是威力和仁爱、压迫和救赎、原谅和审判的化身,是“我们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