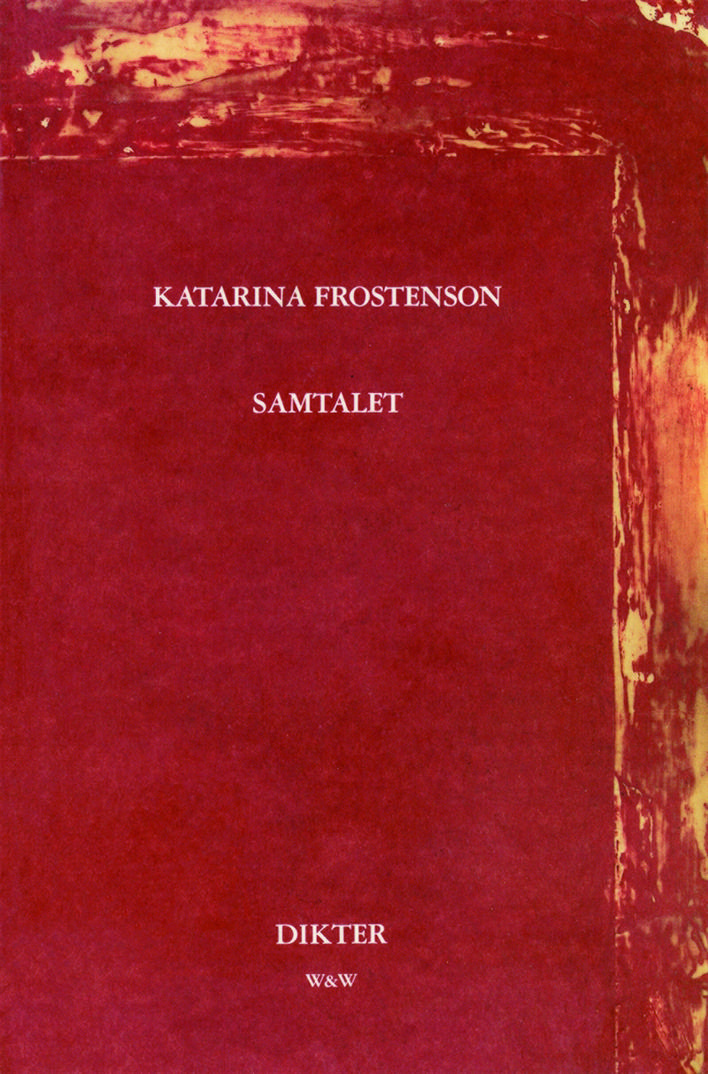还带着旧时代的基因,又有对新时代的感知,弗洛斯藤松并不彻底,她活在悖论里,身处悖论未必不是她流连忘返的舒适状态,悖论或许正是她文字的泉源。
“Me Too”——风乍起
卡塔琳娜·弗洛斯藤松(Katarina Frostenson 1953-)未必能预料,自己的姓名以那样的方式一夜间传布世界各国。虽然这位瑞典学院女院士在北欧原本声名显赫,甚至堪称瑞典最富才华和影响力的当代诗人。
2017年的深秋,“Me too反性骚扰·女性平权运动” 的烽火蔓延到相对清净的瑞典,在戏剧界、教育界等,一些人物相继被揪出示众。11月21日,一篇暗示某文化名人在过去近20年里,骚扰甚至性侵女性的报道登载于瑞典的权威报纸《每日新闻》——这也是一家相对左倾的报纸,如同扔下一颗炸弹。谜底很快揭晓,此人是弗洛斯藤松的法国丈夫。也并非空穴来风,这个法国男人的姿态在首都上流社会和文化圈不算秘密,多年前也曾东窗事发,但多数人将他的言行诠释为风流,不知还有报道所指出的许多不堪。事情越闹越大,甚而爆出其人涉及泄露诺贝尔文学奖秘密!舆论哗然,弗洛斯藤松似乎失踪了,一言不发。她不说话,但她的诗歌,哪怕是以往的,其实并未停止表达。
瑞典诗人和剧作家卡塔琳娜·弗洛斯藤松1953年出生于首都斯德哥尔摩。大学毕业后从事过教师和医护等工作。1978年携诗集《在中间》登上文坛。其后继续创作诗歌、散文,译介包括杜拉斯在内的法国作家作品,也创作了不少剧本。此外,她和她的那位法国丈夫主持了由首都一间地下车库改装的文化俱乐部“论坛”,那里自1980年代以来成为当代作家、音乐家和画家的荟萃之地,对文艺有一定贡献。弗洛斯藤松的诗作繁多,有《净土》《在黄色里》《谈话》等。1991年的诗集《离子》堪称里程碑,内容集合北欧古老民谣、古典神话等元素,语词相互纠缠,又一同滚动向前。1992年,只有39岁的弗洛斯藤松在一派赞扬声中当选瑞典学院院士,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女院士。
弗洛斯藤松自述,瑞典女作家和诗人比姬塔· 特洛泽格、卡琳·博耶等都是自己灵感的泉源。然而,她其实比她所列举的先驱们更进一步。弗洛斯藤松认为,诗歌中必须有音乐之核。她的诗反对譬喻、意象和象征,突出文字、声音和节奏,且让文字和声音相互作用。同时,她所书写的并非传统的那种上下文词意相连的诗,相反是意思跳跃又含混的;传统诗歌排列相对均匀,她则会在字母大小写、字体、线条、空格、图形等方面有所实验,以加强诗歌在情绪和节奏上的表现力。作为剧作家的她,其诗作也有明显的场景特征。因此,她的诗歌一面为众人喝彩,一面又被公认为难以理解,更难以翻译。
后现代——“我迷恋你”
后现代是复杂的概念,谈起它,就不免会谈起解构主义、折衷主义、对权威的不尊重、对理性的不信任、完全的感性等。后现代反思语言,强调理性的局限、真理的复杂,真实和语言的并非紧密相连。在非静态的现实世界里,难分现实与非现实、真与假,更难以识别自己的人们,其自我正在被消融。
1980年代,后现代主义来到瑞典。北国瑞典虽说处于世界经济与文化危机的中心之外,也还是受到主义之风的吹拂。那是弗洛斯藤松风华正茂的岁月,她就是受到强大冲击的人中的一个,正立于时代变迁的分水岭上。她写出的诗里就缺乏一个“我”,“你不在这里/你并不存在于这里,没有面孔”;即便冒出一个来,也绝非传统诗歌中当仁不让的主角,大多只是一张并不鲜明的脸。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弗洛斯藤松拒绝迎合旧有模式,回避譬喻、意象和象征,回避说故事的旧形式,而搜求有动感和乐感、且和意蕴并不分离的语言。她执著探究真实和语言的关系。她在语词上的抱负,她与语词的新关系,似可从以下短诗中看出点端倪,诗的标题是“你”,副题为“我迷恋你”:
你
朦胧了语词
你是我的思想
太阳
我没法思考
在你近旁 眼花缭乱——
当你说谎
阴影生长。火花——那玫瑰
可能性
并非一切都是荆棘
和真相
伟大是字词的
甜蜜广度
你何时不撒谎?
这不是法令
诗人到底说了什么,扑朔迷离。然而,不难感觉,“我”看重“语词”,看重语词的广度,更求真相与自由。弗洛斯藤松曾提及“激进的消极性”,称其为“一种抵抗”,也就是说,对某种现实图景的“反意愿”。她要导出“那些可见画面背后、不可见的图像”,她理想中的书写起自于破坏而着眼于建设。在她看来,文学的语言不在于堆出日常生活,而在于导出那些为日常语言所掩盖的。她的这一审美立场成就了其创作的动力和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他人的诗歌策略。
奇妙的是,“我”和语词的关系,类似于弗洛斯藤松诗歌中“我”和“你”,以及女性和男性的关系。弗洛斯藤松是瑞典女性诗人代表,被贴上这个标签,和她所采用语词的暧昧与性感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两性关系问题是她探索颇多的题材,在不少诗集中一再复现。
“我”与“你”
——相亲相杀的彼此
且不谈诗集 《离子》的第二部分以一首北欧中世纪民谣为题材和基础,大篇幅书写“处女”,写一名男子追逐一头鹿——一个在魔法下呈现出鹿之形态的女子,也是男子的未婚妻。他杀死了鹿,便也杀死了女子和未婚妻,只能把枪对准自己的心脏。古老的传说本已奄奄一息,背起当下活着的人的苦痛,吐出现代人的心声,传说也借机复活了。被弗洛斯藤松复述的民谣,让女权主义者嗅出男女之间难以避免的、相亲相杀的宿命。诚然,在弗洛斯藤松的民谣诗里,鹿于冥冥中知道自己将被射杀的命运,依然“径直向前”,首先被杀成了女子杀死男子的手段。
但还是不谈这个,只谈人与人的“相似”这一个让弗洛斯藤松纠结不已的问题。这部诗集中就有一首,题为“我们相似”。开头这么写:“我们彼此相似。几乎没一点差异。今夜。月宝宝的光亮下。我们在那儿摆下,一个挨一个,白色木腿桌上的亚麻。是无人入眠之夜。静止的相伴,空气里有股宿舍味儿。在长长的霍尔拜因的基督的长度里。”这些句子到底要说什么并无答案,大致能感知,这其中有对某种关系的聚焦——“我们”的关系。
人要抵抗与生俱来的孤独,便都会不同程度地探求与己相似、几无差别的“他人”,“他人”则注定了差别的存在。相似和亲近都是相对而短期的幻觉。彻底或不时的离开才注定是关系中可见或不可见的主旋律。这首诗里出现的瑞典语“lik”一词,作名词用有“死尸”之意,当形容词则有“相似”之解。这么一来,这几句诗被指有尸体一具挨一具之图像不足为怪,虽不算惟一正解,也未必是无稽之谈。弗洛斯藤松的诗作颇具后现代的互文性,词语在碰撞中能叠加和再生出诸多意味。假如一词多义说还略显牵强,“霍尔拜因的基督”一句提及的确实是小汉斯·霍尔拜因和他创作的著名画像《墓中的基督》无疑,显然无法排除死亡的气息。横在木桌上的躯体到底是什么呢?虽然从字面看是提示横着的姿态和长度,但那木桌上的,可能是普通人,也未必没有墓中基督的影子;可能是活的,也未必不是死的或半死不活的。墓中基督超越死和活,不可言说。外加“静止的同伴”一句,让“此地”的“我们的相似”飘荡出一股瘆人的怪异和凶险。“我们”的相似无差别竟只在死境。文字的戏谑宛如对人生的戏谑。戏谑是解构,是态度,未必没有最底部的严肃,也并不消弭绝望和悲哀。
其后,在“否定,闪烁” 一诗中,弗洛斯藤松再提“相似”,这样开了头:
和我相似的某个人
和我曾相似的某个人,直至最后
于是动词可停止行走
邪恶是你自己的节奏——事物里什么也没有。
叮当响,并且再响——
叮咚着漫步穿行这世界
蹙额。去:反对。不。
不。——无名。事物的同类,和简约的语词。“我愿”——
然后沉默。
这首篇幅较长的诗受到一场碎尸案的启发:1984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名妓女被肢解。案件的侦查和审理过程中呈现出双重暴力:女子很可能是被男性所杀;嫌疑人是两名彼此认识的男医生。一位有买春记录,其工作所在地处于两包肢体发现地之间;另一位,有医生的妻子及心理专家整理出的、医生才不过两岁的亲生女儿的证词——目睹了父亲肢解人体的场面。证据似乎确凿,其实不足,嫌疑人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几经审讯,职业生涯终止,婚姻消亡。然而,在诗歌里,“我”成了主导的、可实行肢解的人:“就像两个男人,/像两个来到的男人,看着的。斜靠着/发光的圆桌。一具尸体的所有断块。”在现实的事件和文学的诗歌中,男和女之间都存在一种你死我活的紧张,而真实和真相还在可触及的表象之外。难怪女权主义者认为,弗洛斯藤松诗中的女人时常是存在杀戮潜意识的处女,而男人则是表面温柔的杀手。这一点在上述那首改写的民谣和这首诗中大致都得到了证实。
在这首诗里,弗洛斯藤松说,“我在边界搜寻 世界/我要把你巡猎,直到边缘”,又说,“清澈,更清澈,最清澈/那里头都有什么——我要翻出它来”;她还说,“我躺在坡上吸收阳光/我梦着清澈的事物,/叮咚作响的事物且撞击/着彼此:在那里头”,她认为,“你可掉,转/你可粉碎这形式/你总可摧毁你自己挑剔地筑好的形式/一切——到无。/那自由存在,/就在你站立的地方。/听你的声音说话。”
弗洛斯藤松笔下的“我”在抵抗,就像弗洛斯藤松在为语词抵抗。然而,“我”仍束缚于“处女”的基因和出身,哪怕背负被射杀、又杀人的命运。在这样的诗歌里,女性还是站在男性对立面的一个否定因素、被动的他者。那个存在已久但始终未能获得圆满解答的问题还在回荡:不同性别的人,不同的人,如何能在一起而不至于相互摧毁?
值得一提的是,弗洛斯藤松对语词的追逐也有巡猎到边缘的决心和风格。她要反对。眉头紧蹙。说不。因为“我”撞见的世界是一幅巨大的图像——假象。“我”不情愿,有时“面孔撞墙”。弗洛斯藤松想“写出一个房间,那里,比喻被吹开,世界被写得更直接,且无需转换,而它的回声能被听见”。弗洛斯藤松爱说“不情愿”,在一次读者见面会上,主办方请她朗读一首诗,她就嘀咕了一句:“好吧,可我不情愿。”她谦和,总有一种对理所当然的抵御,又在不情愿中停留于她自己的处境。
两肩梨花
——“从不曾在你内部活着直至我消失”
一首题名《梨花》的诗,按说可以柔而美,它在弗洛斯藤松笔下呈现出如下的风味:
什么和睡眠相似。睡眠,另一种
不是厌烦,不是不愿看见
叶子和开裂的梨的睡眠,蜂
因甜味而迷醉
盐分,那里所有的水相遇——
一个山谷,自很久以前
一条河道穿过它
坡上老梨树
那儿有片田
声音的生命回归
回音和叫喊,巨浪来临
先绊倒你,而后让你回头
有个黑皮男人在那儿
两肩梨花
向前走来,立于我的生活之后
拿手蒙住我的眼
这叫温柔
把手指伸向颊骨
纯净是残酷
黑暗在他的骨头里沙沙沙
他在自己的生命里酿蜜
从田野中,他把它带到这儿,一块块
而后铺床, 涂抹——这场睡眠
不长
类似于崩溃
一个冲向山谷的瀑布,那里不知言语
砾石、雪、格罗兹尼
冻土里的皮鞋
冷土中冒出的唇
在那陌生语言里感觉
它起立的轮廓
一把红梳
火花洒落。他的光芒
带着黑鞋,雪亮的鞋头
而冰冻大地上正落着
来自另一山谷的梨花
“嘴唇”、“骨头”等本是弗洛斯藤松诗歌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字眼。这首诗中还有开裂的梨,河流穿峡谷,床铺,涂抹等。这些字句的整体与其说是勾勒出情色的调子,不如说让诗情之雾得以弥漫。弗洛斯藤松的词句带叮当之音,相互撞击,激荡出一种暗藏的冲突和不安,如“温柔”和“残酷”,“两肩梨花”和“冻土皮鞋”,让人难以无视字词本真的声音和意味。像梦中的断片残章,若有所指,一串流动的气息、声响、动作,先于语词的字面意义和在通常文本中携带的传统历史及文化意义,率先扑面而来,跳成神秘画面。
一般来说,散文和诗歌比之小说更能泄露作者内心的秘密,这在弗洛斯藤松身上或也能得到佐证。早年就有女权主义评论家质疑弗洛斯藤松的一些诗作中“我”与“他”的关系、“我”的处境和态度,断言瑞典的女性杂志若是给“我”提出忠告,定会叫“我”彻底把“他”抛弃。然而,折磨着”我“的他,或许客观上是“我”得以表达出语词和情感的源泉。
细端详,可见一棵开花的梨树在温柔与残酷的悖论和绝境间挺立而出,是濒死状态中求得的最高快感,是于最远的疏离中求得的最大一体。很难肯定或否定,弗洛斯藤松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人与人相遇的一种真相,或不限于男女,不限于同辈、同族和同国度之人,不限于人与人,而可推而广之、念及人与物、与某个地点、某个时代,所有纠结又难分的关系。弗洛斯藤松点燃了一支关系的鸦片,她的语词有罂粟花的神秘、妖冶以及伺机出动的致命绝望,预示着鸦片点燃后的沉溺与幽梦。“梦”或“做梦”,也是弗洛斯藤松时常使用的字眼,她未必想分割梦与现实。本来,现实对她而言,并不是人们以为可想当然看见和说出的,而必须用一种更直接、纯粹和准确的语词去撞出来。她听见响声,声音的回声,那大概便是现实的回声。
关于“我”和“你”,弗洛斯藤松还写过这样的句子:“我看着你/于是你消失/你来了又去”。她也多次这么写:“从不曾在你的内部活着直至我消失”。然而,“我”终究还是活着的,在诗歌里,在诉说里,“嘴巴,/我将教你说话/直到你看见你自己”。诉说与听见是存在的一个重要和必须的方面,被听见就是被看见,就是和他人发生了联系,以便确定自己果真存在。
嘴巴,诉说
——我选择不作回答
弗洛斯藤松经常使用嘴唇、牙齿等和诉说相关的字眼。她提醒过,“听你的声音说话”。而她的《声源》一诗也特别耐人寻味:
那嗡嗡的杂声是什么
我看不出对你我已餍足
从不曾在你内部活着直到我消失
我被填满。因你的目光
闪亮的是根
o
你额上的暗黑和脑子里的沙沙声是什么
我撞上你的脊背。冷笑——
它嗡嗡地,哼哼地。继续
一个切口在你的哼哼里,一个切口
(o为分割号,原诗如此)
可见,“冷笑”或者是别的什么,和“你”有共同特征,嗡嗡地哼哼地。这看似低沉又绵绵不绝的声音里,暗藏着杀伤力——切口。嗡嗡声是这首诗的开头和结尾,是贯穿始终的被聚焦对象,是“你”和“我”的关系中凝结出的声响。探究这声音的源头,或可透视其他。
“我”不“餍足”,在与“你”的关系中被动而受冷遇,却屡败屡战;不然不会有脊背、冷笑和切口。“脊背”形象地显示了一种无法实现的沟通和最遥远的接近——共处中的巨大否定。女性向往一个人,有处子的基因和姿态,怕被粗鲁地对待;女性向往激情和热爱,向往被看见和听见,怕被当作躯体来侵犯。“你”并没有与“我”作有效的交流,只有嗡嗡声。可能是不会,更可能是不屑——认为毫无必要。“我”的诉说,不是模糊不清又沉闷不绝的嗡嗡声,是借助于诗歌的诉说衷肠。语词交错回荡,余音袅袅。仿佛走在一个矛盾里,失望和迷恋共生,又自生自长,有一股不合语法和逻辑的野生气息。这诗歌中的语言不是手段而是中心,这诗歌是语词自己的独白。
“我书写是为驱出图像,那个在我看来遮蔽了原生世界的图像,太肥厚的文字,便让诗的肌腱和骨头都消失了”——弗洛斯藤松曾如是说。她想写出一个房间,那里比喻被吹散,取而代之,世界被更直接、被不加转换地写下来,而它的回声能被听见:“我想创造一个空间让喋喋不休的声音存于其中。”这番话也道出了弗洛斯藤松诗歌的特点和用力之所在。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洛斯藤松具有先锋性,但她还是无法甩开性别及时代的局限性。
就像物质生活的进化总是快于文化生活的进化,弗洛斯藤松在语言上的先锋性不能确保她在意识上的先锋性。假如当今男性真如一位女权主义者所言,多数仍活在18世纪,那么,定有足够多的、意识也活在18世纪的女性来支撑这类男性的存在。还带着旧时代的基因,又有对新时代的感知,弗洛斯藤松并不彻底,她活在悖论里,身处悖论未必不是她流连忘返的舒适状态,悖论或许正是她文字的泉源。
弗洛斯藤松还是会写“处女”主题,写男女两性的战争,而在一个新人类主导的、男女更平等和解放的未来,这些恐怕都不会成为被瞩目的题材。弗洛斯藤松的解放,距离瑞典的妇女运动已超过150年,在上帝的眼中距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大概还是相距不远。女性虽已跋涉千里万里,女诗人弗洛斯藤松依然在奋力挣脱条条框框,并跨越边界。就像她用力在诗里呼喊的:要巡猎,直到边缘;要翻它出;要打破框架。她用自然的语言直面真实的存在和存在中的苦涩与矛盾,以便找到一片田地,在那里,声音的生命已经归来。做语言实验,在语词中追逐自由,力求让语词脱离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依附。但这终究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努力。因为一切都多少和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有关,甚至性别也无法超脱。 由此,弗洛斯藤松所面对和所进行的都成了个巨大悖论——尽管这个悖论也充满诗意,她便在无意识中成了以先锋面目大展拳脚的传统守卫者——带着“处女”遗传基因图谋反叛,这注定了她的先锋性的不彻底。
由于弗洛斯藤松丈夫的丑闻,瑞典学院也陷入一场运动的漩涡。在纷繁复杂的情势里,学院投票表决是否将弗洛斯藤松逐出。赞成者主要认为,不可因友谊而忘却大是大非;反对者则呼吁,不能因一个丈夫的不堪而吊死已在受难的妻子,尤其是,事件并不影响学院的文学判断。这投票进一步推开多米诺骨牌,数位院士唇枪舌剑,并且争斗还在继续。
弗洛斯藤松终于宣布休止学院工作,但并未表示完全退出。今年的5月17日,在风波正激荡的时刻,她的新诗集《七枝》面世。出版社没安排任何媒体访问,书评却都积极肯定,认为弗洛斯藤松从不让她的读者失望。诗稿被认为在“Me too”事件前业已寄出。颇具戏剧性的是,新诗集里有这么一句:“昨天在街头有人跑近,靠近我的脸,说:去死!我选择不作回答。”新诗集被认为继承了弗洛斯藤松一贯的风格,同时也写了忧伤,写老之将至,写生活从自己身边走开,用简易的语言接近生命朴素的真实。诗集分七部分,含有树木及家族树的意味,又不限于此,表达了疑问、惊叹、恐惧、自由。
作为一个一贯呈现出对抗姿态的女诗人,弗洛斯藤松眼下所经历的一切必将出现在她未来的诗行里,必将定格为超出个人、超出社会和文化新闻范畴的大事件。她的诗歌和生活产生了奇怪的互文效果,折射出时代和妇女、人与人等诸多问题,并且,像她的诗歌一样,内容和节奏都在滚动之中。“诗人时常觉得无法给出被期待的答案。人们总希望诗歌能引领到某个地方。诗人就在那里头,对生活和语言有洞见——为何不能从诗歌中问出更多这样的东西?人们希望导出更固定的结论。”弗洛斯藤松则表示,诗人无法针对自己的诗作给出答案。诗歌不回答任何问题,要避免斩钉截铁,否则很快会出现矛盾,诗歌更应是转换,是揭示变化中的存在。世界、边界和框架都被她挂在嘴边,她是否真能突破边界,粉碎框架?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因为她还在书写。
弗洛斯藤松1987年出版的诗集《谈话》中,收录了这么一首自传体小诗。题目为“我”。
我体内的一切动身
去看别处 远离
那些名字、讲话
和地点:一块石上的一只苍鹭,
出身地
我站立且冻僵在我的名字里,它的纯净
一条道上的一个长长独白 在高坡,
一条荆棘路,一架梯子带着
惟一的一节
她或许曾想表达,来自一个名人荟萃的家族,以及捍卫这个姓氏的纯洁性的压力,但也许还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