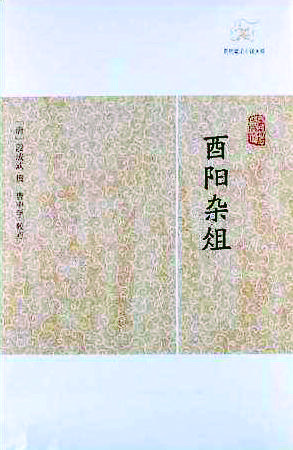对于“儿童文学”的认识,处于不断变化与演进之中。观察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古代如果有童谣、童话的存在,自然有儿童文学的存在。民间儿童文学的存在,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前提。
一般认为,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三大板块,但也有的论者把文学史直接纳入文学理论之中,如美国雷·韦勒克的名著《文学理论》就是这么做的。受其影响,国内已有多种文学理论教程也将文学史纳入文学理论之中,仅笔者所见就有鲁枢元的《文学理论》、南帆的《文学理论》等。因而今天我们讨论儿童文学理论的问题,不妨也可将儿童文学史纳入进来。而事实上,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争鸣往往会涉及到史。由于许多人都将进入文学史的作品(书目)视作经典,文学史即是文学经典化的历史,是对经典之作的一种“权威”鉴定,因而如何书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哪些作品可以或者应当进入儿童文学史,自然是一件涉及到儿童文学理论的意义重大的事。
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国古代是没有儿童文学的,因而中国的儿童文学史书写,最长也就百余年的历史。那你该怎么看呢?
这是使我一直纠结于心、久久难以释怀的一个“儿童文学理论”的重大问题。因为我在某核心期刊上读到了这样的论断:儿童文学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只有“建构”的“观念”的儿童文学才是儿童文学,由于中国“古代文献里从未出现过‘儿童文学’一词,可见古人的意识里没有‘儿童文学’这一概念”,因此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建构”的“观念”的儿童文学,所以中国古代是不存在儿童文学的。
有人告诉我,这一观点似乎已被视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权威观点,照此推论,中国人的儿童文学历史最多也就上百年而已。“建构观”因为是从西方文论批发来的,所以特别显得“高大上”与前卫、先锋。读完这篇大作,实在使我无比忧伤,按此观点,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断:我们的祖先在还没有发明“人”这个字,也即还没有“建构”的“观念”的“人”之前,人是不存在的,因而我们的祖先也是不存在的。再按此观点,那些被周作人、赵景深们反复论证了的“中国童话自昔有之”的童话、童谣等等“实体”儿童文学,尤其是被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研究界视为经典的中国古代“灰姑娘型”童话——唐代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故事自然也不是儿童文学。还有美学家李泽厚,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美的历程》中就断言:《西游记》“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永恒典范,将来很可能要在世界儿童文学里散发出重要影响。”不知道李泽厚是否需要补上“建构观”这一课?
作为一位热爱并坚持了数十年儿童文学教学研究的学人,我在即将完工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论》一书中,也提出了自己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观。
第—、文学的概念是发展的,如同人不可能是搞清了“人”的定义之后才做人一样,文学也不是先有了“文学”这一定义,才出现文学。文学的要义是渐进的、发展的,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文学”一词,如果按照“建构”理论,那么是否可以反证中国古代文献里只要出现“文学”一词,就说明古人的意识里已经建构起了“文学”这一概念,也就有了文学呢?果真如此吗?据查证,春秋时孔子的《论语·先进》里就已出现了文学:“文学,子游、子夏。”这是不是孔子在表扬子游、子夏两位弟子有文学创作的才华或有志于文学研究呢?但遗憾的是,此“文学”非今“文学”,孔子不过是表扬他们爱好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而已。即使到了晚清,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所言“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中的“文学”,也不是现代美学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另有所指。在传统学术观念中,“学”是学识,文学是关于“文”的学识。中国文论史上的“文学”从来都是开放性的,对于文学的认识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同样,对于“儿童文学”的认识,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与演进之中。
第二、文学是一个“类”词,可有一比,如同“水果”是一个类词一样。水果包含着苹果、桃子、李子、杨梅、樱桃等种种具体存在的实体果品,因而只要有“实体”果品的存在,就有水果的存在。文学也是如此,文学包含着小说、散文、诗歌、童话、寓言等多种具体文体,因而只要有具体的文体存在,就有文学的存在。由此观察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古代如果有童谣、童话的存在,自然有儿童文学的存在。
第三、纵观文学的发展,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是必然途径,民间文学是整个文学的组成部分。因而可以说,只要有民间文学的存在,就有文学的存在。中国儿童文学也是如此,只要有民间儿童文学的存在,就有中国儿童文学的存在与发展的前提。这一观点实际上来自《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该书的“童话”词条有这样的说法:“法国童话集佩罗的《鹅妈妈的故事》,集中收有《灰姑娘》《小红帽》等篇,而《美人和野兽》篇则忠实地保留了口头传说形式;德国格林兄弟的《儿童和家庭童话集》则直接根据口头讲述记录而成。佩罗和格林的影响一直很大,他们收集的故事大都成为西方有文化的人所讲述的童话。”“艺术童话大师,其作品与民间故事一样能够永远不衰的,是丹麦作家安徒生。他的童话虽然植根于民间传说,但却带有个人的风格,内容包括自传和讽刺当时社会的各种成分。”
正是据此观点,我在《中国儿童文学史论》一书中明确提出:唐代段成式(803-863)的《酉阳杂俎》是中国第一部童话,这部书中的《叶限》是世界上最早用文字记载下来的“灰姑娘型”经典童话。因为它比法国佩罗(又译贝洛,1628—1703)于1697年所搜集发表的《鹅妈妈的故事》中的《灰姑娘》要早830多年,比意大利巴西尔记载的灰姑娘故事也要早七八百年。我又提出,明代吕坤(1536—1618)的《演小儿语》是中国最早的民间儿歌集,也是中国第一部儿歌专集。
毋庸违言,提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这一文学史概念,显然是基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成熟后对自己“身世”起源的追溯,是一种“后见之明”的谱系的“发明”。如同在凡尔纳时代,人类还没有建构起Science Fiction这一概念,所以凡尔纳本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位科幻文学作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今天被世人视为科幻文学的卓越代表。同样,尽管中国古代没有出现“童话”“儿童文学”之词,但这并不妨碍《叶限》《白水素女》《旁竾兄弟》《虎媪传》等作为古代童话与儿童文学经典文本的意义,因为即便用今天“纯儿童文学”的标准去衡量,它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儿童文学。而载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是世界上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灰姑娘型童话。《叶限》所记载的孤女叶限那只得而忽失、失而复得的金鞋,正是世界各地“灰姑娘型”童话故事的关键情节,并以此区别于一般后母虐待孤女的故事的特殊标志。既然法国、意大利版的灰姑娘故事《玻璃鞋》可以被视为世界童话的经典,为什么中国版的灰姑娘故事《叶限》反而连作为古代童话的资格都不具备了呢?这岂不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双重标准”?
世界上的事,建设总比颠覆困难。颠覆多容易,你说那老房子已没什么价值了,轰轰轰——推土机顷刻推倒,多爽快多轻松,而且还有一种引领新潮的陶醉。但你要说那老房子还是有价值的,那麻烦就来了,你得纵探源流,横诠诸说,小心地考证出价值之所在,当你焚膏继晷爬梳钩稽时,“保守”“封闭”的笑声正从斜缝里钻将进来。但是,对于历史这所老房子,对于文学史这样的精神建设工程,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借助推土机,而是需要洛阳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