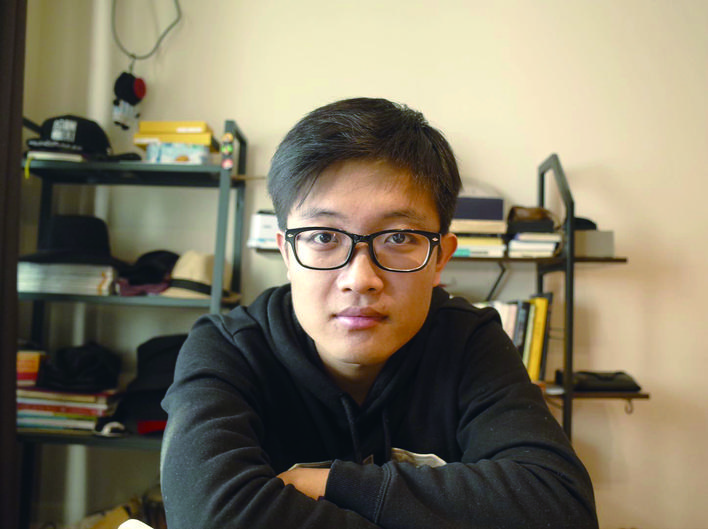自从去年年底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一些“90后”作家作品,至今已对目前比较活跃的“90后”作家有了一个大致了解。这番阅读,我最大的感触,并非是这些青年作家作品中有某些东西让我震惊,而是反过来,这种阅读难有新奇的发现,促使我对我们当下的评论研究进行反思。
难以发现新元素,如果简单对待,必定就是会指向这些作家作品的不新颖、不特别。但这绝对不完全是作家作品本身的问题,很可能是评论者的失误。这有两个可能。一是评论者的思维太陈旧,发现不了新作品中的新元素;第二是评论者使用的词汇太陈旧。或许一个评论家发现了一些新因子,但没有使用全新的表达方式,而无法使人信任这种发现。没有陌生感,也就不会觉得新作品有什么新颖性,同时也会失去阅读这些新作品的热情。
比如对于李唐的小说,如果不用心去琢磨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征,我们很容易就将之纳入先锋、实验、意识流一类,这些特征的确可以形容李唐小说,但绝对不止于这些。或者说,即便有这些叙述传统、文本特征,如果就停留于界定这些标签,满足于通过特征描述来对作家作品进行一个化类,而且是归入一种已经失去了陌生感的概念标签内,那么,这就是评论的惯性化、惰性化表现,是对作品的不负责任。
李唐的作品在语言、叙述上,富有诗性和智性等特征,在故事特征层面,其神秘、幻化的气质也非常突出。但这三个层面的特征,只是表层的风格。我以为,要深入到李唐小说内部去,抛开这些已经谈论了无数遍、四处可见的文本品质,去看到深层次的新颖和特殊。这方面,李唐其实非常用功。比如对传统主体性概念的突破。李唐很多小说都有一些神秘的动物意象,这些动物,一方面是小说人物的情感投射对象,似乎只有动物才能跟人实现真正的交流,现实的人已经无法沟通了。另外一方面,这种人与动物的关系,其实是非常新颖的思考方式。这些年世界性文学理论探讨的主要问题中,就有人与动物关系。李唐小说对此有洞见,甚至具有前瞻性。回到动物,就是回到最本真的人,就是摆脱近现代启蒙哲学所界定的、现代政治经济秩序规定的“人”的概念。这也可以对接上最近流行的“后人类”,回到本真的“人”,人就完全可以进入到“后人类”的“人”。
另外,李唐最新长篇小说《身外之海》,我认为也提供了很值得探讨的新元素。比如小说虽然讲述一个发生在海边小镇的故事,但小说的两条线索,包括很多零零碎碎的故事元素,都映照着现代城市各方面的精神困症,小说其实是创造了一个疗愈型乌托邦空间来表现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疾症。对此,《身外之海》就不可以再以传统的乡土、小镇、城市题材来做简单的类型划分,更不能以直接的题材类型来理解和界定它的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