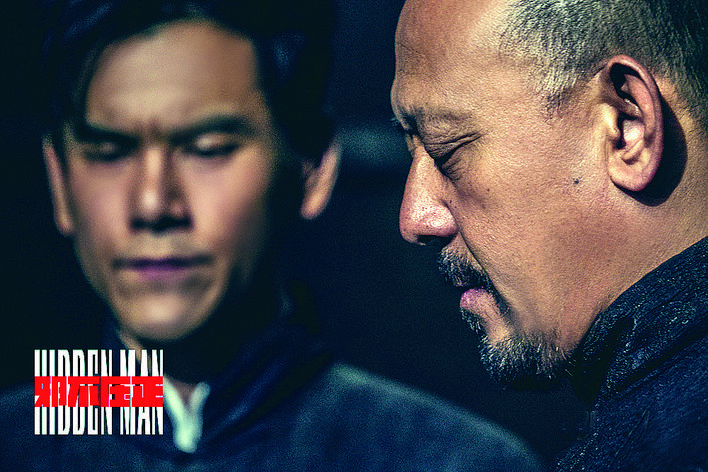30年前的夏天,北京人艺话剧《天下第一楼》首演,旋即轰动北京城。30年来,这部作品常演不衰,走出国门,演出近600场,成为北京人艺仅次于《茶馆》的保留剧目。作为这部戏的编剧,何冀平于首演的次年转战香港,靠着在北京人艺打下的坚实写作基底,在商业社会中重新起步,与徐克合作的《新龙门客栈》为她洞开了影视剧的新天地,《黄飞鸿》《新白娘子传奇》《楚留香》《龙门飞甲》《投名状》《明月几时有》《邪不压正》等享誉华语影视界的作品里都有她的身影。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院庆,她又用一部《甲子园》汇聚起了朱琳、蓝天野、朱旭、郑榕、吕中等再难复制重现的“豪华”演出阵容。很多人说这是何冀平为北京人艺量身定做的一出戏,这大概也可以看成是远走他乡的女儿送给家中母亲的一份珍贵的生日礼物吧。
光鲜的背后,是鲜为人知的超常付出。就在几天前,何冀平刚刚完成了为陈凯歌与章子怡合作的短片撰稿。两周内出了5个构想,不同的本子写了6稿,为赶拍摄期,每一稿都是在几个小时内完成,最后累得要靠人参支撑写成完成稿。如今她已然练就十八般武艺且样样精通,邀约不断,写作不停,在话剧、影视、音乐剧、戏曲等不同艺术形态间自如切换,于文学与市场间维持了难得的艺术平衡,出手的作品既叫好又叫座。她用一支健笔,写出了世间的大气象,也开创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品牌。
创意是人世间最昂贵、最值得尊重的
文艺报:小时候您在北京由外婆带大,外婆也是读书人,她对您童年的阅读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有没有对您此后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或剧作家?
何冀平:那时太小,家里书是有的,后来捐就捐出去3000多本,但专著和古典文学较多,没有什么小说,看了我也不太明白。家里没有刻意培养我,我就是喜欢,也有机会去剧场看戏,看完《天鹅湖》就给幼儿园小朋友排节目。我组织小朋友演,我演老妖。我喜欢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喜欢《红楼梦》,喜欢昆曲的词。记得小时候看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子》,里面有这么一句:“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子”。长大了,渐渐明白了这句话的内涵。
文艺报:您入职北京人艺后完成的第一部话剧是《好运大厦》,1984年首演。能介绍一下该剧当时的演出效果吗?以今天的视角,您又是如何看待这次最初的创作?
何冀平:当时很少有人去过香港,人们根本不了解香港,我1979年第一次到香港,回来带的是“出前一丁”,作为礼物一人一包,那时候都没吃过。吃完了他们都特别喜欢,说太好吃了。我在香港看什么都新鲜,写了很多随笔,前些天,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它们,真还写得不错,但当时也不懂得发表,就想到写戏了。《好运大厦》刚出构想,北京人艺就看中了。记得去人艺谈构想,第一次进首都剧场后楼,见于是之、田冲、夏淳、刁光覃等人艺大牌,听我谈构想,吓得我手直抖。这部戏,我写的算是中规中矩,有几个人物还可以的,但整体不够深入,还是以内地人的眼光看香港,排的演的也不太像香港,我是尽了力,人艺也是尽了力,做了不少素材收集,还把我婆婆石泓请去讲香港的生活、服饰。一开票,买票的人排起长队,挤塌了西单售票亭子,都以为是演唱会呢。记得这部作品连演了80场。
文艺报:进入北京人艺工作后,您当时分配到了剧本组。那时,于是之是组长,在您之前的很多访谈里,您曾多次提及于是之先生对您创作的影响。于是之在抓剧本工作的时候,给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些?他在激励青年剧作家成长、成才的方式、方法上有没有独到之处呢?
何冀平:于是之先生最独到之处,就是两个字“尊重”。他尊重作者、尊重文字、尊重创意、尊重知识,他明白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于是之语)是用脑子用心在付出在劳动,每一个字都是心血的流淌。他文学修养很高,什么都懂,但从不强加于人,口气总是商量的,很谦逊。如今仍有些人,不重视编剧,觉得写几个字算什么,请人搬件东西都知道要付钱,为什么请人写东西就觉得不必给报酬呢?创意是人世间最昂贵、最值得尊重的。于是之懂得我们。知识分子羞于谈钱,也不太看重钱,看重的是尊重。于是之给我的尊重,激励我坚持、不怨、无悔,使我终生难忘。后来在香港,也曾遇到过自以为是的权威,借助权力蔑视我、踩我,逼迫我服从,我绝不屈从,我说,我是人艺“惯着”长大的。
人虽老,只有戏,还像它30年前一样年轻
文艺报:写作《天下第一楼》时您尚不足40岁,如今这部作品已经演出整整30年了。新时期以来,能够常演30年的剧目屈指可数,《天下第一楼》可谓其中的佼佼者。回想当初,最开始排演该剧的时候,您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剧中卢孟实的命运沉浮是否也是您人生经历的投影?
何冀平:撰写《天下第一楼》至最后一稿时,正值《桑树坪记事》火爆上演,我的母校制作、我的同学编剧、我崇敬的老师导演,各大家撰文盛赞,有如发现一颗新星,戏剧界一片欢腾。现代化的视角、全新的演释方式,像一个戏剧新时代的起点,调动起全体戏剧人的兴奋。而它,又是不是另一个戏剧时代的终结?我犹豫了。收起已经基本完稿的三幕戏,重新下笔。这一稿以倒述的方式结构,从卢孟实的成功、狂傲、洋洋得意写起,直到高楼万丈,日进斗金,宾客盈门,写到最后一幕,尾声是“一声婴啼”,卢孟实诞生。这一稿写完第一幕,就进行不下去了,笔拉着我往回走,只能放弃,重新继续已经成型的原稿。
全剧在排练厅连排了。我们都不怕演出,怕连排。近在咫尺,坐着曹禺院长、刁光覃副院长、所有部门大小领导,离退休权威人士,黑压压一片。我坐在最后排靠边,顾不上看戏,不时观看各人表情。戏完了,我出了一身汗。曹禺院长直接走到我面前,眼眶有些发红,他握着我的手,追问全剧结尾那副对联的原意,“你年纪尚轻,哪来的如此人生感悟?”我却一时答不上来。他亲笔为该剧题了剧名,并写下长诗,至今挂在人艺的贵宾室。一位资深的专业同行,走出排练室的时候不经意地说:“这种戏,最多演40场。”我睡不着觉了,半夜打电话给导演顾威,他的回答很坚定:“我保你400场!”有人说《天下第一楼》是北京人艺的夕阳,但这“夕阳”十分灿烂。一时节誉满京城,几乎所有名流皆有文章。1988年6月12日首演之后没停过,一连演出150场,接着去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欧洲以及中国台湾,所到之处皆受热烈欢迎,尤其中国台湾和东南亚。
《天下第一楼》比我的名字响亮辉煌得多。公演第二年我离开了北京人艺,人走茶未凉,人去楼未空,30年《天下第一楼》不停演出。灯光明暗、大幕开合、掌声起落间,送走一位位前辈,迎来一代代新人。走在人艺,不时会有人经过我身边时,认真地说一句:“我演过《天下第一楼》。”演了300多场龙套,才演到师傅的年轻演员已经步入中年;演过500多场的9位元老已退休;老导演夏淳已经仙逝;顾威导演已经白发苍苍;我从一个走出校门初踏戏界,被于是之称为“女孩儿家”的学生,已步入老年。人虽老,只有戏,还像它30年前一样年轻。一部剧,不仅凝聚着角色主人公的人生,也映印着作者的命运,带给我荣辱穷通,理解到人生的给予和索取、规律和无常,以及曹禺院长问我的,感悟与苍凉。
文艺报:《天下第一楼》上演之后,有专家评价其为“现实主义的回归”,您当时是如何理解“现实主义”的?有没有被观念所束缚?在您看来,一部话剧作品的艺术生命力体现在哪里?
何冀平:也许比喻不恰当,现实主义有点像电影的类型化,可以写得非常经典,也可以只是一般流水账,有种观念,觉得荒诞、先锋派、现代派好像比现实主义尊贵。我觉得不在于什么主义,要紧的是怎么写。戏剧是多方面的,最有生命力的是价值,体现在中心人物身上,内中有一点可以称为共通性的东西,能引起所有人有感受、被感染、能回味,但是不容易。那点真谛,像一个精灵,藏在你的作品中,和你捉迷藏,引诱你去寻找。找得到,要靠不舍的精神,找不到是经常的。
文艺报:如今《天下第一楼》不仅享誉国内,而且多次走出国门。您认为这部作品能够让外国人“无障碍理解”,依靠的是什么?30年来,您对这个剧本的改动大不大?是否喜欢别人改动您的剧本?
何冀平:好看、好玩、五行八作、各色人等,题材吸引。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下到老幼妇孺,上至知识分子,以至官居一品都可以找到看点,真正的艺术是可以不同语言、民族共享的。中国话剧要走出去,首先你讲的故事外国人要能懂,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明白的事,包括历史剧,题材要宽泛,道理要有点共通性,不要老想着戏是要教育人的,要想教育人也得先是好看。
话剧除了结构情节,靠的是语言,台词很重要。《天下第一楼》30年,演了500多场,加上香港粤语版56场,已是600场,剧本只改动过4个字。第二幕,卢孟实的红颜知己玉雏儿,为卢孟实乡下的妻子生下儿子不快,一气之下离去,卢孟实摇头暗自感叹。每次演到这里,我都觉得有点冷场,就在他摇头的同时,加了两个字“女人……”在一边的二掌柜,深知卢孟实的内心,紧接着说了一句“男人……”这四个字,牵动起台下观众的心,引起满场回应。剧本受到尊重,是剧作家毕生的追求。我不喜欢别人随意改动我的剧本,哪怕一个字。我说,你们读过百遍的台词,我读过上千次。有幸,《天下第一楼》自首演至今,只字不改。导演不但不许改动一字,连演员口语化的“嗯、啊、的、是、吗”这些虚字都得去掉,他说,这部戏的台词是有韵律的。记得排练初期,夏淳导演对二幕二场,卢孟实和玉雏儿的男女主角一段对话不太满意,说他想改改。虽然不愿意别人改动我成形的剧本,但一向从善如流。老导演认真地写了几天,写好之后拿给我看,我还没说话,他就说:“还是用原来的吧!”这是人艺的老艺术家给我上的一课,我永远忘不了。
我从最难写的话剧开始,底子打得实
文艺报:1989年您在北京事业发展正好的时候,却作出了“离京赴港”的决定。在香港的头几年,创作出了诸多风靡一时的影视剧作品。舞台剧编剧和影视剧编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创作形态,对创作者也有着不同的要求,您是如何在这两种不同的领域之间转换的?
何冀平:我还写过音乐剧、戏曲,好像没有一个太难的转换过程,像徐克找我写《新龙门客栈》,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看了《天下第一楼》剧就连夜找我,他说:“你能把一个饭馆写得这样有声有色,一定能写好一个客栈。”就这样,我开始写第一部电影,40天完稿,没有觉得太困难,后来,就开始接连不断了。《新白娘子传奇》已经开拍,因为卖得好,急需加20集,找到我,是一天一集赶完的。《楚留香》主要演员郑少秋不满意剧本,不肯接,制作人找到我,我改了,他就接了,这种情况不少。不论写什么,根基是一样的,就像食材是一样的,只不过菜系不同,佐料不同,做法不同。但基本功是一样的。我是从最难写的话剧开始,从素描开始,底子打得实很重要。
文艺报:1997年对您来说又是一个新的事业转折点。这一年,您应邀加入香港话剧团,重归舞台剧创作。推出的第一部话剧是《德龄与慈禧》。为什么以这部剧打头阵?香港观众当时接受这样的历史剧有障碍吗?文化多元性在这部剧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
何冀平:写完《天下第一楼》,我就想写这部了,我不喜欢清史,但特别喜欢这一小段,充满人性的阳光。《德龄与慈禧》特别符合香港这个中西杂处的地方,当时我已在香港8年,感受两种文化,有交融、有冲突,《德龄与慈禧》中展示的中西文化,那种碰撞,香港人特别接受,比起《天下第一楼》,他们说更喜欢这一部。剧中的慈禧、光绪、隆裕、李莲英等历史人物,都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旧样子,我以家事写国事,不明写政治斗争,无一点冷场和说教。其中17岁的德龄,这个受西方教育长大的中国人,就像是香港人的化身。
这部戏我没想到的是,一部历史剧特别受年轻人喜欢,小学生都爱看,看到中场休息不肯去上洗手间,怕误了开场。这部戏在香港6次重演,有国语、粤语两版,那时候香港很多人不会普通话,但都争看国语版,有的看完粤语再看国语,去感受其中的中国文化。剧本收入香港中学教材。曾在2008年代表香港参加奥运展演,受到评论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后来我改编为京剧《曙色紫禁城》,由国家京剧院演出,一样很受欢迎,一个小学校长看了,马上包了3场,让学生们来看。
文艺报:近些年,内地很多话剧影视剧创作纷纷走上文学改编之路,您也操刀过几部,诸如刚刚上映的电影《邪不压正》,早些年您也曾改编过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开市大吉》,以及刘鹗的《老残游记》。您怎么看这种改编?与原创剧本相比较,您觉得哪种难度更大?
何冀平:原创和改编的区别并不是很大,改编不比原创容易,编剧要下一样的功夫。倒是在改编或者原创的作品中,塑造一个新的人物,在原有的题材当中,重写已有的人物,给他一个新的角度、新的立意,这个难度是对作家的挑战。有的改编,原著只不过是给我取材。改编对我来说有种快感,就像一篮子各种食材,任我搭配。几次改编都还是成功的,像《开市大吉》被舒乙先生赞许“五个第一”,《老残游记》被我大拆大卸,基本上重写,但我没有偏离这部书的主题,获香港最佳演出等大奖。《邪不压正》和姜文导演谈了很久,改编丰富了原著中的全部人物和人物关系。
每一部作品中都有“我”和我的心
文艺报:纵观您的创作,历史题材的话剧、戏曲和影视剧作品所占比重要远远高于现实题材创作。您为什么会有如此偏向?是什么样的历史观在影响着您的创作?
何冀平:自从到香港,我的写作完全市场化,都是对方找来,有导演、明星、制作方、出资人,他们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不干涉,不束缚,由我来完成。电影主要是和导演配合。我从来不把历史题材当作历史来写,必须是现代人的眼光,纳入现代人的轨道。写《德龄与慈禧》,历史上真实的德龄是十分奉承慈禧的,她在宫里一直都在讲奉承的话,做恭维的事,并没有更多展示她的个性和才能。但是作为戏剧作者,我必须要给她新的个性和行动,把她塑造成我心目中的人物。她与慈禧一老一小、一中一西、一古一今、一尊一卑,涉及亲情、爱情、国事、家事,用她的坦率真性情影响深宫帝王。她书中有一句话:“站在老佛爷的龙床边我就想:如果我能利用这个位置做更多一点事的话,那就太好了。”她没有做到,但在我的戏里,我做到了,作者可以依据历史,写出自己心中的人物。这就是写历史剧的快感。
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
文艺报:作为知名的剧作家,找上门来的项目想必也非常多,面对不同的项目要求,您是怎么取舍的?您曾不止一次说过:“我不是不坚持,只是不固执。”您始终在“坚持”的是什么?
何冀平:以前取舍不多,来者不拒,好在我运气好,合作的都是大导演和“正规军”,作品基本可以保证质量。现在题材对我不是太大问题,反而合作者很重要,导演、制作人能够理解我,懂我,知道我好在哪里,这很重要。如果我写得好的,有味道有灵魂的,都给删了改了,我会很沮丧。编剧毕竟不是第一线的,作品必须由导演和团队来完成。我的“坚持”指的是,内地给了我深厚的文学根基,香港给了我灵活的机敏应变,这两者的结合体成就了我的作品。而每一部作品中都有“我”和我的心,题材可以千变万化,但这一点是变不了的。
文艺报:在编剧这条路上,您可谓经验颇丰,荣耀和艰辛遍尝,更是对这个职业始终笃定、坚守。这个职业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对想入行的年轻编剧来说,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何冀平:重要的是不要图钱、图名,为这两点所误,就会改变初衷,改变本性,写不出真情,没有真情的作品可能名噪一时,但早晚会被淘汰。我说过,我们这一行很个人,但又来不得半点个人,满脑子私欲,就算成名也是一时的,有钱也不是真富有。年轻编剧要记住,认真付出,写出一部好作品,保你一生。做人和写作,从来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