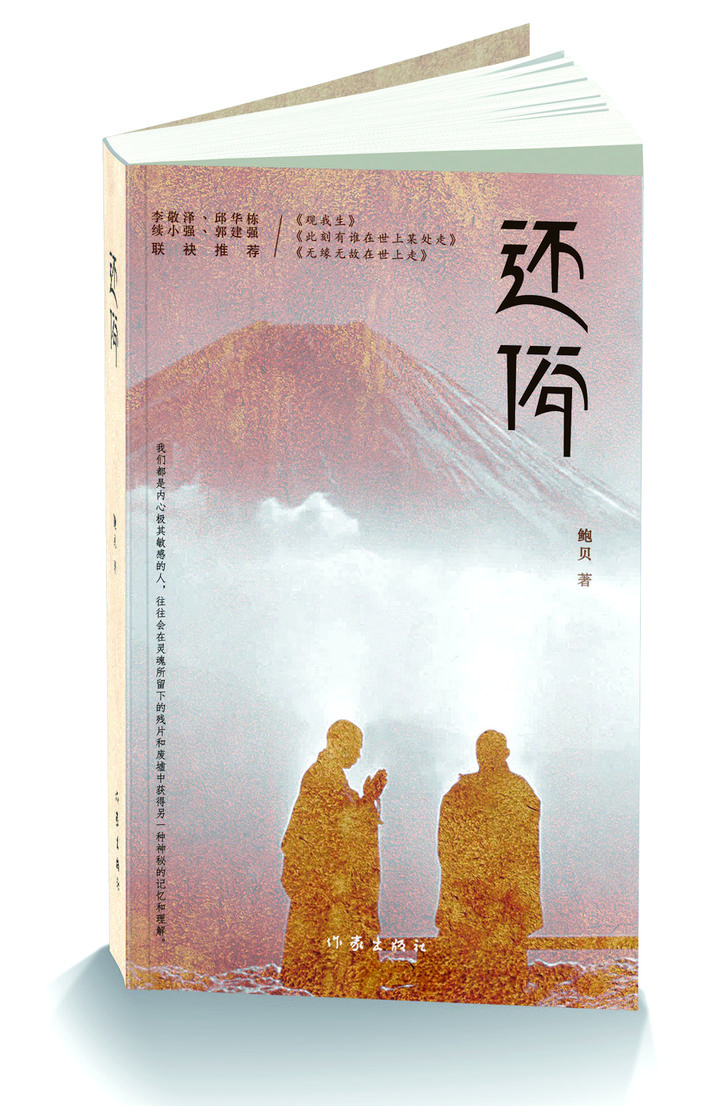《还俗》是鲍贝三部小说的合集。一部是长篇《观我生》,一部是中篇《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另一部是“短篇”《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我是把这个“短篇”当成“后记”来看的。所以,读完《还俗》中的《观我生》和《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一句话便插了翅膀似的向我的脑海中扑了过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是《野草·秋夜》开篇的话。一句被分析、肢解了无数遍的话,它似乎有特别的深意。文末,鲁迅从秋夜的玄思中抽身而回,对着白纸罩上的小青虫,“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呵,飞蛾扑火——“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如今的它们,已是结伴而行,飞入了鲍贝的《还俗》,真可是化作了“苍翠精致的英雄”。
鲁迅的温情奇喻,正可移用在《还俗》主人公的身上。他们是《观我生》中的“我”和Frank(哈姆、贡布);他们也是“我”和泽郎、加央,从《观我生》的“虎穴”中一齐沉陷又沉陷,跌入《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的诗句中,跌入《无缘无故在世上走》的病态中,似乎就要重生于新的现实,冲破虚构的“白纸罩”,拥抱幸福的圣火,不料又被一阵莫名的阴风吹乱,没有升腾,只有坠落。
三部小说合在一起,鲍贝命名为《还俗》,这有一定的合理性。Frank和泽郎都是从寺庙走出的还俗之人,而且他们本就是一个人,一个无端进入寺庙又决意走出寺庙的人。Frank在《观我生》中业已完成了一次生死的轮回,因《观我生》在《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中的“出版”,于是化作泽郎再次出现,找到“我”,用现在时髦的微信聊起了《观我生》中的他和“我”。故事的结局,是他们没有重现《观我生》中的相遇,泽郎在寻“我”的路上因车祸而亡,再次将“我”留置于大而空的世界,于是小说末尾,里尔克犹如咒语般的诗句雷电一般劈闪着: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确有神秘的力量存在,否则不会再有《无缘无故在世上走》中虚构故事的主人公、出版社编辑和作家本人新一轮的虚构与真实的缠绕接力了。三部小说的叠合,增加了复述《还俗》的难度。故事确定,人物确定,时间却是支离破碎又反复拼贴才连缀起来的(那还是时间吗?),未知的命运如冬日雾霾中的人迹一般,似有若无,模糊不定,有点像大变活人的魔术。你的身体和灵魂被虚构的奇幻与叙述的变奏撕扯,一时升腾,一时坠落。从《还俗》抽身而出,你大概也是要化作那“苍翠精致的英雄”了,用《秋夜》里的话说,真是“可爱,可怜”。我想小说家和“我们”是站在同一个队伍中、朝着同样一个高音喇叭的。于是,享受了阅读的“快感”之后,我们不禁要问,《还俗》的题旨为何,小说之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在《观我生》中,“我”只是一个幻想着靠写作谋生的富家女,她的写作尚处于模仿阶段,对于“听来的故事”基本上是照单全收,没有了Frank的讲述,她大约无法控制自己写作的速度。不过,她的虚构和想象仿佛天生异禀,有如神助,许多对梦的描摹确如彩虹一般赏心悦目。这些笔法,我想远非那个身为富家女的“我”所能胜任;这些不时散落的奇丽的梦,大概只能经由小说家的“我”来为她代笔。所以我看,在《观我生》中,一直存在着两个“我”,一个是富家女的“我”,一个是“小说家”的“我”,她们如孪生,跳着危险的贴面舞,时而分开,时而合一;一个跟踪着Frank的脚步,在杭州、拉萨、尼泊尔、不丹的旅行中飘摇,不断确证这一个他的前世今生;一个潜伏在名为古若梅的富家女的梦乡里,不断刺探她潜意识深处的那一片草原,一次次接近这一个她的原初的禁果之核。
“小说家”的“我”,在《观我生》中草灰蛇线般的存在,为《此刻有谁在世上走》奇迹般的出现,留了一颗孤独的火种。在小说中,她如《画皮》的故事那般意味深长地变回了“小说家”的“原形”,再一次作“观我生”的婀娜状。小说中的人物果真找上门来了,对号入座,让人寒惧。在现实生活中,如此的“严重时刻”不是没有。如是贴了金,皆大欢喜,喝酒吃肉,如是抹了黑,大张旗鼓,对簿公堂,徒唤奈何。但还是少数的吧——毕竟,小说家比一般的人还是要聪明许多,更要世故许多,老谋深算大约应是他们这个职业的第一修养吧,绝大多数的小说家怎么都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那么,鲍贝小说人物的打上门来,是真是假?她说得好像是真的,仿佛她真的经历一般。她借了“小说家”的“我”的嘴说:“写作经年,虚构的人物无数,连自己都数不清,也记不清了。还从未碰过小说中的主人公哪天会突然找上门来的。”
可他真找上门来了。我以为,这是发生在小说家鲍贝身上的真事。确有雷同,绝非巧合。在《观我生》的故事中,Frank(哈姆、贡布)纵身一跃、不告而别,以欣然赴死的自杀幻想着能够洗却自身的罪愆。其故事的震撼,是虚构出来的如传奇一般的“读者反应”。在《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中,他以《观我生》小说原型的身份复活,化作惧怕临近死期的泽郎,这合乎基本的人情,他纠结于《观我生》中他的死亡结局而不能自拔,最终却以应是偶然的车祸死亡:尘埃落定,殊途同归。
我是真的唏嘘不已了。《观我生》彼时的虚构,是此时《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的现实,而此时的现实,果真只是小说家又一次精心谋篇的虚构吗?若是,真可辜负了“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的美好的悲情了。
把小说读成了真的事实,这还真验证了余华所言:“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真的中毒太深了,我如小说中的泽郎一般,被“小说家”的“我”一再地嘲笑、反感:“把小说所有细节都往自己身上套的神经病”,“阴魂不散的人”,“真是百无聊赖啊”。
不止是我,小说人物泽郎也以为是真的,作品中“我”的朋友给出的理由是:“虚构又不是撒谎,它只是你们小说家用来表达经验和重构世界的工具。”厉害了,这句话,它真是胜过了许多评论文章的滔滔不绝,这一读感远胜过我千倍百倍。泽郎说:“我失眠了。整夜睡不着。……我们一路上发生那么多事情,仿佛都是我亲力亲为。我知道所有情节都是你虚构的,但对我来说,这些经历比我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真实,它们让我着魔,也让我着迷。”你看,泽郎是一个多么好的读者!
与此同时,“小说家”的“我”也受到了奇妙的感染。“真实的霉菌”在她的心头发芽,虚构与真实的边界消失了,“小说家”的“我”多次蒙圈之后,在泽郎“真实”的裹挟下,也不得不在歉疚、罪恶、恐惧、迷茫的状态下妥协,而任其蔓延,直至泽郎的死讯到来,又陷入新的无以复加的虚无。
苦痛与罪愆似乎永无终结。在短短的《无缘无故在世上走》中,又一次读到的,是虚构人物与真实存在的扭结,是一部小说偶然出世的鬼使神差,是一个写作者不可违抗的宿命感,是人的信仰虚无化的结晶。
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事实是,《还俗》这部小说与我们是切切实实相关的。它迷失,但追问的是真相。它逃避,但时常蜷缩在爬满青苔的角落里做着毫无破败的梦。它笑对孤独,它不惧死亡。它爱每一个自己,它忧郁而宽容,偶尔一次的勇敢决定为每每退缩的人们带来鼓舞。它的现实,是你我的现实。它如此切近俗世中的我们,又指给我们俗世之外梦有别的模样。它叛逆,只对自己的内心臣服。“不停地荡来荡去,不知来处,也不知归途”,“我们对意义的不断追寻,却又让我们不自觉地陷入到无尽的忧虑和迷惘之中”。 如此无形的钟摆,唤回了我们面对时间刻度时早已麻痹的痛感。时光逆流,它带你我重回旧日时光的芭蕉树下,吟一曲“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胧明。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肠断声里忆平生。”它的凄怆是一种暗示,“今古山河无定据”的塞外豪放背后,是“相看好处却无言”这般温婉携扶的更为长久的历史绵延。
《观我生》《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终于合在了一起,成就了如今的《还俗》。它就像冷窗外的那些树,“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在冷的夜气中”,我们“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她说:唯有小说,才是我的人间烟火;唯有在小说中,我们才是彼此的人间烟火。
(《还俗》,鲍贝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