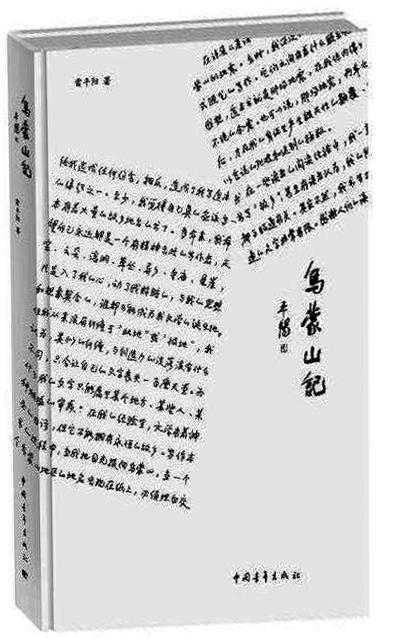雷平阳是个辨识度很高的作家,只要翻开他的书页,密集的诗文伴随密集的思想构成的人、神、鬼同在的别样世界迎面扑来,令人惊喜,无可抗拒。他植根原乡即云南天地的精神史写作,一如热带雨林的野生植物,既蓬蓬勃勃又芒刺在背,可以说是蔚为思想的旷野与艺术的丛林,独此一家,不可复制。
我认为雷平阳的写作是有出处的,在他与时代和生活相应的审美过程中,他既沿着楚辞离骚之文脉上下求索,又在感时忧民的叹息传统中,一如古典诗词天地人神鬼俱全,既静默穿刺于天地山水与人神鬼间,更追寻现世和未来的人的世界。于是,才有他的《在天空喝醉》,也有他知道的旷野的昼夜、阴阳、空门与尘世缝隙间的现实真相,而面对人们的《我不知道》,雷平阳不仅把旷野的“野草和荆棘引种于纸上”,在《送流水》般送走这一切中,直刺时代的神经。
是的,我们的古典诗词本来就是天地人神鬼俱全,此时的人神鬼,不仅在于修辞,也是现实存在,更是作者的文学观念。雷平阳将自身移入天地万物,移入人神鬼间,移入已知与未知,当然,也把万物与天地人神鬼移入自我,移入笔下的人物。为此,雷平阳的精神史写作便有了自己别样的文学世界;于是,大地生长的低吟与天空酒歌的欢唱同叹息也共忧伤,他总能在粗粝而渺小的日常细节中发现生命的欢喜和悲凉。
以《乌蒙山记》为例。我以为雷平阳的散文写作有着文体的自觉,而且文字也是有出处的。这种文脉的传统是诗文融合,其笔尖写人状物是领了先秦的历史散文诗文(诗赋)融合的传统。当我们看《左传》《汉书》《史记》,常常为其叙事写人的技巧而击节,也不能不承认其对后世小说的巨大影响,这样重细节的叙事写人和诗意呈现,在雷平阳的散文里比比皆是,体现了他的文体的自觉。他的散文每一篇都是一个寓言,这种寓言化的写作,在多个精神维度里,天地融合,外在的人、神、鬼,向内转化为灵魂的丰富性。他只求精神的真实,这是一种自内向外的自由自在。我觉得他的散文再一次证明了散文的精神就是一种解放,散文就是自由自在的性情之文,文体和语言皆可开放。可以说,雷平阳的散文拓展了散文的文体边界,他不仅诗赋融合,还频频虚构细节,追求精神真实与艺术真实,这也是对散文自由自在的一种文体实践。散文之“散”最初指无韵,不拘于韵,便是一种解放。用文字诉说生命、思想和性情,这种生命的迸发当然会使雷平阳的散文气韵生动,不拘一格。当然,这来自于雷平阳的个人修为和文学态度。
可以说,雷平阳与现实与时代相应的审美方式,就是一种精神的上天入地,他在人、神、鬼之间求索,他追问人何以为人?人何以如此?人还会如何?诗集《送流水》就已有所体现,而散文集《乌蒙山记》尤为自觉。一如《霍俊明的忧伤》一文中,他笔下的“霍俊明”既有虚构之笔,也有精神的真实。“霍俊明”游离于阴阳两界,探寻天堂与尘世之间的关系,其中自我也在不断的自我启蒙和生长反思中完善和成长,最后实现自我与文本较高的完成度。其实霍俊明的忧伤就是雷平阳的忧伤,也是我们的忧伤,因为一种失败主义总在笼罩着我们,这也是当下“70后”作家写作的一个普遍主题。在忧伤里,我们看到了天堂与尘世之间霍俊明的踟蹰不前、进退两难,且生的苦闷与欢喜同在。这是一种深切的时代之忧。
2006年,《人民文学》《南方文坛》联合举办的“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雷平阳被评为2006年年度作家,授奖辞中提到雷平阳的语言具有石头和土地的光泽。我以为,如今雷平阳的笔尖更隐忍内敛也更成熟了,那是一种矿石般的蕴含着宝石光泽的语言,有着语言的重量与思想的重量,这种重量融入了民间的文化,让汉语抵达尽可能的远方。而且他的语言有两个维度,既是对万物、对人间、对尘世所有的生灵有着一种深沉的热烈情怀,这种热烈情怀是以一种冷静而沉潜的方式呈现,且字字珠玑,叮当摇曳,更芒刺在背,又充满着反讽和隐喻。正如他所说“因为宁静的审视发掘出来的日常性中的人性乃至神性,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王国的孤独与焦虑;吟唱挽歌的声音里出现了阳光和月色,而不仅仅只是哀鸣。”《乌蒙山记》里,我们看到雷平阳不仅不止于叹息,更多地直面现实,尤其善待笔下的每个人物,在一种犀利的隐忍静穆与深切的时代之忧中,他寓言化状写人间,也指向未来。
雷平阳的写作还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作家如何与时代与现实建立一种相应的审美关系。我以为在雷平阳的写作中呈现一种深刻的当代性,他越来越对自己直面现实的审美方式有着理性的自觉。他说他“一以贯之书写的人、神、鬼同在的山中王国中,而更多地出现了因为虚构而产生的未知之美”,他是以直面现实为基点的“感时忧国”的叹息和反讽。一方面为散文文体的细节虚构性的拓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另一方面,从某些意义上来说,雷平阳就是一个天堂的守望者,一个密室的冥想者。他的文风是抑郁顿挫,整体风格是沉郁的,他所有的隐喻、双关,以及一个个寓言,直面怪力乱神的人间,却又对人间充满善意。那种善意是对笔下人物最大限度的尊重,一如对那位《距离东川十公里》独自在采石场挥锤的女人,面对她坚毅的目光,尤其她说“你只看见我一个人,我能看见好多好多的人”,“我顿时感到背上有一颗铁钉,正被铁锤打入骨梁。我没有再问她什么”,直至她忽然要求搭车、下车。又比如《宴席》中那些石匠、木匠、铁匠,那些和尚们,以自己仿生食物过着荒寒却欢喜的年夜,那份含泪的笑,赋予了文本深刻的反讽与寓言化的艺术张力。《天空安魂曲》信鸽家族和风筝家族的兴衰,隐喻了深刻的国民性,作者对两个家族人心得失给予了足够的同情之理解,而结句落在人人感激却是阴谋化身的邮差身上,令人顿生天地何以安魂之感,颇具艺术穿透力。《彩虹》的麻风病族,那抹人性与世道的彩虹,令人叹息与牵挂。《弑父》的寓言性则更多自省。《大戏》里那些如草芥般无望的村民,只能在梦里期待永不会到来的大戏,一代又一代,悲凉而又欢喜,因为这是有梦的村庄。《农家乐》中,谁说农家们没有自己卑微的欢喜,哪怕来自那一点点本能,且曰农家之乐。凡此种种,他把自己对现实的发现与思考,隐喻成一个个寓言化的别样世界,并沉郁地追问:人何以如此?由此可见,雷平阳深刻的当代性和寓言的内核,哪一篇不是以粗粝而渺小的细节,直面怪力乱神的人间,深度挖掘社会与人世的巨变,直指时代的神经,既体现了深刻的当代性,又呈现出审美的丰富性。我想,一个作家生命的宽阔和对人的欢乐、痛苦、伤痛的感受力是至关重要的,生活态度也是文学态度,如盐入水。
回到2006年10月,青年论坛给雷平阳散文的评语说:“散文以风尘仆仆的行旅风格,测量大地的胸怀和灵魂的重量,他的作品见证了一个成熟而谦卑的写作者,回到事物本身,钻探人心与世界的出色能力,也为今天的作家如何反抗苍白的纸上的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证据。”12年后的今天,我以为雷平阳更为独特深厚、颇具思想穿透力与丰富寓言性的作品,构成别样的文学世界,同样对作家如何反抗当下的创作同质化的现象,如何面对时代、理解现实、想象历史,从而进行有难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