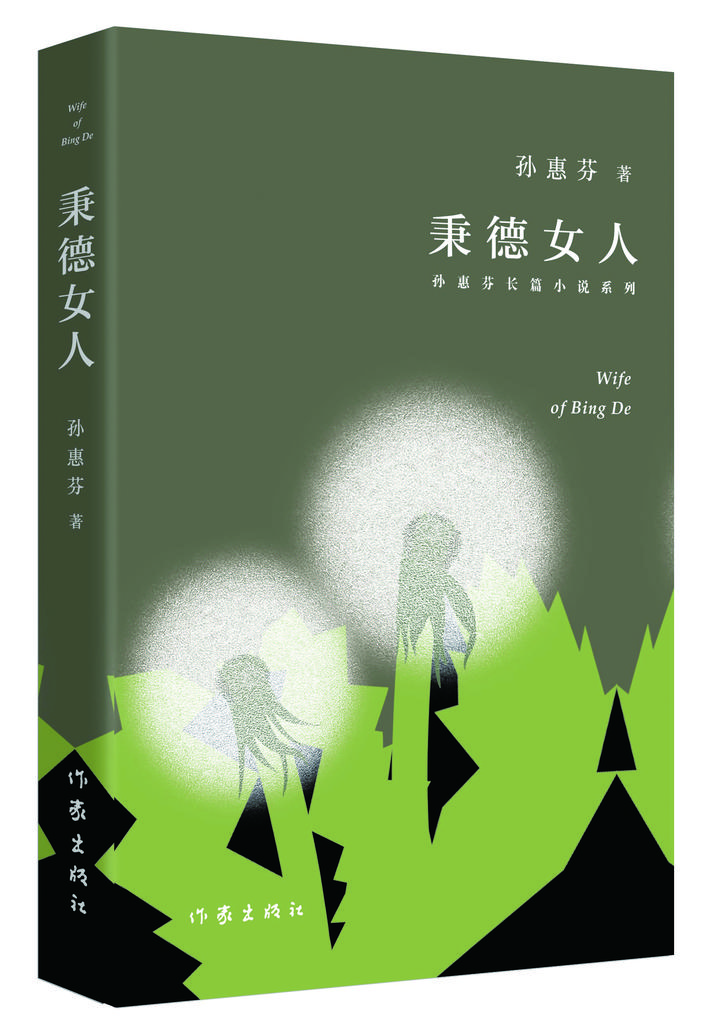五叔是20世纪50年代考到沈阳鲁迅美院的高才生,毕业后在北京、哈尔滨等地工作。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只要五叔从外面回来,当天晚上大家必聚到一起开会,听五叔讲话。五叔是公家人,是国家的人,他讲的事都是发生在遥远的外面的国家的事,什么中苏关系、中日关系,什么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卫星……那样的时刻真是美妙无比,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五叔的脸上,每个人的脸都微微涨红,仿佛五叔的话是从国家这个粗血管里流出的血,一点点渗进了家里每一个人的神经……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还有一种会让我难忘,那是生产队里召开的学毛选大会。那是“文革”初期,每到晚上,我都要在房后小树林里等待老队长的哨声,他哨声一响,我便撒丫子往家跑。那时父亲已经双目失明,他去开会需要我牵着他的手。父亲在那样的会上非常激动,抱着我听队长在上边念报纸讲话,下颏的胡须往往不住地抖动,身子一颤一颤,就像有什么东西正通过队长的话语传进父亲的身体……多年之后,我因为写作从乡村走出,在县城文化馆工作,有两年还阴差阳错地做了县文化局的副局长,变成了公家人,每周末回到乡下的晚上,父亲和三个哥嫂必定自动向我围来,像当年全家人围住五叔一样。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五叔的角色,讲我所能知道的那一点点外面的事、国家的事。那时我已恋爱,回乡下必带男朋友,几次之后,男朋友因为不能在更多的时间里和我亲密,再也不跟我去了。然而我从没因此而修改日程,因为我看到了父亲和哥哥脸上的光……又是一些年之后,因为写作,我散漫的内心经历了由对秩序的渴望到对秩序的排斥,以及到对无秩序的自由精神的强烈向往,我毅然辞掉文化局的工作,从县城调到大连,又在不断写作的努力中有机会做了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意味着再也不用上班,再也不必开一些无聊的会,能拥有这样的自由,对我来说相当不易,可是没有人知道,当我像家庭妇女一样成天坐在家里,再也不能经常出去开会,我的哥哥们是多么失落!偶尔的,我外出采风被哥哥们知道,他们会赶紧打来电话,兴冲冲地问:“怎么出去啦?开会吗?”每当这时,我的心都在隐隐作痛,仿佛做了亏心事。
2005年的一个下午,我带着当时89岁的老母亲去移动通信公司交电话费,面对站在柜台里的服务员排队等待办理业务的时候,坐在身边的老母亲不无遗憾地说:“你这辈子是不是再也不能像那些闺女那样干公家的活儿了?”我一时热泪盈眶,似乎终于明白,在不在公家里,是不是和遥远的国家有联系,只是人的一种存在感,是孤独的个体生命的本能需求,这种需求,不独属于知识分子,它属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包括秉德女人!就像一棵树总要参向天空,一条河总要流向大海。
仰望星空
1985年8月,奶奶去世,我第一次经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一场隆重的葬礼之后,奶奶的生命永远地寂于黑暗,从黑暗中耸立起来的,是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奶奶的出生年月:“1889年生于……”在奶奶活着的时候,对时间和历史茫然无知的我,从没有问过奶奶生于什么年代,从不知道奶奶降生时还是19世纪。当在石碑上看到1889的字样,心灵受到了意想不到的触动。从1889到1985,隔着96年的岁月,在这96年中,奶奶经历了什么,奶奶的生命有着怎样的升飞与回落、激荡与沉浮……那时,我刚刚开始写作,还不知道有一部长篇小说在等待着我,还不知道,1889这组数字,是一颗闪着灵光的种子。后来,父亲去世,叔叔、大爷相继去世,在一次又一次的祭祀活动中来到坟地,我总能看到一片漫长的没有边际的黑暗,它们在一簇簇荒草中间疯狂扩大,它们在1889这组数字的照耀下,露出山脊一般起伏错落的模样,而这起伏错落的黑暗在我眼前,长久地挥之不去……
这是一次黑暗中的写作,它萌芽于挥之不去地通向1889的黑暗之中,起始于对这黑暗探险的愿望和激情。之所以险,是说在这黑暗里,我携带的唯一的光,是心灵,是贴近人物情感的心灵。我曾问自己,我拿什么穿越历史,回答是:心灵。2007年秋天,在奶奶的生命寂灭了23个春秋之后,我发现只有心灵才能穿越黑暗中的荒野,将生命一寸一寸照亮。当然,我试图照亮的,不只是奶奶的生命,还有我出生的那个村庄许多人的生命,小说里的秉德女人,也已不再是奶奶,而是一个集合那一代许多女人生命的又一个生命。在我老家的村庄,不只奶奶,许多奶奶那一代老人一辈子都在关心外边的事儿、国家的事儿,他们的家国观从哪里来,这家国观是怎样一种面貌,它的背后隐藏了怎样一种生存状态,辽南黄海北岸这个17世纪就与世界通港的码头小镇究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在长达三年多的写作中,有一句诗一直萦绕耳畔,那是奥斯卡·王尔德的诗: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
它激励我在黑暗里探寻,一路爬过悬崖峭壁历经千难万险,它激励我寻找通向1889道路的出口,寻找从1889往1985走来的路标方向,就像书中人物在黑暗中一路不停地寻找生命的出口、存在的方向……一些年来的经历让我懂得,对存在方向的寻找,不独属于知识分子,它属于城市乡村所有人群,属于这个世界生活在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它是一种存在感,来自生命的原动力,如同一棵树向往天空,一条河向往大海。每个人都在沟谷中,有的人却在沟谷里仰望星空。这星空就像魔术师变出来的魔术,刚刚还五彩缤纷,却转瞬间踪影不见黑暗一片。在写作中,我,还有我的人物,在黑暗中一程又一程寻找,到又一片星空闪烁眼前,生命又一次欣喜若狂……
在黑暗里向着光明,如同向死而生。
(摘自《秉德女人》,孙惠芬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