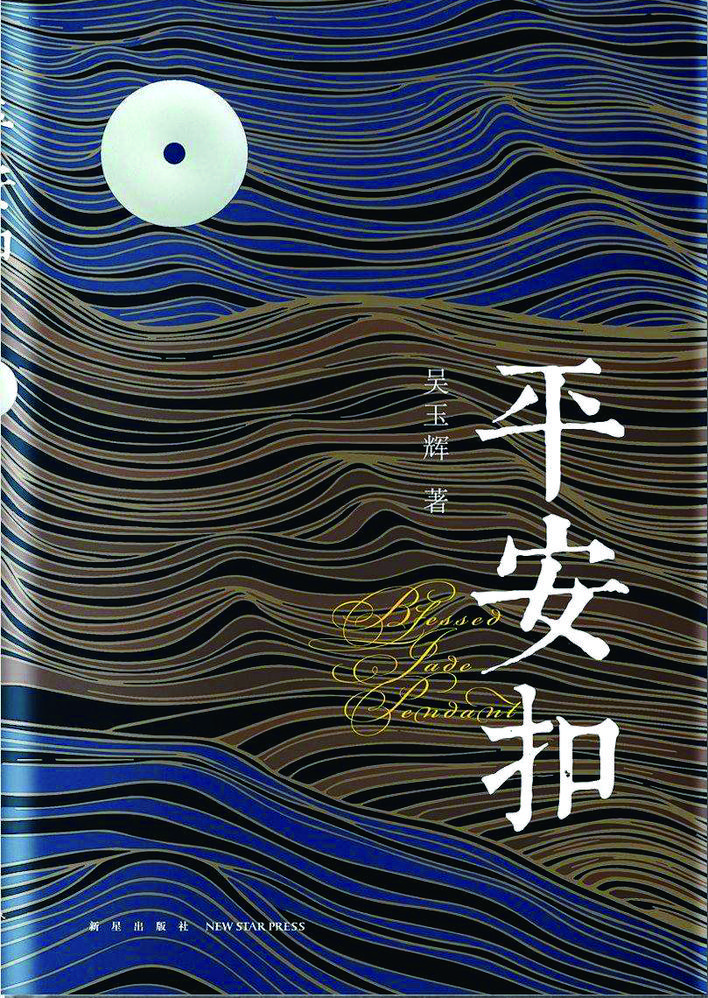福建作家吴玉辉长期从事党政领导工作,10年前携长篇小说《守护》登上文坛,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陆续有长篇小说《援疆干部》、长篇报告文学《谷文昌》问世,而且连续摘得两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桂冠。近日,他的长篇小说新作《平安扣》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小说落笔于东海渔村将近70年前的一场兵灾:1950年5月10日晚上,位于闽粤交界、东海与南海分界处的铜山岛(东山岛)月牙湾(马銮湾)畔的钵头村(铜钵村),溃败的国民党军队一夜从村里抓走147名壮丁,造成全村三天三夜断了炊烟。小说据这一史实,描写了这场兵灾悲剧,村中三对正在办婚事或正在热恋准备办婚事的青年(阿海与阿螺、水旺与阿巧、阿生与阿娇)中,阿海、水旺、阿生均被抓,老渔民余满舱和他那刚17岁的儿子余添贵父子也一起被抓,村民谢番薯为了躲避抓壮丁,用菜刀剁掉可以扣枪板机的食指……一场兵灾悲剧就这样发生在这个东海渔村,并绵延了半个多世纪。被抓到金门当兵的阿生为了兑现对阿娇许下的“第二年回来插秧”的诺言,趁夜色下海准备逃回铜山不幸被抓回,当作逃兵被枪决,阿娇闻讯消失于望夫崖;余满舱、余添贵父子被抓到大担岛当兵,经过比较周密的策划,找到两个可作漂浮工具的篮球选择适当的时机下海,但游到半途中一个篮球被海浪冲走,余满舱把承载着生存希望的惟一的篮球让给儿子,葬身于大海,余添贵回到家,在家翘盼的母亲婉儿婶难于承受这个巨痛,一个月后病逝;水旺和阿巧的故事可以说是悲喜交集:1953年7月,水旺随“反攻大陆”的国民党兵回到铜山,曾偷偷回家和阿巧相聚一夜,有了女儿明月。后来,他在台湾数十年不能回来,回到铜山时,阿巧垂危,不久即病故;小说的男主人公许阿海的经历更为跌宕曲折,他也曾于1953年7月随“反攻大陆”的国民党兵回到铜山,但由于种种顾虑,夜过家门而不入,只把阿螺临别时送他的信物平安扣挂在门上。回到金门后,在实弹演习中受伤,转台治疗后退伍,流落台湾数十年,他先到阿里山落脚,为逃避高山族姑娘阿彩的爱情,又跑到台北的妈祖庙当义工,最后还是回到阿彩姑娘的身边。而阿螺却只能留在钵头村“红妆守空帷”,虽有过几段感情,却终未成家。最后,阿海携阿彩回到钵头村探亲,三方达成谅解,遂成“一道海峡,两岸是家”的风景。
小说以铜山钵头这个东海小渔村三对青年男女由于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而分隔两岸的命运为主线,讲述了他们多达半个多世纪悲欢离合的故事。当然,小说还以相当的篇幅讲述了以许阿海的弟弟许阿义为代表的铜山党政领导反特以及制定、执行“兵灾家属”政策的故事,还有关于妙山妈祖庙菜姑林月乡在海峡两岸不通邮的情况下奔走于台湾、新加坡与铜山之间,为两岸传递信息的故事。小说终卷时,代号“章鱼”的暗藏特务白修德被破获后经改造成为研究谱牒的专家和政协委员,在阿海携阿彩回乡探亲时出现于渔村,当年在金门宣判阿生死刑的军事法庭法官陆子明捧着阿生的骨灰盒到铜山谢罪,这两处笔墨也堪称意味深长。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山岛寡妇村的素材曾被许多作家艺术家关注过,也出现过不少以寡妇村为题材的各种样式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但像《平安扣》这样具有较高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长篇小说还是第一次读到。对于发生在将近70年前东海渔村的这场兵灾,小说不是为了展示和撕裂这段伤痕,而是为了抚平这段伤痕,为了展现海峡两岸那隔不断的亲情。因此,我们可以把这部讲述半个多世纪以来东海渔村兵灾故事的长卷看作是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呼唤。仅就这一点,《平安扣》就值得广大读者的关注。
除了上述生活切口小、主题开掘深且放射大这一特色和长处外,《平安扣》另一重要的特色是虚实结合,作者善于把纪实与虚构两种写法融合在一起。如何从纪实走向虚构,并把虚构与纪实两种笔墨融合在一起,一向是依靠采访进入虚构性的小说创作的一个难题。吴玉辉虽然是东山人,但铜钵村的兵灾发生时,他尚未出生,后来又外出工作,他也是靠大量深入的采访进入《平安扣》创作的。他在创作中比较好地处理了纪实与虚构的问题,小说的大框架和背景是纪实的,诸如1950年5月10日晚发生于东山岛的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抓壮丁事件,1953年7月中旬痛击来犯的国民党军队的东山战斗,东山党政领导改“敌伪家属”为“兵灾家属”等等,都是纪实的。而关于钵头村三对青年男女由于受兵灾之害遭受长达半个多世纪分离之苦和家破人亡之痛的故事,其人物、情节都是作者在大量深入采访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概括虚构的。就这样,纪实的大框架和背景、虚构的人物与情节,再加上动人的、耐人寻味的细节描写,为我们讲述了一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兵灾故事,当然,也为他的同行积累了解决由采访纪实进入虚构创作时所面对的虚构与纪实融合这一难题的艺术经验。
我还十分赞赏小说中关于东海小渔村生活氛围和民俗风情的描写,以及通过插入歌谣、俚语和适当运用方言表现地域文化这一鲜明的特色。小说开卷时描写阿海等青年渔民在月牙湾拉山网,阿螺躲在沙丘的龙舌兰后窥视的生活画面;小说终卷时写阿海携阿彩回到渔村同阿螺团圆,阿螺登上妙山把平安扣扔进大海而妙山上钟声悠扬的场景,不仅充满生活气息和诗意,也表现了人民对美好的和平生活的企盼和赞美,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小说中关于婚庆礼仪的描写,诸如新娘“挽面”、坐花轿、“新娘桌”上的十二碗、“说四句”等等,还有婉儿婶唱“歌册”,都有浓浓的闽南民俗色彩;小说中插入的不少歌谣,诸如阿巧唱的《五更鼓》、何水旺唱的《望春风》、阿螺唱的《阿兄》,都是用闽南话唱的歌谣,它们不仅强化了作品的民俗色彩和诗意,而且深化了作品的主题。而无论是民俗风情的描写,还是歌谣俚语的插入,又都可以表现东海渔村的乡愁,强化作品的主题与艺术魅力,是值得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