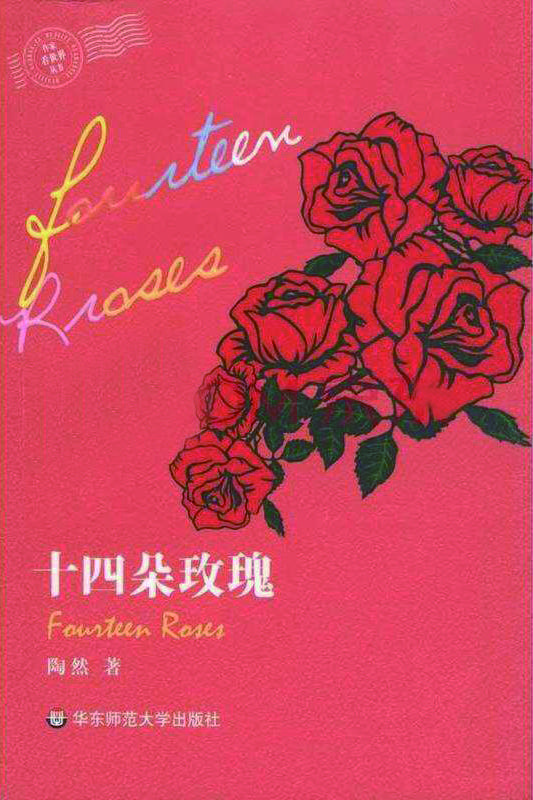文坛常青树
陶然是文坛的常青树,他主攻小说,兼顾散文和散文诗,可谓著作等身。我对陶然的认识,先是读其作品,其后才见本尊。
陶然在一篇文章中说:“已经几乎不记得是怎么认识袁勇麟了。隐约似乎是20世纪初在汕头开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吧,会议已经曲终人散了,在酒店等候出发前,我走过北师大师弟李安东的房间,他那时开会一向和袁勇麟同房,被他叫住了,于是便进去闲聊。其实之前,应该早就相识了,只是较少接触。而他跟李安东是复旦大学潘旭澜教授的同门师兄弟,自然感情颇佳了。那回,预定的汕头—香港直通巴士有点阻滞,临时要改票,勇麟和安东当机立断,陪我去换票。我还记得,巴士站在另一头,我须乘上小车驳巴士去,他们送我上车的情景。”这些细节我已忘记,难得他记得如此之清晰。
我除了选编出版《陶然研究资料》,也撰写过几篇与他和《香港文学》有关的论文,在一些学术研讨会或刊物上发表。如《捕捉都市灵魂的悸动——评“香港陶然新概念小说”》《散文的多元化与开放性——以2000年至2007年〈香港文学〉为考察对象》《漫游记忆的情怀书写——评陶然的散文新作〈街角咖啡馆〉》《从〈陶然研究资料〉谈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等,2018年6月29日,我参加在香港文学出版社深圳读书会UNI空间举办的“陶然作品读书会”,发表《香港有陶然》的演讲。活动由《香港文学》总编辑周洁茹主持,一同演讲的还有秦岭雪、凌逾。我介绍了自己对陶然身世的了解,并从《别离的故事》引出他的写作,凌逾的研究生霍超群参加了读书会,写下了生动的观感:
陶然老师还是像以前一样安静,话不多,独坐一隅,但有可能他正侧耳留心身外之物,捕捉新的文学灵感。从福建来的袁勇麟老师则非常通达健谈,与陶老师一热一冷,相映成趣。
我认为,出版于2015年6月的小说《没有帆的船》最能集中体现陶然40年的社会思考与创作流变。从创作于1974年的《冬夜》到2014年的《芬兰浴》,从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到微型小说再到闪小说,内容丰富多彩,手法多有创新。陶然的关注面很广,从移民、九七回归到都市批判、怀旧等等,都纳入其思考的范畴,呈现出两个最主要的写作面向:冷酷的世情与隐喻的爱情。而随着时代发展,陶然不断改变小说形式,其经典改写、意识流等手法的创新与应用,亦值得注意与讨论。纵观陶然40年来的小说创作,无论在题材开拓还是艺术形式创新上,都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热爱与不懈追求。自然,在香港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这样的热爱与追求何等艰难,而陶然的坚持来自于“我依然相信,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文学的城市,经济再发达,也还是贫血的城市”。
从陶然的散文可以看到,他在用心灵的眼睛观察生活表象,用灵魂的温度感受生命本真的坚持中,逐渐成熟、圆融,最终达到淘洗浮华的境界。散文集《街角咖啡馆》付印前,他曾邀请我与董桥、郑明娳一同为该书写推介语。我写到:“在厌倦了喧嚣璀璨的声色光华之后,当代人纷纷调转头来追逐澄净质朴的自在天然,但不知有多少人能像陶然那样,把自然当成一种人生态度和生命状态,不管辗转游历了多少变幻风景,亲身体会过几许世事沧桑,都不会被岁月冲刷纯真的向往,也不会被时光磨平感触的敏锐。他的散文删去了曲折离奇的情节、摈弃了惊心动魄的悲欢,在细碎琐屑的市井人生里分辨是非,在平凡拥扰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感动,这种成熟浑然、从容大气的意境也正是自然天成的真义。”
资深的编辑家
陶然不仅是个勤奋的作家,也是一位资深的编辑家。正如痖弦先生在2018年1月底写给陶然的信中所指出:“《香港文学》17年,兄的建树甚大,将来文学发展史上,样样都会记下来,功不唐捐。且我发现你在烦劳的编辑生活中仍不断有新作,文章著作,质量都好,这非常不容易。17年不算久,还可以再发挥,由于不影响你的创作,可以把编务和自己的创作视为车的双轮、鸟的双翼,并而行之,以竟全功。”
陶然早在1985年就参与了《香港文学》的创办,并担任过半年的执行编辑。2000年7月,他继刘以鬯之后任《香港文学》总编辑,他在8月20日所写的《留下岁月风尘的记忆》,作为刊首语发表于《香港文学》9月号。他说:“《香港文学》改版了……改版,并非出自空中楼阁,《香港文学》自1985年1月创刊,已逾15年,在刘以鬯先生的坚持下,本刊已成为香港文学杂志的一个品牌;这个基础,成为我们承接的条件。继承之外,也还要跟着都市节拍发展,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够获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他特别强调:“作为一本文学刊物,我们极端重视创作,与此同时,也不忽视评论。没有具创见的评论的推动,创作难免会有些寂寞,而且也难以总结经验、开创前路。”“对于有影响的作品不流于捧场,对于值得商榷的问题提出中肯的批评,当中的分寸如何掌握,难度颇高;但我们当会尽力而为,倘若多少有些参考作用,便于愿已足。”在刊物版面极其宝贵的情况下,他每年坚持推出文学评论专辑,他在2005年11月号的卷首语《更与谁人评说?》中写到:“我们深知,有穿透力的文学批评,对于创作者何等重要,即使往往可遇而不可求,但大家都不放弃。”
香港文学缺少评论,原因或如《香江文坛》主编汉闻所指出:“这一方面因为能提供发表文学评论的园地寥若晨星,另一方面写文学评论容易开罪人,业内人碍于情面,也就懒得动笔。这种现象导致……文学评论成了香港文学薄弱的一环。”正是出于对评论的重视而在香港又不容易找到作者,我和内地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便经常受邀撰写相关论文,渐渐成了《香港文学》的作者。我第一次在《香港文学》发文是《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再思考》,刊载于《香港文学》2002年第10期,从此开始与《香港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十几年间发表了30余篇评论文章。曾当过台湾《联合报》副刊编辑的诗人陈义芝,深知办好一本文学刊物的不易,他特别夸奖陶然:“重视文学批评。主编者再三表达批评有助于文学交流,‘批评与创作,是文学的双翼’,期望创作与评论良性互动,‘使各种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得到及时有效的评论’,引导初涉创作的人进窥文学经典的堂奥。陶然欣赏形式活泼、自有见解的品评,亦感慨有穿透力的批评可遇不可求,更点名散文评论薄弱,期望众声喧哗。”
热爱生活的人
陶然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只会埋头书斋写作的人。他喜欢旅游,经常利用参会时机饱览中外大好河山,真正践行了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这些年我与他结伴,走南闯北,除了国内各地,其他如韩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地也留下了我们共同的足迹。
陶然祖籍广东蕉岭,因为他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香港内外》是1982年6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常被误认为是福建人。不过,他确实跟福建有缘,像他的文学领路人蔡其矫就是福建籍诗人,而香港闽籍诗人兼书法家秦岭雪、出版家兼学者孙立川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其余如福建学者孙绍振、刘登翰、诗人舒婷等人,也是他的至交好友,孙绍振教授有篇评论甚至直呼《陶然,变“邪”点!》。
我陪他走过福建不少地方,如福州、漳州、泉州、宁德、南平等,陶然在许多散文随笔中写过福建的山山水水,记录了我们之间真挚的情谊,他或直书我的名字,更多时候常以我姓氏的第一个字母“Y”指代我。“航机降落在华灯初上的福州长乐机场,海关外人群中,远远就见到Y在挥手,含笑,我却知道他等了许久,只因为航班迟飞”(《悠然走在山水之间》);“临别那晚,Y在酒店西餐厅设宴,意大利餐,最后一道甜品是雪糕,我的最爱。S在旁边议论横生,纵横睥睨,但食欲普通,他笑说,晚饭不能太饱呀!饭后送他们上车,我们百步走,随意走到温泉公园,想要重温那歌舞之夜,但公园里静静,有几滴雨点飘下来,竟不见跳舞的人群,也没有歌声飞扬。有点失落,恰如即将离开的暗夜心情”(《有福之州》)。
关于国外同游经历,也有十几次。最早应该是2008年9月20日,我与陶然、也斯等人,应朴宰雨教授邀请,出席在韩国东国大学庆州校举办的第十届韩中文化论坛。对于这次韩国之行,陶然说:“记忆深刻的是,安东、勇麟和我在酒店咖啡座太阳伞下喝咖啡。”朴宰雨先生惊悉陶然去世消息后,在微信朋友群里写道:“2004年初识,一起爬泰山同房住。后来在香港见面好多次,跟也斯与金惠媛喝酒。2008年来韩国,跟香港也斯和金惠媛,瑞士洪安瑞,意大利达德,芬兰高歌,中国袁勇麟、韩国严英旭等一起爬顺天曹溪山仙岩寺。”当时我和也斯、陶然在旅途中经常因为内地和香港的关系互相打趣,一路欢歌笑语,甚至在朴宰雨的导演下,连平时斯文万分的陶然、也斯,也跟我们一起跳起来,摆出腾飞的造型合影留念。在酒吧里,我们三人组成“中国队”,与东道主“韩国队”和远道而来的“欧洲队”比拼,我第一次领教了韩国“深水炸弹”的喝法,在一大杯啤酒里放置一小杯白酒或洋酒,端起来一口闷。
2015年3月23至28日,我与陶然赴印尼棉兰,出席“从郁达夫看一带一路给印华文化与教育的动力”研讨会。印尼是他的出生地,近乡情更怯,我们来到多峇湖,住在萨摩西岛,这里的一山一水都让他回想起少年时光,“但见稻田中央立着几个稻草人,还挂着铃铛,当风吹过,铃铛响起。噢,那是赶鸟用的,小时在万隆的稻田里我也见过”,“朦胧中我又好像回到那久违的热带地方生活了”(《梦幻多峇湖》)。
外表严肃、内心幽默
陶然是一个善良且乐于助人的好心人,国内研究香港文学的学者许多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而我更有切身体会,几乎每次到香港开会,他有三件事必办:一是只要他身体许可,不管刮风下雨,一定会到机场来接我;二是知道我在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研究,常常利用会议闲暇时间陪我逛书店淘旧书;三是安排我与秦岭雪、孙立川见面餐叙,大家坐而论道,谈文说艺,其乐融融。
我曾在《书香墨影里的香港》一文中,记述了陶然陪我淘书的经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苏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杂文史论》时,承蒙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玮銮帮我在旧书店里觅得《七好文集》《三苏怪论》等图书,获益匪浅。后来有机会到香港开会或途经香港时,我请陶然带我到那些早已耳熟能详的旧书店,它们往往散落于街边巷尾,在繁华都市,独守一片清闲。
最新一次他陪我淘书经历是2018年7月8日,我应香港公共图书馆的邀请,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与陈智德、黄念欣一起主讲“文学的成长叙事”,我谈的是曹文轩《草房子》的成长书写。陶然特意前来旁听,并给我带来了所要的图书。会后又帮我一一打电话确认几家二手书店的地址和营业时间,他还迈着沉重的步履,陪同我走访森记书局、乐文书店、梅馨书舍、序言书室、田园书屋等书店,那次我购买了台湾《中副50年精选》、刘克襄《随鸟走天涯》初版本、焦桐选编的《八十六年短篇小说选》等。
不仅是我,连我的学生都感受到他的热情待人。在得知陶然不幸猝逝后,我的研究生吴海燕回忆道:“去年香港匆匆一见,陶先生与我们师兄弟几人相谈甚欢,我还留了一本北岛的书,请他帮忙签字,他爽快答应了我,说经常会见到北岛,只是那段时间北岛在云南度假,我还打趣说陶先生比较忙,可能会忘记。他笑着回复说,你以为我老了吗!”
陶然是一个外表严肃、内心幽默的人。陶然常给人严肃的印象,尤其是朋友聚会时,他常常静默少语,他自己也说:“我性格如此,而且自知并无高见,每遇有高明谈古论今,我总愿意做听众的角色,以增见识。其实朋友见面只是为了友情氛围,话多话少不是问题,所谓尽在不言中。”
他性格安静,但有时也会跟我们到KTV狂欢。2007年12月10日,在暨南大学出席“曾敏之与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当晚参加完曾敏之先生90寿宴后,陶然、曹惠民、凌逾和我等几个朋友意犹未尽,到天河东路155号K歌王唱歌。虽然他只是轻唱一首,便静静地退到一旁听歌,却很仔细观察我们每个人的神态,并在事后撰写成文《广州夜色》:
那晚人们脱下了教授的光环,还原本色,大帅表演童真,动作狂放;OK也不甘示弱,与他构成互动画面;连C也手舞足蹈,狂歌当醉。只有L依然安静地唱,唱出了让举座惊叹的动人歌声,原来是真人不露相,一露相便把人们镇住了!有时人在不经意中才能露出真性情,这种毫不修饰的率性,有不设防的纯真,我们又回到了从前。
陶然幽默的一面在2002年11月11日发给我的电邮中更是可见一斑:“坏孩子勇麟博士后:望成了长颈鹿,以为如你会前在福州信誓旦旦所说的那样:衡山路见!哪里晓得坏分子只顾和美眉厮混,坏了哥们儿义气,不但咖啡喝不成,连人影都不见!下次狭路相逢,须吃洒家一刀,方解心头之恨!”他说的是2002年10月27至29日,出席复旦大学主办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期间,我们事先相约到衡山路喝咖啡未果一事。起因是那年5月17日,陶然来闽参加福建作家协会、《台港文学选刊》和福建画院合办的“秦岭雪诗集《明月无声》研讨会”,住在福州西湖宾馆1号楼204房间,我18日中午去看他,获悉他前晚钱包失窃,还好深夜被人“捡到”,只是里面的港币和人民币都不见了,证件和信用卡俱在,是不幸中的万幸,不然回去乘飞机都成问题。为了表示东道主的歉意,我答应10月到上海开会时请他喝咖啡,不知为何没约成,留下一段回忆。
千古文章未尽才
自古多情伤离别,3月9日晚从秦岭雪、周洁茹、赵稀方的微信和凌逾的电话中,相继得知陶然去世的消息,我如五雷轰顶,忍不住失声痛哭,人一直恍恍惚惚,不相信这一事实。因为千古文章未尽才,陶然还有很多写作计划等待完成。
陶然跟我说过:“我想重新拾回在前几年福州世华会议上与花城社长谈好的长篇,拖了多年。詹秀敏叫她手下一个人,跟我联系,要看书稿。我才写近三万字,须赶写。”2月26日他又告诉我:“林滨说,‘昨日纪’下半年拟列入出书计划。这‘思想起’,也是你的思路,希望写成万隆、北京、香港的文学回忆录性质的一本书。”
去年在槟城,我曾把他在《文汇报》的“昨日纪”专栏推荐给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林滨副社长。“思想起”则是今年他新开在《大公报》上的专栏,开栏之前他告知我,专栏两千字左右,每周四刊出,并与我商量专栏名称和内容,我建议他写文学生涯的回忆录。此外,林滨知道陶然与蔡其矫先生交往多年,在蔡其矫的直接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陶然与蔡其矫的文学交往、人生交往,是蔡其矫文学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真实、全面地挖掘与记录他们交往的时代变迁和文坛风云,以及对文学理念的探讨、对艺术人生的追求,可以丰富蔡其矫的研究资料,增加读者对蔡其矫的认识、有助于研究者对蔡其矫的深入研究。他特意约陶然写一本关于蔡其矫的书《我与诗人蔡其矫》,书已交稿,也还来不及出版。
在天人永隔之后的几天里,我还陆续收到他生前从香港寄来的两箱图书,睹物思人,情何以堪!林岳桦安慰我:“老师,正面来思念陶然老师,其实他是有福之人,生前没有受苦,还可以天南地北到处去旅游,时间到了,他离开我们身边,但是相信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虽然不舍,还是要接受,大家互相勉励,好好照顾自己,珍惜当下。”这使我想起陶然在2015年1月17日所写的《痛别——悼曾敏之》中的最后一段话:“如今,曾公走了,据说是在睡梦中安然离去的,有些突然,但走的时候应该没有痛苦,这又值得安慰。回望曾公一生风雨,无愧人生,是凡人,是长是短,终有一天要离去,曾公离开我们,虽然痛心,但他留下的精神,却让我们永远缅怀在心间。”我想这一段话也可以借用来代表所有人对陶然突然离世后的感受。
陶然兄,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是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