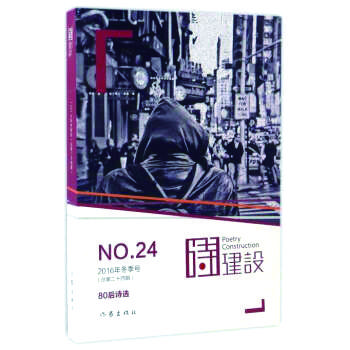出场与标准
金理:今天我们讨论的诗歌文本来自于《诗建设》2016年冬季号(总第24期)上“80后”诗歌的专辑。这组“80后”诗选体量太大,两位主发言人蔌弦(林诚翔)、王子瓜(王玮旭)经过筛选后缩小了阅读名单。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两位主发言人根据他们的视野所挑选出来的诗人,和耿占春先生在专辑点评文章《八十年代诗人:原始场景、对话与论述》里所评点的诗人,几乎没有重复(交集好像就只有包慧怡)。面对“80后”诗歌这一共同对象,前辈与两位“90后”入手路径几乎完全不同。
簌弦:我们所谓的“80后”诗人通常在本世纪的最初10年开始写作。对于刚开始写作的“80后”诗人而言,前人的作品一方面加速了他们的成熟:师法前辈的技艺无疑是一条捷径;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他们对话的对象:如何完善、突破前人开创的传统,乃至寻求别样的资源以谋划新的路径,都是他们必须面对的。
我们一共挑了10位诗人,诗人彼此间的差异相当明显,各自的面目都比较鲜明。王璞可以说是在北大诗歌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研究者,他的诗歌形式多样,无所不包,但不囿于内在自我,而是始终在文本中呼应如火如荼的当代生活。
包慧怡和茱萸也是学院环境所孕育的诗人,阅读、研究是他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构成了他们写作时的重要资源。包慧怡的研究领域高度专业化——中古英语头韵诗及8—15世纪手抄本,同时她又是一位高产的译者,已出版十余种译著,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她作品中异域文化的滋养。茱萸是青年一代中具有丰厚古典文学修养的诗人,他最为重要的作品展现了重新检阅汉语的文化抱负以及对形式感的极致追求。某种意义上,包慧怡和茱萸构成了微妙的对称。
了小朱是一名飞行员,他拥有伸缩自如的诗才,能够将绝妙的想象与独到的形式妥帖地整合起来,实现某种愉悦的均衡,值得大家细读。郑小琼则是务工诗人这一群体中较早受到关注的一位,希望以她为突破口窥探工人诗歌更多的可能性,观察她的写作溢出“工人诗歌”的部分。
王子瓜: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一个好的诗人,至少要对他所操持的语言十分熟悉,才谈得上表达和创造。语言若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冗余和套话,展现它的灵巧自如,维持特有的内在气息、节奏,就可以称得上是纯熟了。关于修辞,最主要的就是隐喻,诗歌中的隐喻是否新鲜而合理,在此基础上是否能做到开阔和精确,事关诗人对现实的体察和对神秘的领会。诗的阅读必须回到经验。我所选出的5位诗人大体符合上述标准,其中肖水和洛盏是很早以前就熟悉的,安德和钱冠宇虽然也曾读过但还没有见过面,张二棍则是此前从没读到过,这次读后觉得是很好的诗人。
晦涩,或碎片重组
王子瓜:安德的诗整体弥漫着一种荒诞和冷酷,经常出现的是“观察”“猜”“雪”,这些都涉及诗人处理现实的方式和核心关照。《深海恐惧症》的“鱼肉闻起来像电池”,指向工业、资本对生灵的入侵;“扎啤”“咯嘣脆”这样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市井词语,“潜水员”“压力计”等更富现代感、技术感的词语,也都标明了诗人的感受力取向。有时语言过于节制了,会让诗的晦涩走向极端,比如《罗马假日》一诗,每一行你大概都能够明白诗人的意思,但是不能理解行与行之间的逻辑,因而不能对整首诗有准确的把握。我觉得这是他风格的一个极端。
金理:《罗马假日》对没有诗歌阅读训练的读者而言实在很晦涩。其实我大致能理解晦涩在90年代诗歌生成语境中的意义,那个时候诗人与真正的市场化初次短兵相接,外部现实急剧的动荡,会促使诗人回返内心世界,在其中反复进行修辞锤炼,由此造成某种私密、不可解的面貌。但这种“不可解”,置放在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中其实是“可解”的。但“80后”诗人与其所身处的当下,已不复当年的对立、对抗,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撕扯,在这种更趋复杂化的含混中,如何来理解晦涩呢?
王子瓜:安德诗里的语言游戏,比如谐音词的戏谑,一些句型的变换和重复,涉及到诗歌的音乐性问题,这也与诗歌的写作意图有关,诗可以着力于对语言的丰富或者对音乐性的探索。除了形式和内容上对中国古典的借用,他还使用了很多关于西方的东西,比如尤利西斯、帕涅罗帕、本雅明等等,这是一种具有互文性的写作。
洛盏:安德对心理学、对拉康特别感兴趣,他对潜意识、小他者、欲望唤起机制等很关注,并能将其内化成诗歌的一部分,同时一些物理学、天文学素材也可以进入他的创作,并成为其创作的动力点。
簌弦:现在写诗的群体相当多元,大家的知识背景各不相同,可以依凭的东西也很多。不少理工科出身的诗人都喜欢以技术性词汇入诗,这类专业词汇激发的想象很容易与诗歌精巧的构造相互呼应,给读者带来新鲜感。
徐铭鸿:安德的诗有意地将连贯的事件进行拆解、重组与架空。相对连贯的事件经过如此的结构处理,呈现出错落驳杂的效果。或许它们更侧重视觉角度感受,这里所谓的“视觉”不仅需要适应顺序的语句、段落与词的跳跃和组合,还需要去勾连段与段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的关系。《罗马假日》似乎可以将每一段的两行分开来读。四个第一句相连,“隐形”“埋下”“变色”与“精装”,我把它们当做一条关于“掩埋”与“变形”的线索。而每一段的第二句,“晚来”“袒露”“旧书店”“归来”“乡船”“疏松”与“死星地图”,我把它们当做一条关于“坦白”与“复原”的线索。罗马假日广场由一群欧式建筑组成,而内部售卖的主要是古玩商品,店面中也不乏服饰、小商品、足浴等等。照片中的广场人头攒动,地摊遍布,典雅的欧式建筑外墙和熙熙攘攘的活动场景糅合出一种颇为诡异的市井气息。结合罗马假日广场的实景图,《罗马假日》可能是安德在时间穿梭中产生的一种迂回的感怀。
古典文学的资源与限度
簌弦:茱萸是很自觉地动用古典文学资源的诗人。在两首他自创的“谐律”中,《谐律:路拿咖啡馆》里有15处谐音,《谐律:译李商隐〈北楼〉诗》则多达18处;“谐律”之“律”有律动和律法之意,大家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律诗,茱萸的谐律均为8行,在规格上确有效法律诗的意思。汉语里很多同音字词,因而借助谐音来拓展语义容量、关联不同事物,都是很常用的技法,同时谐音运用得当的话,还能带来回环反复的音律之美,这几点在茱萸的谐律里都有很好的呈现。举个《谐律:译李商隐〈北楼〉诗》里的例子:“抑郁突燃,如何扑救?异域的/风情,舞断的腰身或无端之蕊?”“异域”似乎是“抑郁”的缘由,“突燃”似乎是“徒然”之举,“谱就”新曲纵能“扑救”羁泊之愁,也奈何不了花朵“无端”飘坠,如宫腰“舞断”,而这又似乎是对《北楼》中“花犹曾敛夕”一句的再书写。
茱萸的“谐律”尝试固然新颖,但也存在问题,毕竟既要保证语意通顺,又要兼顾谐音,处理得不好的时候显得过于生涩,可读性不强。其实一个便捷的做法是减少谐音,在诗意与音律层面下更多功夫,当然,茱萸本人可能对这种诗体试验的“难度”有更高的追求。
金理:在取法古典资源这一方面,除了茱萸之外,我觉得钱冠宇也比较有代表性。不过两者不同。茱萸好像更多还是形式上面的考究,钱冠宇的诗歌虽然有怀古的外貌,但他表达的主题——孤独、零余、自我分裂,其实非常现代性。
王子瓜:钱冠宇未被选入的《夜晚的蜘蛛》是一首成功的短诗,精巧、完整、没有冗余,腾挪空间也很大。总体而言,钱冠宇的诗并没有特别成熟,但这样的尝试是值得继续的。
簌弦:除了钱冠宇,还有很多人写故事新编式的诗,近年来这类作品的大量涌现可能和一代人生活上的单调有关,大家似乎想要表达,又无话可说,于是纷纷到历史中寻找书写的题材,寻找思绪的载体。当然我不是说这种写法不可行,这条路上有成功的先例,但很多时候给人一种硬写的感觉,而且也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套路:往往是从历史中发掘出一些契合现代性体验的故事,将故事的主角置换为现代的抒情主体,由此完成一首兼具古典与现代色彩的抒情诗。这类故事新编其实并不“新”,比如40年代沦陷区的校园诗人吴兴华就写过不少这样的诗,且在音乐、语言、形式层面都近乎完美,然而即使是在40年代的环境里,也很难说吴兴华的创作是绝对超前的。
比喻与叙事
王子瓜:洛盏的诗代表着对经验进行精确把握的一种诗,在写法上他也很跳跃,但不会在不必要的地方跳跃。洛盏的诗像一把刀在划着纸,有一股强大而内敛的力量。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豆豆》这首。
丙杰:洛盏的那首《父亲》其实不能打动我,感觉有些修辞是故意用的,阻碍了情感表达。洛盏有一次在微信圈写了首比较传统的诗歌,主题也是怀念父亲,应该是草稿,但情感真挚。当真情实感冲击自己、需要表达的时候,修辞反而常常阻碍情感的表达,这或许是他的困境。要突破这个困境,或许正需要放下习惯了的东西,勇敢面对真实的自我,袒露真实的自我。这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而这或许不只是洛盏面临的问题,而是“80后”诗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邱继来:洛盏诗歌的叙事性很强。在紧密连环的意象中导出诗歌形式的叙事,甚至危险地徘徊在散文体的界限附近。就以《豆豆》为例,描绘的对象、叙事形态、意象连贯性是一环扣一环的。他和安德正好是两个极端,采用散文的叙事形态却保持了诗歌的语言,就白话文的形式而言,这是非常难得的。
金理:谈到诗歌的叙事性,我们不妨来聊聊肖水,他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尝试。
王子瓜:肖水最近写了很多“小说诗”,这个概念很容易受到质疑:小说和诗怎样糅合在一起,为什么不是叙事诗而是小说诗?他对此有自己的想法:小说诗不是小说也不是诗,叙事或诗意都不是它的核心,关键在于它是将诗和小说都还原为“写作”,他不想以文类概念限制写作。肖水显然进入了新的探索阶段,在自己的内部寻找着突围。对小说诗的尝试才刚刚开始,还有待展开和积淀。
簌弦:所谓“小说诗”就是跨文体写作吧,20世纪以来读者已经接触过很多跨文体写作的文本,我觉得大可不必再提这样一个说法。肖水的“小说诗”我读得不多,读完的更少,好像没有特别触动的地方。就讨论材料里的《渤海故事集》《南溪乡》等诗而言,题材主要为都市情感故事,个人感觉叙事上略显滞重,当然肖水可能是有意为之吧。
邱继来:这样的实验如果需要作者自身来解释,我觉得这就够不上一种好的方式。我会保守地认为这些抛弃意象而以叙事展开的诗歌已经走出了诗的领域而变成散文,而且这个散文并没有诗的语言和意象,并没有构成散文诗的必要要素。
丙杰:从呈现出来的诗作来看,尽管有许多问题,比如诗歌结构、表达方式、诗歌主题的重复雷同,在用诗歌展示故事方面,也没有达到一种普遍的成熟。但是,我还是很高兴看到肖水的这些尝试,而且有些尝试已经达到了他的初衷。比如《手工联社》《边界天光》等诗作。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边界天光》:
她第三次从金州戒毒所出来,家人没有再出现。
她走了很久,才走到主干道上。后来,她和顺她回城的货车司机
结婚生子。当然,故事并没有那么简单,人们被继续要求不能
随意横穿马路,也继续被要求:在年轻时候,不要爱上一个英俊的坏人。
这首诗包含的故事很容易被叙述:“她”因为“爱上一个英俊的坏人”,在情感受挫中接触毒品,三次被送进戒毒。在青春的挫折中,她不只被爱情打击,也失去了亲情的关爱。最终,“她”在一无所有的途中,与“顺她回城的货车司机”结婚生子。这个故事可以理解为失足女子最终走入人生正途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个体无法把握命运的故事。我想,这个女孩一定承受过人世间的冷暖伤痕,也许在狱中认清了现实,放弃了爱情中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走向了“结婚生子”的所谓“主干道”。“她走了很久,才走到主干道上”,说明她第三次走出戒毒所之后,努力回归生活常态。走向人生的主干道,与随后的“结婚生子”,两者看似顺理成章,但一个“顺”字,打破了这种惯性的理解,使得这个女子走向人生“主干道”的行为有了更多复杂的况味,因此这个词包含了太多的想象空间。
在我看来,诗人在这首诗中体现出来的高妙之处,不只在于通过一些特殊的词拉开叙事空间,比如,“第三次”“再出现”“主干道”“顺”等词,省略了太多的人生故事和心灵体验,让一首短诗承载了一部话剧、一部小说可能包容的故事能量,更在于,在这首诗的最后,诗人让这个故事在形而上的层面得到了提升,从而摆脱了单纯结构一个故事的技术操练。这首诗最终指向的,就不只是对人类道德伦理合法性的思考,也指向对命运强大的沉思。这样的结尾,让我想到张爱玲《金锁记》中写的那样:“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但是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肖水用如此短的诗歌构筑这样充满厚度、长度和张力的故事,足以看出肖水在叙述能力上的用功。
簌弦:我觉得这些大概谈不上新鲜,一首诗做这种程度的延伸都不会太困难。
丙杰:这句话说来简单,真正落实起来并不容易。反而很多情况下,我们正淹没和迷失在修辞的快感当中。海子在1988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说:“从荷尔德林我懂得,必须克服诗歌的世纪病——对于表象和修辞的热爱,必须克服诗歌中对于修辞的追求,对于视觉和官能感觉的刺激,对于细节的琐碎的描绘”,“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
如果总览肖水诗集的话,可以发现,肖水并不是不会修辞,甚至可以说,肖水最敏感、最擅长的,恰恰就是修辞(在此推荐肖水的短诗《桥上》),而他不擅长的,恰恰是叙事和故事的构筑。但我觉得可喜的是,肖水对于自己的诗歌成绩时刻有一种焦虑,一种自我反思和警惕,他一直在寻找一种内心更渴望的东西,在此推动下,他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挑战自己已有的成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诗的尝试,正是积极突破自我的一次实验。他说过,《世说新语》《聊斋志异》这两部古典小说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让他沉迷其中,也希望从中汲取新的营养。在我看来,《世说新语》的特色在于,在短篇制中,通过一言一行展示人物个性;而《聊斋志异》则擅长在短篇幅中,结构故事,营造超现实氛围。或许,这恰恰是肖水倾心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这部诗集有多少失败的半成品,只要有一首诗歌达到了他的目的,我觉得都是值得鼓励的。而且,他敢于展示自己最新的尝试,不论这种成果是否成功。这份坦然,是一种自信,也是在诚实面对自我。
修辞
簌弦:既然今天洛盏也在场,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很多同代人看来,你的诗应该很早就在技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这几年似乎写得很少,是否遇到了瓶颈?有没有考虑过未来的写作进路?是否打算处理一些个人私密情感之外的经验?
洛盏:抽象的概念性的东西,我能感受到它的必要性,但我写东西更接近偏向于语言的物性和感受力。很遗憾我的写作近年来没什么突破,还没有抵达理想中的更复杂的境地。
金理:以这卷《诗建设》“80后”专辑提供的样本为例,我们能否总结出这代人创作上的一些整体性的特征?这种提炼整体性特征的观察方式,对于“80后”而言已经失效?“80后”诗人迄今的诗作中,是否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表达?
簌弦:比如今天我们如何表达互联网生活?
邱继来:或许可以换个方式理解,肖水的诗歌意象已经从图片式的碎片视角转移为影像(短片)视角。这样理解或许能比较明白他所要表达和尝试的东西。从现代性的蒙太奇碎片跳脱到后现代的影像式叙述,就这一点而言,或许更容易理解其内涵,更容易理解诗人和变革时代的关系。
金理:这次集中阅读“80后”诗歌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80后”诗人似乎已经高度成熟,但这种成熟又明显是被学院生活、阅读生活所“催熟”的。我在这些诗歌中看到一张张“很严肃的面孔”,但绝少有散乱、保留着清晨露水的、“刚刚采集的鲜花”。当然,这样的阅读印象也可能和《诗建设》的“取样”有关,我不知道他们选择的依据是什么?这般模样的“80后”诗选,之于“80后”诗歌创作的实存状态,到底有几分覆盖力?
洛盏:我觉得这个选本中大部分是学院里的“80后”诗人,偏向于沉思和技术流。但其实,“80后”最开始是混迹于诗歌论坛的,往往以相互开炮,以暴力、直接的方式交流。他们刚开始写诗的时候,那种有点偏口语经验的、下半身的、一眼能看透的诗反而是主流,但写这种诗的诗人大部分到后来就不写了。而这个选集比较“稳”,质量上乘,技术老道,总体来说比较缺乏一种清新的、料峭的感性和凌厉。
丙杰:我发现今晚对于诗歌的选择和讨论,都是从修辞的角度,从技术的角度展开的。真正好的诗歌,首先不是技术打动人,而是诗歌的情感、思想打动人。刘勰说,“修辞立其诚”。真情流露,正是文学打动人之处。我想刘勰提出“诚”与“修辞”的辩证关系,正与他对于南北朝文学那种华丽的修辞与无诚的内核的文坛倾向有关。从另一角度来看,如果把修辞理解为恰当传达思想和感情的话,修辞最高妙的,恰恰在于“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式的表达。诗歌也一样,用情之处,看似没有修辞,却能震撼人心,这或许才是最高的修辞,最好的表达。
簌弦:我想你说的“没有修辞”肯定不是指没用修辞手法,海子的诗里肯定是存在修辞手法的。按照我的理解,很多写诗的人说一首诗“很修辞”的时候,一般是指它在语言上较为华丽,其实这种华丽很多时候是堆砌了太多无效的形容词造成的,在诗歌中,名词和动词往往更直接有效。
丙杰: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最真实的体验,也有属于自我的独特的表达。文学,正是要聆听自我内部的声音,寻找属于自我的表达,而不是去模仿,更不是把模仿的风气怪在前辈身上。
刚才说到王璞《阶级的黄昏》,这首诗最后一句“我真想冲出我的皮肤跃入你脏兮兮的身体”,放弃了修辞的繁复,而这句恰恰提升了整首诗的品格。“真想”恰恰表达出了“80后”这代人不彻底的个性——有理想的余晖,但没法再为理想而轰轰烈烈去行动。现实的各种牵绊让这代人成为最谨小慎微的一代人。这种个性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表达中。
生活的表面在变,但人类的情感和对生活的体验,仍然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我们能被“90后”后诗人许立志那些泣血之作深深震撼。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写道:“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鲁迅懂得了什么呢?这值得我们思考。
簌弦:不过也不要把修辞的问题神秘化,纠结于要不要修辞没有意义。修辞不是点缀文本的东西,而是托着文本的东西,修辞的最终目的还是更准确、更有新意地表达意思,必要的时候使用合适的修辞就好了。
丙杰:“80后”诗人其实生活在断裂和过渡之中,他们在开始诗歌启蒙的时候,受的是90年代市场经济搅动下风靡市场的徐志摩、席慕蓉、海子、汪国真的影响,而当他们真正冲击诗坛的时候,90年代新的诗歌美学在逐步成熟并压制了80年代的诗歌美学,附带着各种诗歌媒介平台也在接受新的诗歌美学。“80后”诗人在新世纪初出道的时候,“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种美学,已经成了他们最直接的借鉴,但他们内心又保留着80年代余留的抒情情结和理想情怀。这两种心境很多时候是无法调和的。所以,我感觉,真正把修辞作为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写作方式的,不是“80后”诗人,而是“90后”诗人,“90后”诗人所拥有的诗歌写作的无限可能性,恰恰从要修辞出发,“80后”却注定是要烙上过渡阶段的痕迹,他们的成绩也要从这种断裂和过渡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