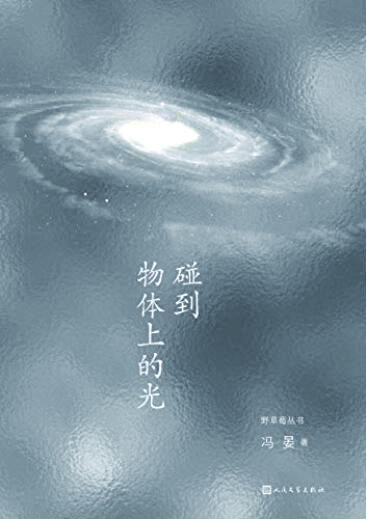光有二象性,或者说双重性格。它是波,也是粒子;是丈量空间的射线,也是测试时间的飞矢;是神的赏赐与启示,也是人的索取与延伸。它带来光明,同时造就阴影;它塑造生活,同时生产文学。冯晏的诗集《碰到物体上的光》所呈现的,便是光从物理到诗学的升华:她的诗穿过日常生活的透镜,折射繁复而纯粹的词语光束。她用冷静却具有诱惑力的声调,唤醒流动的时间、打开延展的空间,逃离密不透光的身体与重重迷雾。这些看似刻意的表达在其诗歌呼吸吐纳间毫无雕饰;她的声音如同“碰到物体上的光,一刹那,/一刹那从无到有,或反过来。”(《碰到物体上的光》)
冯晏似乎与光具有相同的性格,但她并非在事物的两极摇摆,而是兼具两种互异的特性。在她的诗中充盈着“复杂风景”,小到尘埃、缝隙、冬日的“窗口”、“清晨的局部速写”,大至空气、海洋、无限的宇宙、无尽的冥想;她滤除“时间史里的杂质”,“穿越时间”,既重返历史现场窥视“阿赫玛托娃的厨房”,又对话未来如亲历般说着“一百年以后”;她站在真实与虚构的“边界线”,既“复制或模仿”着真实的生活——“万物相聚如空气”(《过年》),“你厌倦了厮守万物与空气共享”(《私人空间》),又收藏或编织“虚构的相处”——“写作是蛇蜕掉的皮”(《一百年以后》),“你揪住真实如去抵达一枚果核”(《虚构的相处》);她的思绪与诗绪既环绕在平实而日常的“室内生活”,又航行在神秘而危险的“百慕大”。她具备女诗人的敏感与敏锐甚至骄傲:“想象天空,如同你穿不了那双/九寸高跟鞋”(《走过九月》)、“给你,口红。我要融入油脂和粉色,/被玫瑰接受”(《在海上》),也不乏男诗人的气量与力量甚至野心:“肺里,我吸入青花水印,/肾里的宇宙,有几颗陨石飞行”(《镜子》)、“你按下生命地理,为此,/你保留永恒和远视”(《航行百慕大》)。性别的成见将成为理解她的障碍;她的诗,更倾向于适用“去性别化”的讨论与阐释。
冯晏的诗浸润着她对宇宙的思考,抽象而空洞的词语在她的诗歌中被赋形,变得可观可感。她企图构建的空间是多维的,无数个光源投射出无数光束,这些光束指向同一个原点,时间是其中不可动摇的轴线。进入诗歌内部,犹如在黑暗的密室中突然打开一扇窗,刺眼的光线充满整个空间,而眼睛无法承受的词语的炸裂已由身体先行悦纳。美国哲学家舒斯特曼认为,“我们的身体边界从来不是绝对纯粹,而是相当疏松而容易渗透穿越的。”如他所言,身体是容纳各种固体、液体和气体的驳杂容器,始终遭受着来自外界的事物的渗透,同时,我们也不断从身体内部将这些物质排出。词语的光线也是如此穿越身体的边界,渗透进诗人与读者的身体,又从身体的内部遁出。诗的国度俄罗斯,埋葬着普希金、契诃夫、果戈里的新圣女公墓之畔,冯晏感受到了词语与身体交织的悸动——词语的光线从发丝渗入身体——“你继续被生活放生,正走在蝴蝶中间/光线点亮头发,黑暗又被减去一寸”(《新圣女公墓》);当她退出旅行、离开网络,回归搁浅的室内生活之时,这种感受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词语从你身体的黑暗中飞出”(《室内生活》)。在谈论诗的格局时,冯晏说道:“写作,为破解词语所蕴含的最小粒子的突变与体力较劲。”对于冯晏来说,词语与空气一样,都是身体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词语不间断地进出于身体之中,写作便如同呼吸。
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身体感受对于提供时间意识的认知是至关重要的,对时间流逝这一现象的感觉,绝不是纯粹持续而无实际内容的感受。在冯晏处,抽象的时间被置换成直观的“光”,时间的流动便是光的流动。她谈论或描摹时间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射到光本身:“分解一场雪,水滴聚集泥土,/日子被还原时,光,间断性移动。”(《碰到物体上的光》)与夏日炽烈的阳光相比,冬季的光是轻盈、安静且苍白的。透过稀薄的氧气,黎明的日光散落雪上,试图将雪花分解成水滴。水滴又将太阳分解成无数个小亮点,折射着微弱的光线,使“剩余感、碎片感遍布视觉”。这是北国之冬独有的景象,窗帘上,光线与冰凌交汇:“光线让清晨像箭一样深入,/通常,箭与日子是平行的。”(《光线》)视线移向窗外,那些柔软的光正轻轻触碰着物体,给予它们刹那的亮色。目光回到室内,那短暂的亮色变得模糊不清,它们光辉的边缘是时间的背面,人们身居于此且深居其中。冯晏记录着幽深的细节——“我的许多朋友都过着幽深的生活/他们用书的镜子照自己的躯体或者骨头/在浮华的事物或肤浅的娱乐中,他们/永远是躲起来的人,就像地图上/不可逾越的一条条粗线或者细线/把世界越分越窄。我也是,无论臃肿/或者清瘦,都不影响成为时间的剪影/去感受光辉的边缘——时间的背面。”(《被记录的细节·深居》)
实际上,将时间与光相联系并非冯晏的专利。在古代,“光阴”表示时间;“时光”一词则更直接地将“时”、“光”并论。冯晏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笔下的“时”与“光”都与身体直接相关、可知可感。她不惧怕时空的失真和未知的探险,在生死未知的神秘航行之中,她依然可以坦然地说出:“时间,一种习惯而已。”(《航行百慕大》)
除时间外,冯晏的诗也通过拟构文本空间以重现真实空间。她在诗中坦露了写作的心迹:“我阅读被编织的红柳,仰望嘴唇筑起的黑色空间。”(《立春》)冯晏诗中的时间与空间是同质且同构的,她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时间不能抹去的,/看来,空间也不能。”(《五月逆行》)永恒而同一的时间被压缩在空间之中,构成了繁复多样的空间,使时空连接在一起的,则是词语的光束和诗人的声音。冯晏认为:“诗句在替自然中那些不被看到的事物发出了声音。”(《诗与自然》)她的诗完成了她的期待,那些微小事物都在她词语的魔法下,变得灵动鲜活。自然之光照耀在她的诗歌空间内部。光是宇宙的缝隙:“夜晚,一束光打开纽扣/穿透身体,清晨又从脚下退出。”(《感受虚无》)在光与身体的肌肤相接中,人们感受着真实的虚无。光是诗人的收藏:“我收藏光,蓝湖落进繁星时,/暗夜和孤寂燃烧一次。”(《收藏》)繁星倒映在蓝湖,蓝湖如宇宙;孤寂在暗夜燃烧,宇宙亦如蓝湖。在黑夜浸入的自然空间,光是无声的言说。当亘古的自然光线在文字的宇宙中黯淡,现代性的电光便穿透语言。在冯晏的诗中,时空的限界也被冷漠的电光消弭殆尽:在清晨的候机大厅,“体内的填充物是报纸被揉成一团,/照亮它们的白炽灯/高冷,发出吱吱声”。(《清晨的候机大厅》)极富现代性的不只是电光,还有雾霾。雾霾遮蔽了光、冲淡了光,但光线无法穿透的浓霾却给诗歌留了一个出口。诗集《碰到物体上的光》中辑录了多首关于雾霾的诗作。在冯晏看来,雾霾正和纯洁的词语、干净的光与时间一同渗透进我们的身体,污染母亲为我们赋予的洁净:“都市,雾霾一次次越过母亲/新赠送给你的护身符,血管里/后来流进什么,父母一无所知/就像他们的血液,生你时/大自然还洁净,如今他们是所有人。”(《内部结构》)
正如《碰到物体上的光》这一题目所透露的一般,冯晏以词语的光束作为诗的指尖,轻轻触碰着世界万物。她的语言有柔软的肌肤,也有坚硬的骨头,她敏感的诗思与精妙的诗艺如同一道光线,锐利、精确,不断拆解着缠绕在日常生活与神秘宇宙之上难舍难分的“千千结”——“光线解开打结的红绳,/晒干阴湿的裂缝,/照亮我文字里的骨头。”(《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