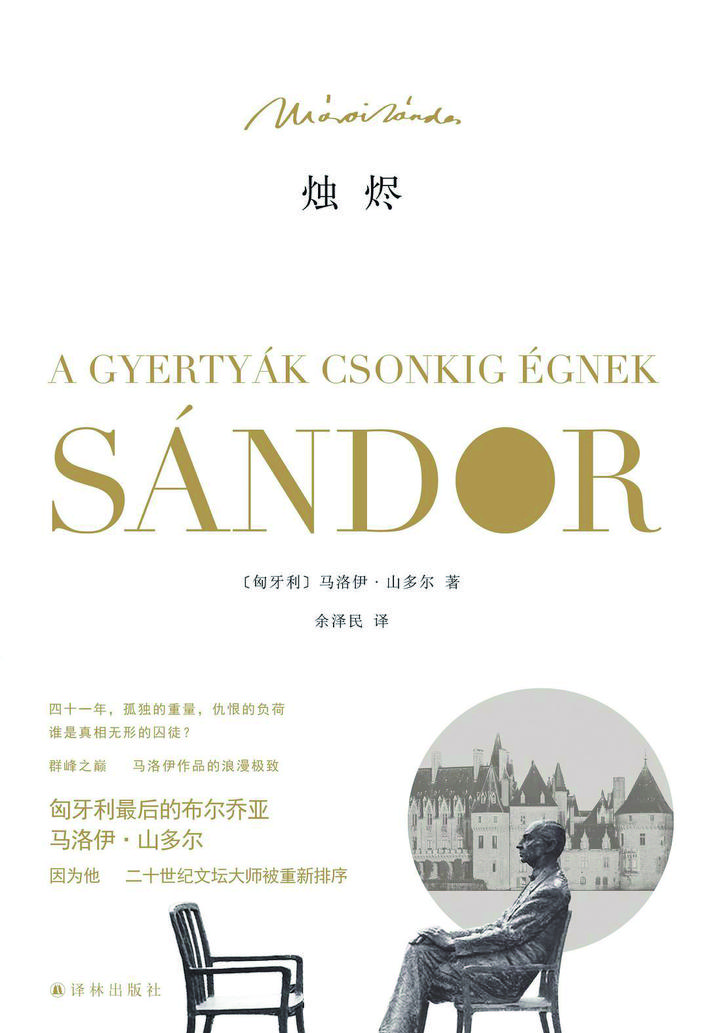马洛伊·山多尔(1900-1989)的人生和文学创作都是复杂的。这位本应该成为20世纪匈牙利文学史上大师级的作家,于1948年离开母国,流亡他乡,在改变自己人生的同时,也多多少少改变了文学史的写法。从山多尔1918年发表第一部诗集《记忆书》到他背井离乡的20年间,是匈牙利背负深重民族苦难的时期,也是山多尔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两者互鉴,更能凸显出山多尔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山多尔虽然生活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芜杂历史场域,但他的创作也如这一时期很多《西方》杂志作家一样,存在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战争及周边的社会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小说的背景,但并不是全部,在社会历史现实之外,山多尔思考的是关于文学本身的意义。
《烛烬》是早期山多尔小说的代表作,这部1942年问世的作品因为使用了“孤独的匈牙利语”写作,虽暗香浮动但却一直无人来嗅,直到1990年代末期才重新进入西欧读者的视野而最终被确定为经典。《烛烬》讲述的是将军和他的老朋友康拉德在分别了41年之后,又在将军的宅邸重逢,并秉烛夜谈直到拂晓,所追忆的往事涵盖了他们的身世、家事、青春、友谊和爱情。小说形式上的特征是以“骨”和“气”为主,两位主人公的交谈既像是中世纪骑士决斗前的激昂陈词,又好似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慷慨独白。而在所有关于过往的勾连中,隐含了一个仿佛是又仿佛不是秘密的秘密,即当年康拉德因为爱上了将军的夫人而背叛了将军,以至于妄想在某一时刻用一颗子弹结束将军的生命。这成为两人分道扬镳40余年的原因。
然而,这只是对这部小说主题和内容的一般性描述,并不能代表小说作者的全部初衷。将军回忆了诸多往事,最重要的是少年时的挚友因为他的妻子成为了背叛者,但这些往事并没有在康拉德那里得到确证。换句话说,《烛烬》看上去“讲述”的故事,只是将军的一面之词。这就给小说赋予了很强的蕴藉性,也留给读者更多的阐释空间。所以,小说实际的一种可能是,确有将军所言其事,康拉德因为羞愧一言不发;而另一种可能是,将军所言只是自己的臆想,康拉德不屑一辩。可以确定,这种故事或情节的设置是小说家有意为之,山多尔像形式主义者一样,运用“阻碍”和“延迟”等多种手段保持着读者对故事进度的注意,但最终呈现的是一个关于含混和歧义的小说文本。
含混与歧义的表征之一是,小说呈现的故事本身就“似是而非”。作者为了能够使读者悉数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用了大量的笔墨介绍人物及其关系,在关系中塑造人物形象演绎故事情节,但实际上从作者的主观上说,山多尔并不想讲述一个完整而饱满的故事,而是用散点的写法完成故事中大部分“点”和“线”的叙事,与其说看上去将军是在“建构”一段关于往事的历史故事,毋宁说他是在用片段言说着某一段时光的切面。在《烛烬》中,将军之所以选择和康拉德彻夜长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想了解康拉德对于爱情、友情与背叛的真实想法,比如“在那天早上打猎时,你是不是真有意杀了我?那是否只是一个幻觉”,再如“那时你是不是克里斯蒂娜的情人”,他既想知道答案,又禁不起他所预想答案的打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左右摇摆踟蹰不定。其实,小说本可以有一个关于问题的解答,将军夫人克里斯蒂娜的遗物中包含着“真相”,将军本想和康拉德一起打开本子,共同见证克里斯蒂娜内心的天平倾向于何处,可是在康拉德拒绝之后,将军将日记本投进了壁炉的柴烬中,又一次将答案抛向了未知,将含混和歧义进行到底。
含混与歧义的表征之二是,为了达到故事“似是而非”的目的,山多尔可谓费尽巧思,运用了很多手法。一是以“权力意志”般的“作者论”严密控制并“监视”着小说节奏,在卡尔维诺所谓“快”与“慢”中拿捏着足以控制读者的尺度,一开始就为读者布下了叙事圈套,使读者穿梭在华美语言编织的已知与未知中,而对故事的封闭性与否浑然不觉,被作者“控制”的读者等来的是一个有待补充的故事而不是故事的全部。二是将康拉德塑造成了一个弱势形象。他少言寡语,和将军的滔滔不绝和义正言辞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将军的问题也“不想回答”,以至于读者掉进了一个相信将军就是相信正义甚至相信事实的先验中,但恰恰如此,将军回忆和判断的真实性也被降低了,故事呈现出了某种模糊的美感。三是戛然终止叙事导致故事没有结局。在小说中,将军和康拉德41年未见,但给读者的感觉上一次分别仿佛如昨天,所以两人情理中的寒暄被省略,以至于虽然将军和康拉德彻夜长谈,但问题没有解决,关系没有恢复,创伤没有抚平,故事就因康拉德的离开而终止,后面发生了什么,山多尔并没有给出答案,这无疑增强了故事本身的不确定性,“召唤”读者完成情节与人物的“填空”。
那么,为什么山多尔如此含混和歧义的小说,能俘获那么多读者的心呢?除了前文说到语言的激情之外,其中也涉及一个比较重要的叙事学问题。实际上,《烛烬》和19世纪的很多伟大现实主义小说一样,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回忆、友谊和背叛的故事,但讲故事的方式却与巴尔扎克式的或狄更斯式的明显不同。在《烛烬》中,将军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力,他在小说中的话语远远超过了康拉德,是事实上的小说叙述者。这样一来,从叙事学的角度而言,就产生了一种象征:小说作者“控制着”将军,读者“成为”康拉德,表面上是将军在和康拉德对话,实际上是作者在和读者对话。将军和康拉德、作者和读者同时存在于《烛烬》中的四维世界中,既拉近了读者与文本的阅读距离,又缩小了读者和作者的心理距离。尤其是,《烛烬》虽然将故事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内,但并不是在讲述一个社会历史事件,所以社会历史事件在小说中变得无意义,这使读者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文本之中,心甘情愿地陷入到作者的“叙事圈套”之中。
文学是开放而多元的,从施莱尔马赫经伽达默尔、伊瑟尔到尧斯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思想不断提醒现代读者,很多作品都为读者对文本的阐释提供了一片开阔地,他们甚至可以成为作者本身,而含混和歧义已然成为这片开阔地的地标性建筑,使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成为实践上的可能。也正因如此,福斯特才有勇气宣称,文学并不存在一个准确的定义,文学的概念具有多种可能,自20世纪初期的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不断地预见或印证福斯特这种说法,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卡夫卡、普鲁斯特、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思考“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山多尔也可以位列其中,在《烛烬》中,他在有意识地引导读者去完成对文本丰富性和蕴藉性的确认,同时也认识到,含混和歧义及其所产生的诠释和过度诠释,都可以指向文学甚至文学概念本身。人们不会忘记《烛烬》,是因为他们合上书页的那一时刻,也参与到了小说的创作之中。至于文学史中的《烛烬》,虽然对这部小说的解说才刚刚开始,但时间已经证明这是一部经典之作。就像小说自身讲述的那样:蜡烛燃尽了,可是小说并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