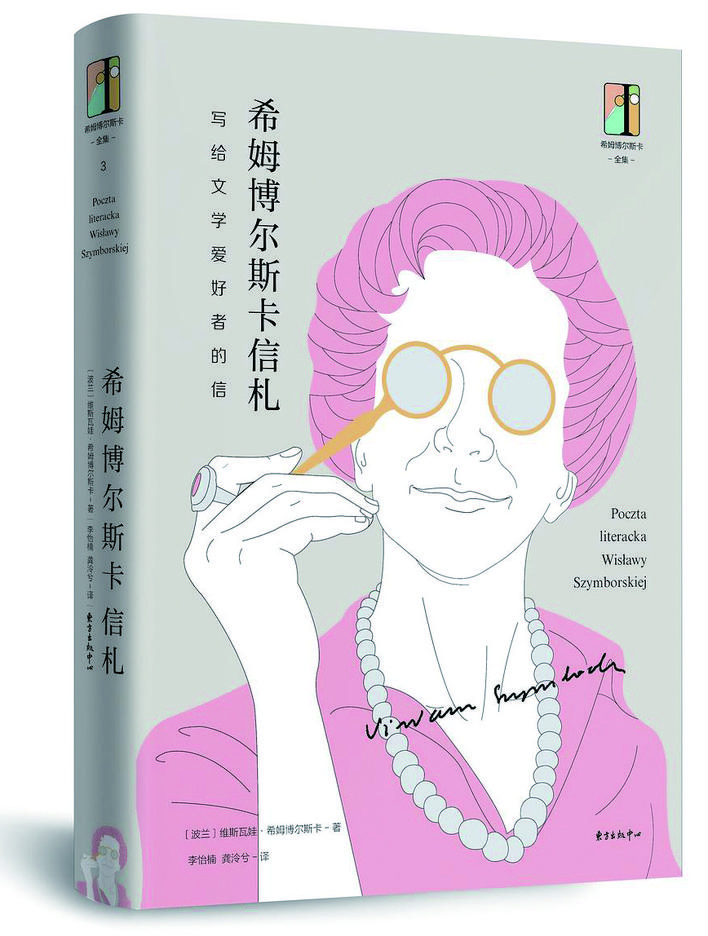在199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作为诗人,希姆博尔斯卡早以其巧妙精准的构思、力道张弛有度的反讽与字里行间勃发而出的原生力量为各国诗友所熟知。然而,作为文学杂志《文学生活》的编辑,更兼“文学信札”栏目的主笔,她仿佛在书山文海间起落跌宕、谈笑风生间便把江湖笑傲;又仿佛是文学桃花源入口的隐士,以阅文写作多年的胸中底气,为文坛后辈指一指路。而几十年后的我们借着他人的译笔,也终于有机会赏读这漂洋过海的《希姆博尔斯卡信札》,以文学爱好者的心同秀笔锦心的诗人希姆博尔斯卡,隔山隔海超越时世来对谈。
文学编辑最恐慌的季节
作为文学编辑虽是与文稿信件打交道,却也少不了与纸头之上承载的人与事有所牵扯,而信札你来我往之间,便又是一幕幕妙趣横生的“编辑部的故事”。共同邮寄诗稿要一分高下的夫妇、被男友贬损愤而修书编辑部以求肯定的姑娘、授权编辑部修改作品的作者、邮寄芬兰语原文诗歌让编辑挑选以备翻译的文学爱好者……种种奇观令人又是好气又是好笑,顿时便读懂信札之中希姆博尔斯卡时而嬉笑怒骂时而好言相劝的心意所及与心境所在。
文学编辑希姆博尔斯卡最为恐慌的是哪一个季节?是春天!她在“文学信札”中流露出一名文学编辑对春天的心声——
“我们有这样一条规定,就是所有关于春天的诗都会被自动取消资格。这个主题在诗歌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然,在生活中它仍然存在,但这是两码事。”
哪怕早已在诗句中见识过希姆博尔斯卡的幽默诙谐,信札中她略带嗔怪的口吻着实令人忍俊不禁,但也忍不住要作为“普通读者”或“预备作者”对其指摘换位思考,若她指出的春天不应该出现在字里行间,那何种春天才有成为诗歌的资格?你还没回过神来时,文学编辑希姆博尔斯卡已经按捺不住要给文稿中浩如烟海的“春天”一个下马威——
“您写的诗愉悦、流畅、无可指摘,但毫无新意。没有任何能让我们耳目一新的画面或者描写。然而诗歌,哪怕只是触及一些永恒的主题,比如春天的蓬勃,秋日的伤感,都应像初次书写一般,有新的抒情点。换句话说,前人写的那些诗歌,难道还不够吗?此致敬礼。”
读到此处,不论观点暗合还是又懵懵懂懂被数落了一番,在春天里、作为诗文爱好者的你更多的只有欣喜,为这次不出声音的脑内对谈甚至博弈暗生欢喜,太久没有这种纯粹地为诗歌或文学心跳加速的感觉!
与文学爱好者的对话
坐阵《文学生活》,面对形形色色的文学爱好者来信,不论是取决于随信作品水准的答复品评,还是单纯回馈读者的答疑沟通,其中甚至不乏身为编辑对部分行文潦草错误百出、态度简慢随意投稿的讽刺批评……一篇篇回信翻过,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时而对着书页自省、时而替投稿人暗自唏嘘、时而回忆起多年前初提笔尝试写作投稿的自己,信札之间,承载的对话绝非单向度的投递,而是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可以令文学爱好者间心生共鸣的跨时代交响曲。
对于作品颇有才华见地却生性羞怯的作者,希姆博尔斯卡收起狡黠,连语句间的调侃都变得温柔;对于精妙有趣的诗文,希姆博尔斯卡也从不吝啬她的赞美。然而回信面向的毕竟更多为初出茅庐的写作者,因此信札中对于才露尖尖角的文学好苗子,希姆博尔斯卡更多以对症下药的方式鼓励、引导——
“您的文字里有一些东西,有一点想象力,一点玩世不恭,一点了无意义的感觉(非常时髦)。但每个故事都必须重写至少五次。顺便提一句,契诃夫进行了七次修改,托马斯·曼五次(同时发明了打字机)。”
不知他人读罢这些信札之后做何感想,哪怕我深知自己没有成为一个作家的天赋与才干,但却逃不开打心眼里对投稿时能够收到这样一份回音的期待。
对于文学天赋着实有限的文学爱好者,信札这头的希姆博尔斯卡则仿佛扶额长叹后奋笔疾书的文学捍卫者,以各式各样的风格向一位位不合适的文学簇拥者投去编辑的谏言。面对编辑辛辣的回应,也不乏有文学爱好者发起攻势、指责编辑的残酷或严苛。面对来信诗文中的明显缺陷或偏颇,比如只由情感的力量决定诗歌的艺术价值、“所有人用喇叭喊话!”设定的声音效果、垂死的父亲要求外科医生把自己大脑换给儿子的小说情节……诸此种种,有时希姆博尔斯卡也会忍不住拍案而起,用轻快幽默的方式向文学爱好者抒一抒编辑的读者感言。
虽然希姆博尔斯卡的文学信札中对文学爱好者的调笑甚至幽默讽刺随处可见,但大部分时候即使以己度人,作为收信者也绝少有受辱或不对等沟通的感觉,因为信件那头的毕竟是一个好言相劝的文学守望者,只是她的才华让她得以用更多的方式抒发心声,却毫不尖刻。而纵览全集,我们骄傲地发现文学编辑希姆博尔斯卡也未曾吝啬对于性别歧视者、教育价值观偏颇者等群体的批评甚至痛斥。
希姆博尔斯卡谈诗
从读诗、学诗到试着写诗,“诗”的意涵在文学爱好者的心路历程中亦随之起伏波动,什么是诗?诗之于诗人又究竟有何意义?诗人何以成为诗人?在“文学信札”中,希姆博尔斯卡以卡尔·桑德堡的“诗是生活在陆地却希望能飞在空中的一种海洋生物所写的日记”来回应读者“诗的概念为何”的问题。“诗歌(无论我们怎样描述它)无论是现在、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一种游戏,而游戏就有规则。”而诗人绝非拥有一种“习惯于”写诗的能力,诗歌也绝非日常,而是特殊的产物。而每位诗人心中都有在一首诗中讲述一切的渴望,但如果不加以克制,就会沦为超出诗歌范畴的词语狂欢。
“有才华的人不会被‘灵感’所局限。灵感会时不时地落在每个人身上,但只有有才华的人才能长时间坐着,在纸上默写下来自灵魂的声音。不想这么做的人显然不适合写诗。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即因灵感写就的诗歌总是昙花一现,而时常写诗的真正诗人却寥寥无几。过去如此,现在也是这样,将来亦是……”
掩卷辗转,作为文学爱好者,我遗憾没能在尝试写作尤其是诗歌写作的初期读到希姆博尔斯卡的文学信札,以给自己无果的热情再找一个出口;作为文学爱好者,消除了山海时空的阻隔后,得以默默无语地与心神向往的作者对谈交锋,此刻的我,依然因此而心潮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