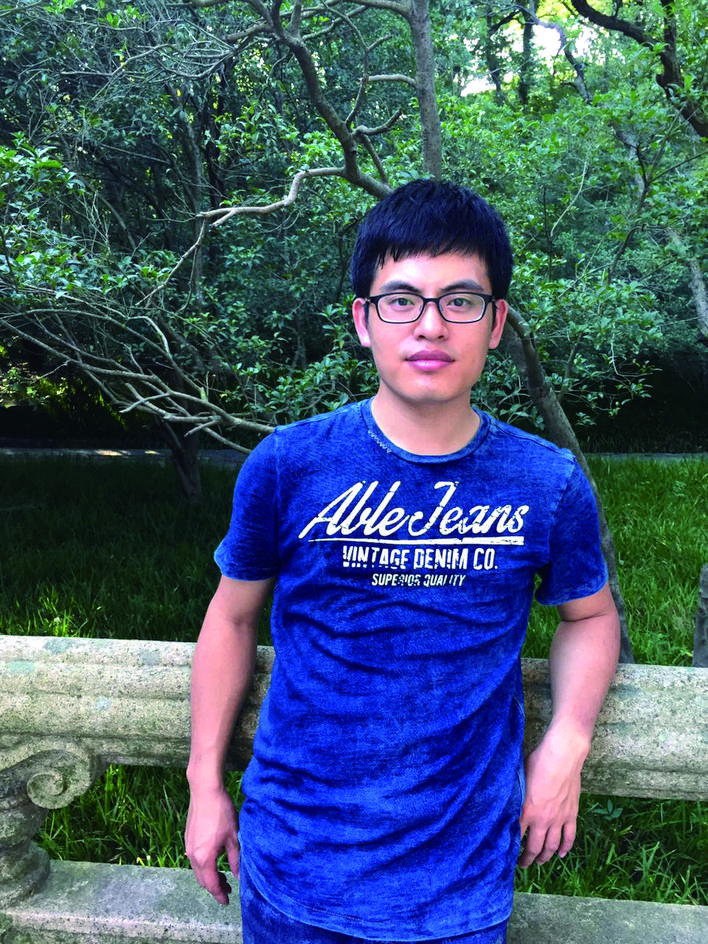截至目前,在还称得上年轻的日子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忘的记忆?
■刘大先:2007年夏天我接了一个活,与某电视台的几个编导到新疆拍摄各民族文化主题的纪录片。新疆幅员辽阔,如果租车自己开不可能短时间完成任务,所以基本上每天都在坐飞机,一下飞机就直奔联系好的人那里采访,选外景,也没有脚本,就是按计划的思路临时构思细节,直接架机器。到塔城的小飞机只有我们一行五人,飞机在空中摇摇晃晃,那个机场空空荡荡,墙上写着“离海最远的机场”。记得从阿勒泰出发去喀纳斯找图瓦人,早上六点出发,忙到夜里一点多才吃饭,居然还有开着门的馕店。喀什到塔什库尔干没有飞机,找了辆颠簸不已的破车开过去,经过沙湖和贡格尔雪山,到地方已是深夜,正是中秋时节,硕大无比的月亮将大地与山川照得纤毫毕现。总共跑了一个多月,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快乐,丝毫不觉得辛苦,可能是因为第一次那么充实而密集地接触到不一样的人口与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同时也和当时精力充沛有关,那是无所挂碍、无所畏惧的勇往直前的青春。
■彭敏:“还称得上年轻”这表述,真是满满的恶意……哼……作为一个没什么出息的文青,青春里惟一的正经事似乎就是谈恋爱。不是我吹,我那会儿谈恋爱,一个人就可以包圆。对方不需要知道我的图谋不轨,学校小树林里的树知道,我把暗恋女孩的名字用小刀刻在了树皮上还附带两句诗:今生已过也,结取后生缘。那是一个不能成寐的月夜,当我做完这件事,心里充满了命犯天煞孤星的悲壮感,像个落败的英雄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呢喃着青春的哀歌。这个夜晚是我整个青春时代的缩影,当有天我回想起来觉得当时好傻好好笑时,我的青春便结束了。
■班赞:最难忘大学时光吧,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期间,为了心中热爱、敬畏的艺术,如是辛劳,如是谦虚,如是投入,如是忘我,也如是执著过。大学四年,从解放天性、观察生活、动物练习、小丑练习,到小说片段、剧本片段再到毕业大戏……我总共塑造过大大小小400多个人物形象,老的、少的、古的、今的、中的、外的、土的、洋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生活万象,千姿百态,而且很多是从车站、胡同、菜市场中捞出来的鲜活形象,是当时中戏学生完成人物形象创作最多的人,这四年是我迈向自己艺术创作的坚实起点。梨园行有一句话叫“搭班如投胎”,这四年,于我算是一次“投胎”,面向了新的开始,一扇大门,就这样豁然开启了。
■王占黑:说来很奇怪,我有一个十分寻常的记忆一直忘不掉。小学四年级的某个下午,天很热,大约快到暑假了。我走在放学路上,照例去邻居阿姨开的烟纸店里买冷饮,边走边吃。那是一种用气球皮来装冰淇淋的奇怪食品,戳一个口就可以开始吸食。那时因为家里翻修,我搬去爷爷家住了半年,再回去,家快装好了,我爸和我约定一起给木地板打蜡。对,那个记忆到这里就结束了,并没有包含到家以后的事。我记得的就是一段边走边吃的放学路。那个画面,那种心情,里面没有一点不好的元素。各种细节非常普通,但组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巨大的快乐。后来每当我很快乐的时候,聊天、行走、独处,记忆就会一跃而至那个下午,情绪完全不受时空的阻隔,好像自己又走在那条路上了,嘴里吸食着奇怪又便宜的冷饮。它成了一个快乐的底色,伤心的是,它也变成了快乐的天花板,往后的事再怎么好,也许能与它比肩,却再无法超过了。
日剧里常有这样一种“童年闪回”的套路拍法。阴影或乐趣,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在主人公生活的关键时刻跳脱出来,刻意引导观众往他/她的童年去想。看多了就觉得无趣,刻板,厌烦。可是仔细想想,自己也确实有这样类似的体验。这东西说出来或许毫无意义,也很难做到令人相信,甚或共感。我想这是私人记忆中最神秘而有魅力的地方,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记住哪一段,也说不出因为什么而记住它。
有没有一个人、一部作品曾深深影响过你?有人认为,星象与自我建构 和创作存在某种关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大先: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是综合的,很难说某个具体的人或作品,但是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对于我还是有特殊的意义。最初我是在一个美术系教授的讲座上听到这本书,后来找来看,以高更为原型的故事让我发现一个人居然可以抛弃世俗的一切去寻求自己的理想,虽然我可能做不到,但那种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影响无疑是微妙的。我查了一下毛姆是水瓶座,我不觉得星座和创作有必然联系,当然苏珊·桑塔格可能不这么认为,她会将本雅明、阿尔托、巴特、卡内蒂等放到土星下讨论。我是天蝎座,据说天蝎和摩羯是十二星座里最强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它们的特质具体如何,这个应该是建构和自我建构相结合的产物。
■王鹏:女画家周思聪。1996年,还在上初中时得知女画家周思聪去世的消息,不禁泪下。那时年少自不知道周思聪的艺术成就和人生经历,却忍不住悲伤。原因很简单,看到了她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平淡微笑却掩不住倦意的脸,就像是一位母亲。后来渐渐了解了周思聪,也接触到《人民和总理》《矿工图》《边城小景》等一系列作品。我还道听了一些她虽不算传奇但仍让人感慨的情感经历,这时我多少理解了那种倦态和寂寞,可在那难以触摸的微笑和沉默背后,就真的没有怨吗?
带着这样的心情,遇见了周思聪在生命最后时期创作的残荷系列,我的疑问似乎也有了答案。荷虽凋残但没有一丝颓败,徘徊于自在云水之乡;虽用宿墨,墨障却如此清明澄澈。“最后的风荷”,是画家临终的绝响,没有幽怨,有的只是对自然生命的轻声叹息。画家把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传达于水墨,寄寓于残荷。这位经历岁月飘零的画家给出了这样的态度,她选择了微笑。时至今日,面对这一系列作品,恕我仍无法用任何赞美技巧的词汇和术语来形容,可能我真的还看不懂她的艺术,但我知道我真的被感动过。
■季亚娅:嗯,有的。但我其实是想让他的影响存在于自己的作品里、在做过的事情里,而不是直接说出来哈哈哈。他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90年代的韩少功”,题目是我的硕导贺桂梅老师建议的,可能因为我是湖南人,现在想来意味深长。研究对象分很多种,一位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会在一个青年人构建、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混沌初开的时刻,打下精神的底色。他对我的影响,最大的在于,他自觉区分于学院知识分子的站位,他曾以思想和文学、更重要的是以行动的方式参与一个时代的想象和建构。知识与行动是合一的,心与身是不分离的,学问与生命是相关联的。回到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许多看起来了不得的立场主义之争,不过是“索引之学”和“口舌之辩”。嗯,行动派,在行动中理解、感受、思考,“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这甚至影响到我的职业选择,在一线做编辑而不是学院研究;不过这条路上我还有第二个偶像,希望以后有人再提问,让我有机会说(手动微笑),更希望有一天我能把他们写在我的文字里、做过的事情里。
至于精神笼罩,没有笼罩,他(她)们也是具体历史处境中的人,他(她)们也曾经历分裂、变化,与你契合的部分才会长出你自己。因为你要面对的是你的问题、你的生活,你可能在自己的问题里出现反对他的时刻,然后在否定的意义上意识到他的存在。比较严重的情况其实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曾经敬仰过、相信过的人,被证明是……你会虚无吗?其实这样的时刻已经出现过了。也不能保证以后还会不会出现,是吧。可以肯定的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是我自己的导师。
哦,星座,巧了,他们都是摩羯座。
■班赞:北京人艺焦菊隐导演的《茶馆》吧。台词、导演、表演、舞美、音效、气氛……演出的整体性,太好了,简直不能更好了。《茶馆》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国话剧艺术的标高,现实主义表演的巅峰,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代表。《茶馆》几乎是所有戏剧人心中的一座“圣殿”,说它是一座高峰并不为过。这个高度其实是中国人在舞台上感受、思考、表达时代生活的深度、浓度、准度、精度融合凝结而来的。北京人艺对我来说,不仅是工作单位,让我获得良好的创作方法、工作氛围,更是价值观、是一场关乎视野、格局、艺术心性的淬炼。在这里,我知道了,须永在舞台上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我知道了不是“演”,而是“生活”在舞台之上。我知道了,舞台是生活的搏击场,是人的精神交流之处,是一个民族思考的场所。
■杨好:雷蒙德·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确实影响了我。钱德勒出现在一个青春的诡异时期,当时我恰好结束了经典阅读的时期,在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之后,突然看到了钱德勒,有一种接受了某种诱惑的解禁快感。钱德勒的作品有强烈的迷人感,是来自于作品的氛围和摇摆的直觉世界,而不是正直的精神力量。我恰好和他同一天生日,严格来讲处在巨蟹和狮子的交界,这样的星座组合带来了暴力和敏感、奔放和自闭的结合。其实我觉得星座和创作没有太大关系,星座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种心灵巫术,可信又不可信。
■黄湙云:由陈可辛导演,张曼玉、黎明和曾志伟主演,1996年公映的香港电影《甜蜜蜜》曾经深深的影响到我。1996年正值香港回归前夕,也是一代歌后邓丽君逝世翌年。电影借助这一特殊时代背景,讲述了20世纪末期香港新移民的艰辛岁月,并以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贯穿始终,成功抓住两岸及港澳地区中国人的共通情感。影片剧情始于1986年,终于1995年邓丽君骤逝当天,在中国出现移民潮的大背景下,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展现了香港回归前十年的历史变迁。
该电影的核心命题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社会的同化与自我认知。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文化多元、贫富两极乃至地域歧视都是城市的特点,也是整部电影的推动力。二是实用主义爱情与理想主义爱情的比较。黎小军给了李翘最初的心动与异性的关心,是初恋情人的角色。豹哥则使李翘的人生展开,令她蜕变成真正立足于社会的女人。三是小人物的命运挣扎。影片中黎小军与李翘时隔数年重逢在婚礼上,相互问及现状却彼此无言。曾是多么坚定带着理想去生活,可岁月将人们变得面目全非,生活完全背离了当时的初衷。当然啦,至于影响是好的还是坏的,说不清楚。
创作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创作素材时会焦虑吗?通常来说,你从哪儿获得创作素材和动力?有没有卡在瓶颈、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班赞:创作时从不会焦虑,从来没有过。不创作才焦虑吧。戏剧工作的各个环节,无论导表演,还是舞美的灯、服、道、效、化各部门创作、排演、合成的过程,大家精神上都是高昂的,无比快乐,尽管很累很累。因为只有创作时,我们才获得无比珍贵的机会,可以敞开心扉,散开怀抱,去观察人、体贴人,去喜欢人、爱人。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儿吗?好像没有吧。或者我还没有遇到。如果遇到特别烂的剧本,不接工作就是了。如果非要说的话,无论是导演还是表演工作中,我感觉艺术创作最终的着陆点都应该是“人”。我总愿意对“人”、“人物”和“人物关系”进行最有热情、最有耐心的挖掘和发现。《红楼梦》里有句话“人情练达即文章”。人情练达才是戏,才有戏。
创作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
■郑小驴:在家写作的时候,我首先把自己伺候得很舒服才写,比方书桌很久没擦啦,地板脏啦得拖拖了,老朋友好久没联系啦该联络联络感情了,冰箱里的啤酒不太够了,龟背竹好像几天没浇水了,有几本想看的书还没来得及看,咖啡也没泡……等一切忙完,已经精疲力竭,又到该吃午饭的时候了。所以我更喜欢在图书馆或者咖啡馆写作,在公众场合没法开小差,注意力更容易集中,效率相对要高一些。写作的时候我喜欢单曲循环,听点轻音乐或者老歌,我听窦唯的《入秋》,写过一篇中篇小说,听到熟悉的旋律,写作的温度就上来了,能保持手感。
我手心容易出汗,书桌前得摆一块湿毛巾,或者经常跑去洗手间洗手。写到嗨的时候,想抽烟,站起来蹦哒几下,伸伸懒腰,吼几嗓子,在公众场合没法干这些。我很希望能改掉这些劣习,听说陈独秀最高产的阶段是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时候,看来作家有时的确是需要点规训与惩罚。
曾在哪些地方长时间生活过,对你有什么影响?对自己最满意和最不满的是什么?
■班赞:不是说艺术是故乡吗?艺术是来处,也是归处。最满意是有天赋,最不满意是天赋不够。
你现在多大,会开始养生吗?会不会在某个时刻产生对时光飞逝的恐惧?
■季亚娅:韩少功曾经和我说:45岁之前随便折腾,到45岁就不要折腾啦,就要定下心来啦。按这个标准,我还能抓住个折腾的尾巴,我理解青年也就是折腾哈哈哈哈,所以我自以为还赖在青年的队伍里。
养生?许多年前,第一次去汨罗八景峒看韩少功,他那饭桌兼书桌兼会客桌上赫然放着一本书《求医不如求己》,忍不住哈哈大笑。这本书出现在当时的他那里,怎么说呢,就好像是,仙女也会上厕所吗?革命者也要吃肉的吗?仰望星空也会关心冷不冷的问题吗?嗯,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喜欢吃肉胜过枸杞。我还在创造和享受呢,如何有空顾及衰老。泡脚?泡脚如何能比得上泡澡啊?
■彭敏:我今年36岁……你才养生,你们全家都养生……我可是一个每天喝可乐雪碧美年达的宝宝,还是一个拍照用b612别人比剪刀手我比心的宝宝!在我看来,所谓衰老并不是牙齿的松脱、发际线的位移、小肚腩的扩张,而是进取心的衰减、好奇心的收缩以及对孤独的抵抗力下降。上述症状已经在日甚一日地侵蚀着我,而年轻人则会用种种尊称把我排除在他们欢快的阵营之外,后者比前者显然更能令人大起我生已老的感慨。养生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养生的方法并不指向物理层面,而更多是激励自己维持对外部世界的欲求。如果我还能不断占有更多东西,我的灵魂或许就能老得慢一点。如果有一天我像米沃什诗中写的那样:“尘世中没有什么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人值得我去妒忌。/无论我遭受了怎样的不幸,/我都已忘记。”要么我开始贩卖专供中年人的廉价鸡汤,要么我老得无可救药了。
■班赞:不仅在艺术上遵循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演剧传统,在养生上也遵循北京人艺老艺术家的教诲。92岁的蓝天野老师说,最大的养生就是不养生。哈哈。尽管时光不停留,不过,无论在任何年龄,都不妨碍我们拥抱生命,人艺老艺术家苏民老师曾经有一句特别好的话,“痛饮生活的满杯”,嗯,痛饮生活的满杯。
■杨好:我很依赖养生,养生已经成了我必不可少的日常流程,虽然更多的时候,这套流程是为了让每天熬夜的不良习惯得以有一个安慰和弥补,而不是真的有着天大的效果。养生特别像悔过的仪式,比如给自己刮痧,敲胆经,吃小药片,分早晚喂自己各种芝麻丸、八珍糕啥的,其实都抵不上熬夜带来的消耗。也不是为了抵御“老去”,时光一直在走着,和我没有关系,从不拿时光和年龄来励志,这会让人生少了很多不设防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