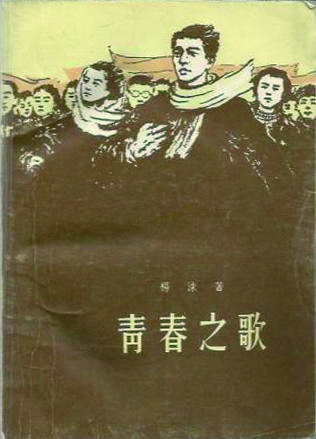在十七年文学中,《青春之歌》是少有的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这部带有作者杨沫自传意味的作品一经问世,不仅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在日本也引起了青年人的热议。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著作都会把它作为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经典之一进行讲解。事实上,小说中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爱情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晚清到五四时期风行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林道静与卢嘉川的感情纠葛则更像是欧洲浪漫骑士小说的革命版本。但是,在我看来,《青春之歌》的经典性在于它塑造了林道静这样一个在历史中不断追求成长的女性形象,而她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作为个体的女性和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命运走向。
我们知道,现代中国的两大主题是启蒙与救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的要义是建立个人的现代性。因此,现代文学初期特别注意书写个人与家庭的冲突,力图使个人从家庭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巴金的《家》突出表现了这种思想意识。在讨论个人启蒙的过程中,女性的个体命运也浮出地表,成为当时的作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面的契机是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国的上演,它引起了人们对出走的娜拉的命运的思考。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预言,娜拉要么回来,要么堕落。很明显,鲁迅对走出家庭的女性命运持有比较悲观的态度。鲁迅的悲观不仅体现在他的杂文中,而且体现在他的小说《伤逝》中。走出家庭的子君与涓生结合后,很快就因为无爱而重新回到了旧家庭,最后郁郁而终。但是,女性在现代中国的命运走向恰恰不是沿着鲁迅的预言走的,一批批觉醒的女性个体最终通过参加社会事务甚至革命,使自己不断成长。从某种意义上讲,《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个人成长就是现代中国女性人生道路的缩影。
小说一开始,出走家庭的林道静是一个尚未被启蒙的少女。此时,等待她的是北大学生余永泽。通过他,林道静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余永泽的书单中有《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茶花女》以及拜伦的诗歌等,我们从中看到了新文化运动中个人觉醒和个性启蒙的影子。正是这些19世纪的人道主义思想给予了林道静力量和勇气,使她最终摆脱了旧家庭的束缚,与余永泽住在一起。然而,对于现代中国女性而言,仅仅从旧家庭中逃出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女性如何以一种主体的姿态参与到社会和国家的事务中。如此,女性的个体解放方能与国家的救亡事业融入到一起,获得更高的意义和价值。而现实却是,受到五四新文化启蒙的女性刚从旧家庭出走,又回到新家庭中去了。此时,新家庭便不再具有解放的功能,相反成为了阻碍新女性走向社会的力量。作为女性个体,林道静与余永泽结合之后,面临的困境便是如此。显然,不断追求进步与成长的林道静无法忍受这种情况。因此,当共产党员卢嘉川出现在她的生命中,她很快就受到了新思想的吸引。这种新思想的主题是阶级、救亡、革命。毫无疑问,对于林道静而言,它们堪称又一次思想启蒙。只有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她才能与余永泽分道扬镳,冲破新家庭的藩篱,走向社会,与历史同行。事实上,林道静的“左转”也是20世纪30年代青年大学生思想转变的象征。“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步步入侵,国家日益危亡,当时大学生纷纷倾向于左翼思想。因此,《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思想和人生转变既是对现代女性个体命运走向的实录,也是对从启蒙到救亡的过程中青年思想变迁的记录。
众所周知,《青春之歌》前后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958年的初版本,一个是1960年的修订版。两个版本差异很大,修订版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生活的七章和组织与领导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在我看来,增补的内容对于丰富林道静这一人物形象是非常必要的。从现代中国女性成长的角度看,女性成长的真正落脚点必然是社会实践。因此,对于女性个体而言,思想启蒙仅仅是成长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步骤是将思想化为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思想才能找到落脚点,女性也才能真正地参与到社会变革当中去。同样,对于林道静而言,卢嘉川的任务仅仅是完成对她的思想启蒙。小说中,卢嘉川很快就牺牲了,替代卢嘉川帮助林道静继续成长的是江华。与卢嘉川不同,这是一个革命经验非常丰富的共产党员。正是在他的帮助和带领下,林道静得以真正地了解中国的现实和革命并投入其中,成为一个革命者。所以,回顾林道静的成长之路,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在她生命中的三个男性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具有不同的思想性功能。余永泽的人道主义思想帮助她摆脱了旧家庭,使她获得个人意识;卢嘉川的阶级革命理论让她走出新家庭,走向了广阔的社会;江华的革命实践意识则帮助她第一次关注了中国的具体现实,并参与到改变这一现实的革命进程中。在与这三位男性的交集中,林道静实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女性个体在历史中的成长。
这是从女性成长的角度来看小说增补内容的合理性,杨沫本人对此也有自己的解释:“这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定的基础。”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杨沫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概括了《青春之歌》的主题。也就是说,林道静的成长之路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成长的隐喻。从中国革命文化的角度看,如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参与到革命进程中,需要一个改造的过程。对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很明确的说明。在这篇经典文献中,毛泽东首先肯定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但是他又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与工农结合,不能自我改造,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在中国革命文化里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战士之间是存在差距的。如果前者想要转变成后者,就要有一个与工农结合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修订本增加林道静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当然,我们不能说,杨沫如此写林道静仅仅是为了符合革命文化逻辑的要求,而不符合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事实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有一种与工农结合的冲动。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一些人便喊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量的知识分子真正深入到民间,与工农结合在一起。这都是历史上真实的存在。因此,《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道路便不仅仅是革命文化逻辑的演绎,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十七年文学重新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一大批学者对它们进行了“再解读”。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青春之歌》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青睐。正如本文开头所言,我更愿意把这部小说的经典性落实在这样一点,即它以一个在历史中不断追求成长的女性形象林道静隐喻了作为个体的女性和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从当下语境出发返观这一经典人物形象,她对于今日女性和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仍然具有很大的思想意义和价值。
作为一个女性,在个人成长方面,林道静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社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朝着两者融合的方向迈进。因此,对林道静而言,个人的启蒙与国家的救亡是一体的。并且,阶级、革命和救亡意识的觉醒是一次更大的思想启蒙。正是基于这第二次启蒙,她才能把真正的个体生命投入到社会事业中去,实现女性个体的人生价值。与林道静相比,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在强调女性解放时,往往在女性个体与社会之间建立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其基本逻辑是,因为社会是男性的社会,而男女之间是对立的,所以女性与社会也是对立的。既然女性与社会也是对立的,那么她们便更愿意强调女性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却往往忽视女性和男性一样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而存在。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中国的女性逐渐与社会相隔绝,变成了更加孤独的个体。如此,封闭性的女性个体不仅无法从整体上分析自己的命运,更无法从社会方面获得自我解放的资源和力量。从这个层面看,林道静的女性成长之路恰恰是今日女性的镜鉴。她启发我们,女性在获得了自己的房间以后,重要的不是把自己封闭在里面,而是走出房间、走向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和国家事务,取得拯救和解放自己的力量,实现女性个体的人生价值。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林道静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和成长,是因为她有勇气走出自己狭小的经验世界,走向更广阔的社会人间,与无穷的陌生人发生切肤的关联,从而开拓自己的人生边界。她的这一精神正好是今日青年知识分子所缺失的。在当下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一般囿于学校所培养和塑造的个人经验和书本知识,很难走出舒适区,去实践一些能够丰富自己人生体验的事情。从反思当下青年知识分子的角度看,林道静的人生选择对我们不乏启发。她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只有走向社会,让自己与社会国家发生正面的、积极的关联,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成长。
事实上,十七年文学的一大特点便是它着力塑造超越个人的主体形象。《红岩》中江姐和许云峰便是这样的主体形象,《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也是一个不断超越和克服个人的主体形象。正是在对个人的不断超越中,作为女性个体和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在历史中获得了成长。对于这种超越个人的主体性,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它的危险,即它很可能产生一种对个人性的压抑和控制机制。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它的优点,它可以使个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产生有效的关联,让个体在集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也是今日重读《青春之歌》以及理解林道静这一经典人物形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