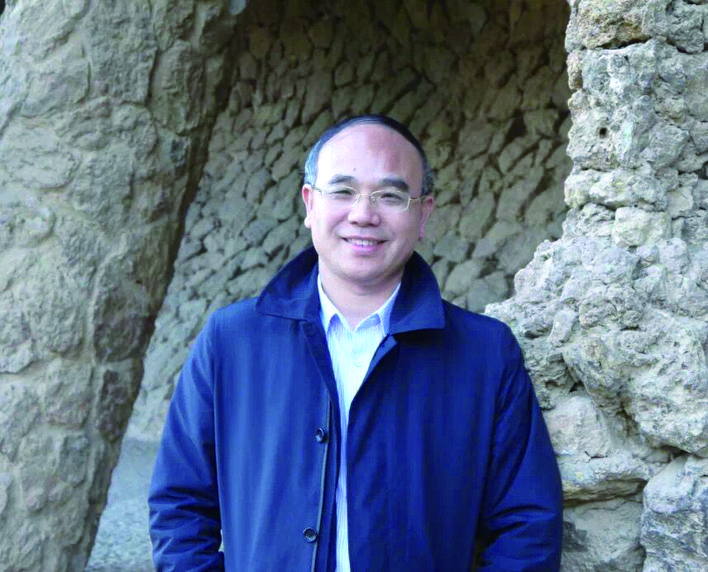记得在2017年底,应邀去北京大学访问,在人文工作坊谈文学翻译。我说,都讲做翻译难,但我觉得翻译者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有幸翻译过巴尔扎克、雨果、普鲁斯特这样的文学大家,能有机会跟他们神交与对话,是一种幸运。通过翻译,我有机会接触到加利、勒·克莱齐奥、德里达这样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哲学家,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借助“异”之明镜照自身,认识自我,丰富自我,更是一种幸运。
在多个场合,我也说过,做翻译,不能止于翻译,要去探索翻译背后丰富的世界。就文学翻译而言,要经由翻译,以自己的理解去重新阐释经典的作家,用自己的目光去发现尚未被认可的优秀的作家。对于法国文学,我没有系统的研究,不是专家,但作为一个热爱法国文学、多年译介法国文学的译界中人,我与法国文学的接触,用的是特有的方式,是有温度的、有感情的接触。
因为喜欢《红与黑》,我关注《红与黑》的翻译,发起过有关《红与黑》汉译的讨论,这样的讨论,不仅仅涉及翻译的原则、标准与方法问题,对于进一步理解《红与黑》这部作品的文学特质与文字风格无疑也是有益的。因为参与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我深切地感受到理解普鲁斯特的难度和表达普鲁斯特的限度,但我更在普鲁斯特这部绝代名著的翻译过程中,一步步走近普鲁斯特的世界,看到了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在文本中如何呈现,体会到了其隐喻的丰富表达和叙事的精心结构。在与普鲁斯特的文字的亲密接触中,对文本之魂有了自己的理解与把握。我不仅在翻译的层面明白了文学翻译中“度”之把握的重要性,更在文学层面领会到了文学创作之个性的独特价值;也在翻译理论的层面,通过对《追忆似水年华》汉译的思考,在句法、隐喻、叙事、风格等维度对如何理解普鲁斯特、阐释普鲁斯特、表达普鲁斯特作了有益的探索。
由翻译为入径,我接触了种种法国文学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如浪漫主义的夏多布里昂、雨果,现实主义的司汤达与巴尔扎克,意识流的鼻祖之一普鲁斯特,法国新小说派的杜拉斯,法国新“寓言派”的图尼埃和勒·克莱齐奥。通过重读我写下了与他们相关的文字,我发现这一个个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辉的文学大家,无意中构成了我数十年来所致力的文学与翻译之双重历险的精神坐标,让我感受到了阅读文学经典、翻译文学经典之于我个人成长的深刻价值。
《法国文学散论》所收录的文字,有别于专业的文学批评之作,没有生涩的术语,没有理论的构建,也没有系统的探索,但字字句句都带着真情实感,希望形成一种鲜活的批评力量。我希望如圣伯夫所言,在阅读与批评中有所发现,发掘生成的力量;我更希望,批评能把读者引向文本,在阅读的时刻,文本能生成并内化为读者的生命之流,与读者的灵魂“建立起联系”(“小王子”语),成为读者的“生命之书”(朗西埃语)。
在与法国文学大家的相遇中,我深知选择之于一个翻译者的特殊意义,选择书,就像选择朋友,与好书为伴,会有更开阔的视野,会发现更美丽的风景,会有更丰富的人生。好书,好运,好人生,翻译者之大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