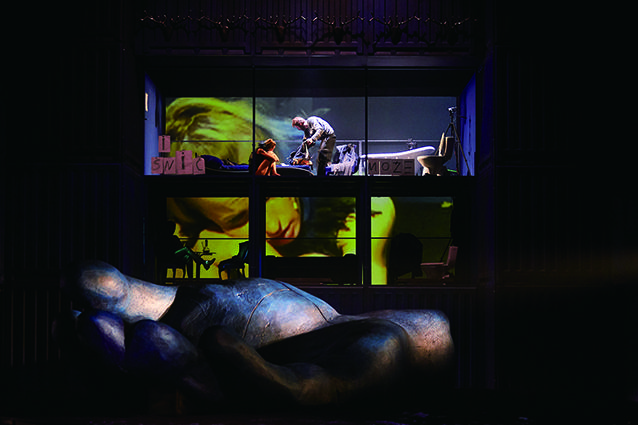■对话人:巴托斯·西德洛夫斯基 (波兰克拉科夫神曲国际戏剧节 艺术总监、导演) 徐 健(本报记者)
每年圣诞前夕,波兰最优秀的戏剧团体和艺术家们会不约而同地汇聚到波兰的千年古城克拉科夫。他们借助剧场空间、舞台呈现表达各自对现实的关切、对人性的探究,在精神的思辨和艺术的逐新中,挑战着陈规,打破着陋习,拉近着戏剧与人、戏剧与城市、时代与人之间的关系,参与并见证着波兰社会的演进和日常生活的变迁。这就是有着12年历史的克拉科夫神曲国际戏剧节。在众多的国际知名戏剧节中,克拉科夫神曲国际戏剧节的参演剧目并没有那么的国际化,也没有其他戏剧节那样大腕云集,但这些都丝毫没有减损其在欧洲剧坛的影响力。这里不仅汇聚了波兰每一年度最值得关注、有代表性的剧目,集中展现着波兰戏剧的选题视角和创作现状,成为观察波兰剧场艺术的风向标,更重要的是它接续着传统、预示着未来,为富有潜力的青年戏剧人提供了创造和交流的平台,显示着波兰戏剧的开放与自信。短短10天的戏剧节,背后是深厚而强大的波兰戏剧文化在支撑、滋养。
在2019年12月6日至15日第12届克拉科夫神曲国际戏剧节举行期间,就戏剧节的办节理念、艺术特色以及波兰戏剧的历史与现状等问题,笔者独家专访了戏剧节的艺术总监、导演巴托斯·西德洛夫斯基。
剧院是人们建立信任的场所
徐 健:您能谈一下创办克拉科夫神曲国际戏剧节的初衷吗?
巴托斯:我是一个善于做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的人。也许正是因为性格上的这种特点,才被推动着去做戏剧节,这样才有了克拉科夫神曲国际戏剧节。准备办节之前,我首先做的事情就是环游世界,我去了伊朗德黑兰和哥伦比亚波哥大。这两座城市给我最重要的影响和灵感就是戏剧节给城市和社会氛围带来的改变。这也是促使我建造剧院的想法。因为我相信,戏剧可以对现实产生影响,可以产生转变的力量,并有力改变一种象征性的叙述方式。
徐 健:在波兰,戏剧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戏剧节的举办与现实生活存在哪些关联?
巴托斯:我总是把戏剧作为最好的传播方式来告诉每一个人“我是谁”,我相信波兰的戏剧家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传统,那就是戏剧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我们所说的社会演进、政治事件和日常生活。波兰的戏剧艺术家和波兰观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波兰观众也确实发现自己由这种艺术视觉和象征性的叙述所代表。所以,戏剧节期间充满着节日的气氛,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总是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些关于波兰的事情,不用读文章和报纸,只要进波兰的剧场,就会知道波兰人的性格和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也会感觉到其中的情感,我把它称之为直觉。它不仅是信息,而且你能感觉到它。这点非常棒,剧场是一个能对社会进行及时反映的地方,也是用来给人们建立信任的场所。艺术家运用想象力表达着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而不是直接在舞台上说出来,这也是波兰戏剧的传统。这其中,演员的亲密感、真诚感和内心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做一个戏剧节,不仅让人们对戏剧感兴趣,也要对波兰的历史文化和波兰的今天感兴趣。
同样重要的是,戏剧节作为艺术的媒介也很有现实意义。它是一种对抗、合作、交流的平台,所以我们把戏剧节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地狱”,这意味着竞争,有最好的演出、国际评审团,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工作是不仅评估自己的创作水平,也对外国人的观点、评价很感兴趣。他们正在改变我们的艺术体系,有时改变我们的观念。这一部分通常有11至12台精彩的演出,由我和我的挑选团队共同完成。第二部分是“天堂”,主要是面向年轻或者崭露头角的艺术家的,我们希望能给这些青年的艺术家提供某种庇护,保护他们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帮助他们参与剧院的相关演出活动。第三部分是“炼狱”,也就是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地带。包括制作、联合制作、国际交流等,这一部分是克拉科夫作品的展示平台,尽管这些作品并不包括在竞赛内,但所有的讨论和辩论都非常重要。
“通过剧院谈论波兰和我们自身”
徐 健:您提到了波兰戏剧的传统,其实剧院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这些年,波兰的剧院,包括戏剧节有没有担心缺少观众的支持?
巴托斯:通常我们不会抱怨波兰剧院缺少观众,这取决于剧院。有些剧院通过它们使用的语言塑造、培养着自己的年轻观众。但总的来说,无论从艺术还是从与观众的关系角度,剧院都是波兰人最重要的艺术体验和生活经历。波兰剧院里有受过良好教育、准备充分的观众,他们对于舞台上的表演拥有很高的接受意识,但有时观众也感到困惑。比如戏剧节,不是业内的同仁邀请同仁观摩演出,而是一个行业真正的节日,我们需要建立的是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增强对剧院作为净化场所的信念。
此外,在波兰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谈论观众、剧院和艺术家之间不寻常的联盟关系。因为剧院是波兰的传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波兰的剧院都是创造语言的地方,它们绕过了审查,绕过了所有政治紧张局势,时刻提醒着我们要团结在一起。艺术家所扮演的角色使他们始终相信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对观众并不冷漠,我们可以去剧院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虽然有时会感到不舒服,但也是很棒的体验。
徐 健:波兰每年大概有多少个剧目演出?你们是怎么从大量的剧目中将这些戏选择出来的?
巴托斯:波兰每年有300个左右的剧目演出,大约有150个会被选中,然后我的挑选者们会去看它们。我自己是凭直觉选择的。通常我都会触及要点,这种要点不是指的主题,而是你看演出时的一种顿悟。我的意思是它不需要是一部伟大的戏剧,但有时看到出色的女演员或不可思议的创意氛围,或它的某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然后你捕捉到它,接着形成一个判断。有时,不得不做出平衡,这个作品在整个波兰戏剧创作中的价值。因此不管是小的临时的剧场,还是一个城市的大明星演出、杰出的大师作品,我们都是戏剧的一家人,都会将大家呈现在这个传统与现代相互碰撞的戏剧节中。在这里,年轻人变得富有抱负,他们可以挑战大师,甚至消灭权威,大师也可以慷慨地同年轻人分享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他们可以用不同的表现方式、艺术理念去表达同一个主题。比如,本届戏剧节的演出主题就包含着“妇女”,因为2019年有很多关于女性和女权主义的话题,所以每一个导演都在试图触及、讨论这一点。首先我会做出剧目选择,然后我会发现这些剧目中存在的共同的观点。我不喜欢先预设一个想法和概念,然后去寻找能够表现这些想法和概念的戏。
徐 健:这一届克拉科夫戏剧节的演出剧目有没有延续以往的风格特色?
巴托斯:戏剧节就像一个孩子,每一年都会有成长和变化。同样,波兰的各个剧院每年也都会有不同面孔且令人振奋的作品出现,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只能适当地保持平衡。毕竟,我们是通过剧院在谈论波兰,通过剧院谈论我们自己,剧院正在成为一种工具,它在激发、推动着我们参与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剧院是有生命的,它始终关注的是人,包括人的身份等基本问题,以及关于当今的紧张局势如何导致相关主题而非其他主题的出现。剧院也是停顿的时间,是塔尔科夫斯基通过电影谈论的停顿的时间。我通常将艺术活动视为时间的停滞,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这种智力话语背后的一些神秘事物,而这些神秘事物,我们在生活中往往容易视而不见。这个戏剧节总是在圣诞节前举行,因为我相信,这个时刻会使整个戏剧节充满活力。它不仅是一个艺术市场,而且在某些方面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戏剧节建立了这样一个品牌:任何风格的表演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人们对波兰戏剧的发展充满信任、信心。
对话、理解与包容
徐 健:选戏的过程中,是否知名导演的作品会更容易入围?
巴托斯:克拉科夫神曲国际戏剧节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没有艺术家的等级存在。我们更多呈现的是波兰戏剧创作的真实现象,它带有一种对话性,不同年龄段的艺术家在对话中相互补充。年轻艺术家可能会面对老一代艺术家的压力,而老一代艺术家也会不断受到年轻人的启发。这是波兰戏剧的一种独特现象,我们既有最重要的艺术家,如陆帕、克拉塔、亚热纳,也有最富活力、创作力的年轻艺术家米哈乌·博尔楚赫、伊沃娜·肯帕等。他们都是艺术之路上的旅行者,都在为同样的目标而战,他们用敏锐的艺术发现、创造,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我们想在戏剧节上保护这种“敏锐的状态”,为那些经常遇到麻烦的艺术家创建一种保护伞。我们不想通过戏剧节去展示谁的作品比谁的更好,谁比谁更有资历,而是我们作为艺术家能带给世界的东西: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能为社会做什么。面对现实,艺术家们并非都是无动于衷的,这些都要归功于舞台上的表演,但是在当今这个务实的现实世界,这样的追求并不普遍。我们的戏剧节带有乌托邦式的气质,犹如一个难民岛。
徐 健:戏剧节评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如何构成的?举办这样一个大规模戏剧节的资金都来自哪里?
巴托斯:戏剧节评委会有非常著名的戏剧评论家、电影制作人、剧本作家等,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领域。例如,如果他们有电影方面的背景,就不会仅仅局限在戏剧的视角看问题,这也是为了有一个新鲜的和使讨论更加复杂的氛围。也许明年的某个时候,我会选择一些视觉艺术家,也只是为了真正发现这个多语言剧场的价值。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戏剧节的举办得益于同一些机构的合作,像克拉科夫市为主要组织者和资助者,波兰文化部从早期开始支持,或多或少给我们15%的预算,以及亚当·密茨凯维奇学院也是一个真诚的合作伙伴,帮助发展这种合作,有他们的帮助和理解是多么的重要,要不然这个戏剧节将永远不会发生。我们戏剧节没有其他大的赞助。克拉科夫市,波兰文化部以及亚当·密茨凯维奇学院加起来总共支持大概85%,剩余部分来自门票收入。
戏剧信仰与改变世界
徐 健:办节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持着波兰戏剧人的创作?
巴托斯: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必须把戏剧节的时间压缩到10天,因为评审团成员都很忙。我们会在10天里尽力来创建节日的氛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见面和交谈。在克拉科夫,大约有10个地方在上演戏剧节的剧目,几乎每一个剧院都在使用。这个戏剧节也是波兰戏剧最后一个重要的演出季,观众可以看到波兰戏剧是多么丰富多彩,艺术家们是多么独立地创造着戏剧的诗学。我喜欢波兰的这种艺术方式,因为艺术家们对戏剧有着非常严肃的态度。他们真的相信并为戏剧而奋斗着,不是在消费剧场,而是一直在为某样信念用心地投入。有一个佛教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和尚20年来每天都往干枯的树枝上浇一桶水,20年后,他看到树枝开花。波兰艺术家认为剧院和戏剧就是这样,每个艺术家都在认真对待戏剧,希望不断用剧院改变世界。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不会诞生任何作品。剧院以这种方式影响社会,播种某种希望,而有信仰的艺术家在追问这些棘手的问题时,也会建立内在的力量和坚韧,包括摆脱日常遵从性的束缚。
徐 健: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波兰导演?
巴托斯:波兰的戏剧导演有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有的倾向于概念化,有的主要是和演员一起创造,这取决于导演对波兰社会的敏感度。除了陆帕,戏剧节上我们还会看到米哈乌·博尔楚赫的作品。他有一部非常棒的作品两年前在戏剧节上演出,叫《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并获得了最佳表演奖。这是关于你如何记住你的母亲的故事,导演的母亲在他7岁时死于癌症,演员的母亲在他高考时也死于癌症。这两个人创造了这个作品,非常感人。事实上,它展现了人的脆弱和无法逃避的悲剧。本届戏剧节,他带来的《道德焦虑的电影》同样是值得关注的。还有我推荐去看看我执导的《哈姆雷特》,所有评论都说它创造了一门“新语言”。
(翻译:伊沃娜)